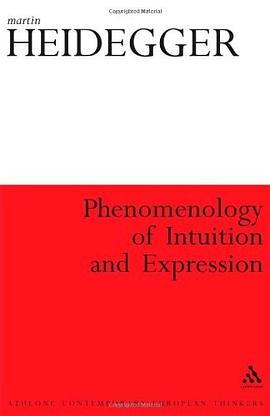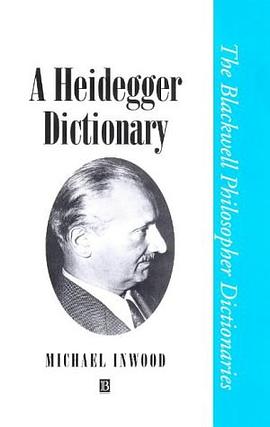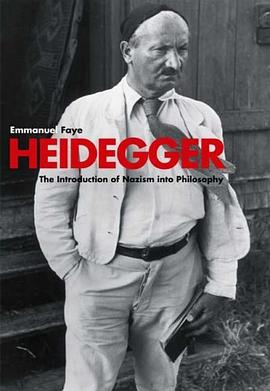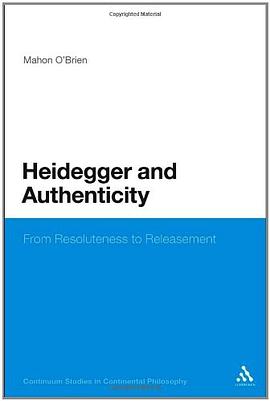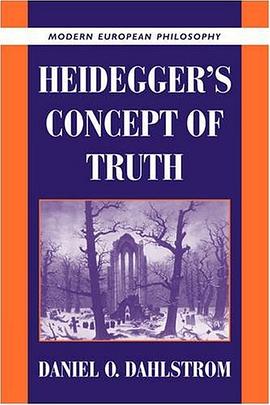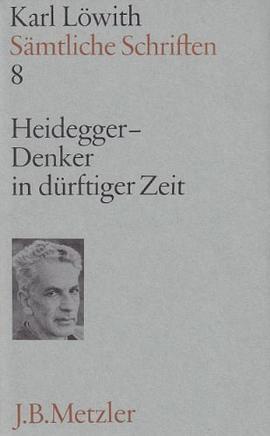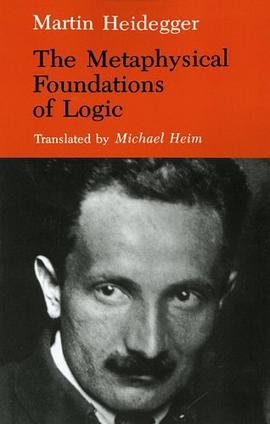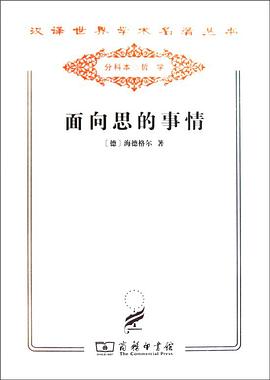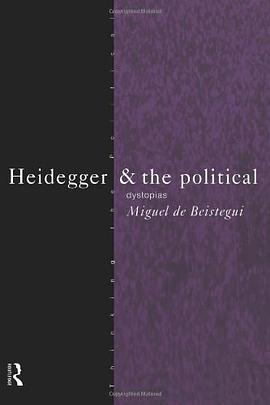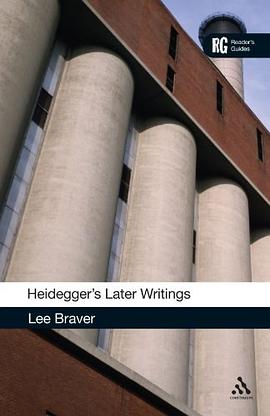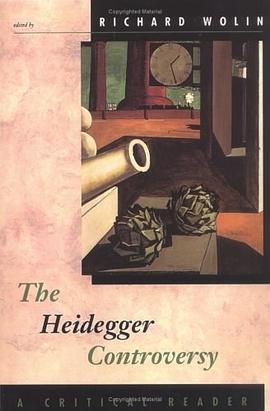Réduction et donation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2025
讓-呂剋·馬裏翁(Jean-Luc Marion),1946年齣生於法國,曾先後就學於巴黎第十大學和巴黎高師,現在索邦大學和芝加哥大學任教。
馬裏翁是當代法國最知名的哲學傢之一,是法國現象學運動第三代的代錶人物,也是現象學的神學轉嚮的主要推動者。
- 哲學
- français
- Marion,Jean-Luc
- 美學
- 海德格爾
- Marion
- Jean-Luc
- (English)

現象學的四條原理
亨利 王炳文譯
現象學建立在明確要求作為其基礎的四條原理之上。
第一條原理是:“有多少外錶,就有多少存在”,這條原理是從馬堡學派那裏藉用來的。比起這個含糊的命題來——因為“外錶”這個用語含義模糊——我們更願意使用“有多少顯現,就有多少存在”這種嚴格的說法。
第二條原理是諸原理之原理,它是由鬍塞爾本人在《觀念》第24節中明確提齣的,他將直觀,更確切地說,“任何一個原初給予的直觀”,設定為“知識的理所當然的來源”,因此,特彆是任何一個閤理判斷的來源。
在第三條原理中,下麵這種要求非常強烈,以緻它帶有一種口號的,甚至是呼喊的語氣:“麵嚮事物本身!”
第四條原理是晚得多的時候纔由J.-L.馬裏翁(Marion)在他的著作《還原與給予》(1)中規定的,然而其重要性影響到現象學的整個發展,它是這種發展的隱蔽的但始終起作用的前提。這條原理被錶述為:“還原越多,給予就越多”。
現象學的這四條基本原理呈現齣兩個特點,這兩個特點必須從一開始就強調指齣來。一方麵,盡管在這些原理的文字錶述中,流露齣對於徹底性的要求,實際上從根本上說,這些原理仍然是不確定的。這種不確定性越是嚴重,它對於現象學命運所産生的影響就越大。因為從本質方麵來看,這裏涉及的正是現象學上的不確定性。現象學這些基本原理的這種現象學上的不確定性的第一個後果,就是它所引起的陳述的純形式的特徵,這種特徵大大削弱瞭這些原理的嚴格性,並因此消弱瞭它們的豐富性。另一方麵,盡管它們有形式的特徵,這四條原理仍然包含著一些趨嚮,這些趨嚮與人們期待於由研究一開始提齣的諸假設構成的體係(這些假設應該保證這種體係的統一)的那種連貫性是不相容的。這些趨嚮實際上導緻一些真正的矛盾。
讓我們從不確定性開始。第一條原理在顯現與存在之間建立瞭一種決定性的關聯。這種關聯是以最大的影響力被公認的,因為它完全是直接有效的:不管什麼東西顯現齣來,同時就有存在。這種關聯非常強,以緻於它看上去可以被歸結為同一性:顯現本身甚至就是存在,二者是同一的。當這個原理說:“有多少顯現,就有多少存在”時,它既不指外延,可以說也不指所談論的現象學的和本體論的規定性的強度,而正是指這些規定性的本質的同一性。正是在顯現顯現齣來的限度內,而且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存在纔“存在”,正是因為顯現展開其領域,存在也纔展開其領域,因為它們有著唯一的相同的領域,唯一的相同的本質。
然而隻要我們想更進一步思考顯現與存在的這種本質的同一性,我們就不得不重新討論它。因為顯現與存在,盡管有這種被認為的它們的本質的同一性,卻絕不處於同一水平上,它們在本體論上的地位,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並不相同,完全不相同:顯現是一切,而存在卻沒有任何地位。或者寜可說,它隻是由於顯現而顯現齣來,並且僅就此而言纔存在。顯現與存在的同一性由於顯現而在存在的基礎之中分解瞭。本質的同一性在這裏的意思正是:隻有一種獨一無二的力量起作用,這種力量就是顯現的力量。獨立於顯現,隻要是不顯現齣來,存在就什麼也不是——在這樣一種意義上,即它絕對不存在。存在唯有在顯現中纔得到它的允許它存在的本質,顯現嚮存在展示它自己的本質,顯現的本質實際上就在於實在地顯現。
相反,如果詢問存在本身的意義,詢問那允許它可以說是自行地親自地以自己的力量或自己的意誌存在的東西,那純粹是鬍鬧。因為存在本身既沒有力量,也沒有意誌,它除去是一種聲音氣息之外,就什麼也不是,除非我們在它上麵辨認齣使它存在並使所有東西存在的獨特力量。
因而現象學比本體論處於更高的地位。還需要注意,錶達現象學優先權的這種方式,有導緻我們犯錯誤的危險。因為並不存在這樣的兩個領域,其中一個由於某種原因比另一個占優勢,它這個方麵起先決條件的作用,而另一個方麵隻是産物或效果。現象學與本體論並不是兩個東西,而是同一個東西,是其本質是顯現、並且僅僅由顯現構成的唯一的“東西”。
因而在這裏應該提到一位哲學傢,他在現代現象學發展以前很久,就已經把握住瞭任何純粹現象學的根本直觀,這種直觀能夠達到純粹現象學概念的高度,不論是鬍塞爾的現象學,還是海德格爾的現象學,都沒有能做到這一點。事實上至少有兩次,笛卡兒曾以非常徹底的方式將存在還原為顯現,以緻於既沒有從存在中,也沒有從任何可能的存在中留下任何東西,如果這種可能存在的東西本質上不是顯現,而且不是純粹顯現的話,即這樣一種顯現,在其中顯現的東西是顯現這種純粹事件本身。這種就其本身考察的顯現的純粹事件本身,笛卡兒在《指導心智的規則》中仍然是按照傳統方式理解的,他當時用各種各樣不適當的名稱指稱它,其中如“自然之光”這個名稱,而他在《沉思錄》中的突然顯現的直觀中,則在其真正的本質中發現瞭它,他稱之為“我思”。於是在這個問題的範圍內,顯現與存在的關係就被揭示齣來瞭:“我們存在僅僅是因為我們思維。”它的意思是:我們所是的存在以及(在經過懷疑之後繼續存留下來的)任何存在化歸於它的那個存在——因而就是存在整體——,是由顯現獲得存在能力的,是從顯現的能力這種唯一能力獲得存在能力的。這就是以《沉思錄》的問題的語言明確錶達的東西:“我是一種進行思維的事物,這就是說,它的全部本質就是思維。”它的意思就是:存在就居於顯現之中,並且完全溶解於顯現之中。或者還可以說:沒有任何存在本身是不同於顯現的顯現的,沒有任何存在不能被不摺不扣地還原為顯現。
於是我們就被引導到第三條原理。這條原理的錶述使得在它上麵顯示齣一種用語上的二重性,這種二重性在這裏不是語言現象,而是訴諸語言所要談論的事物:一方麵是“麵嚮”,另一方麵是“事物”。“麵嚮”說的是嚮某物接近,是達到某物的可能性,而“事物”則指人們在這種接近中所達到的某物,即在這種接近中可以達到的內容。
當我們對現象學的這個口號進行初步最扼要解釋的時候,我們不可避免地一方麵重又陷入最傳統的問題,另一方麵,我們就放棄瞭,或更確切地說,拋棄瞭在解釋第一條原理時作為本質的知識提供給我們的東西,即建立在將存在還原為顯現的這種基礎之上的顯現與存在的同一性。
這就是矛盾。因為如果可以說存在有事物,即我們應該努力達到的事物本身,而這要沿著某種途徑:通過某種正是達到這些事物的接近的方法,這些事物是目的,即在我們遇到它之前自身已然存在的存在;那麼存在就不再能夠還原為顯現瞭,它不再能從純粹顯現這種事件得到那種使它存在的力量瞭。
顯現的問題當然並沒有因此而被排除,因為在現象學的這個命令中,直接地將我們導緻事物的“麵嚮”,正是顯現本身。惟有這個顯現(它被認為是接近的純粹的可能性),從那時起呈現為起初從屬於我們可以接近的那個東西。這種從屬關係引起嚴重後果,以緻不但接近的可能性僅僅是為瞭達到作為真正目的的事物纔顯現齣來,而且這種接近方法本身是由這個目的決定的。正是所要認識的對象的性質決定適閤於認定它的方法,就是說,最終決定認識的方式本身,錶明這種方式應該是什麼,應該用什麼樣的程序和什麼樣的方法論纔能把握住這個對象,纔能達到該對象本身。於是本體論從屬於現象學的關係被顛倒瞭,因為事物構成唯一的目的,為瞭這個目的纔采用那些接近它的方法,另外還因為這些方法的性質取決於該事物的性質。
但正是在這裏,現象學與本體論關係的這種顛倒導緻一種疑難。因為除非這種事物和我們稱作它的性質的東西從現在起嚮我們顯露齣來——在它的現象中並藉助於顯現——,否則我們關於這個事物的性質以及它藉以決定接近事物的諸方法的方式能知道什麼呢?對於是事物的性質決定達到它的方法的這個斷言,爭辯說:是接近事物的方法造就瞭它的性質,這些方法就是它的性質,是看決定瞭被看東西的視覺性質,是聽決定瞭被聽東西的聽覺性質,是空間決定瞭事物的空間性質,是時間決定瞭事物的時間性質等等,是不適當的。因此,即使有一天排除瞭由本體論給現象學,由需要認識的事物給認識所下的素樸定義,那時仍存在這個由古典思想和現代現象學所設定的他們的二重性的問題,——相反,在從存在到顯現的徹底還原中,這種二重性的問題被消除瞭。
存在與顯現的關聯是在現象重確立的,現象的概念錶示某種顯示著的東西,並因此將兩種含義結閤起來,一方麵是事物、存在,另一方麵是顯示、顯現這種事件。不管事物隻是就它顯示而言纔“存在”,因此不管存在不可抑製地退迴到現象,都不能迴避認識下麵這個問題,即通過變成“現象”而顯示齣來的“某物”是否本身與顯現(甚至是根本與它不同的顯現)就沒有區彆。證明這種詢問的正當性的是這樣一個時間,即在現象中,在不管怎樣的物質世界的現象中通過實例顯現齣來的東西,可以說正是在這個“被發現物”(這個被發現物提供它的現象)之前,在顯現將它安置在顯現著的東西,以現象的名義對我們存在的東西的條件中之前,已經在那裏呈現齣來瞭。
這確實是擺在我們麵前的一個矛盾。存在與顯現的不可避免的分離突然代替瞭從存在嚮顯現的徹底還原。因為存在可以獨立於顯現,如果它在現象中並通過現象對我們呈現之前就以某種方式“存在”(而不管這種方式對我們來說是多麼模糊)。
現象概念本身是通過矛盾而達到的,至少這個概念是含義不明的。在它的世紀含義中,它錶達存在於顯現的原初緊密關係,這個牢固的基礎被第一條原理所確認,現象學曾希望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因為畢竟在某物顯現的時間內,任何批判都無暇實行。人們可以說,“這現象是一種幻覺”,但是由此在現象本身中並沒有改變任何東西,並沒有達到任何東西,隻要它的顯現沒有停止齣現,隻要人們限於這種顯現。
即使現象避免瞭批評,卻並沒有因此避開分析。這種分析所針對的,最初無疑並不是顯現與存在的關聯,而是存在嚮顯現的還原。關於存在的觀念,除去作為顯現本身的可能性,沒有其他可能性。事實上,如果仔細觀察,現象絕不包含從存在的存在嚮顯現的顯現還原的這種徹底性;相反,與它們的關聯同時,並且不管這種聯係多麼緊密,它似乎並不假定至少作為理想可能性的它們的區彆。不是這個以某種方式屬於現象學上的現象的區彆使分析成為必要的嗎?
這種分析在現象中區分齣兩個方麵,一方麵是顯現者,另一方麵是顯現這種事件。換一種說法,現象這個概念是雙重的,同時既是本體的,又是現象學的。從本體的觀點看,現象錶示顯現著的東西,這種桌子,這個句子,這個記憶。但是現象的本體內容,常識在這個名稱下所意指的東西,決沒有窮盡它的概念,除去這種特殊的內容,這個概念還意味著它的現象性,即它顯示齣來這個事實,並且僅僅因此它纔是現象。
現象概念的這種雙重劃分現在所進行到的程度,在它引起的破壞性斷裂中所發生的變化,顯現與存在的原初統一,這些是必須徹底思考的。因為如果現象的內容無限變化而它的現象卻不變,這裏所應涉及的就再也不是現象的內容與它的純粹顯現之間簡單的概念區分瞭。顯現的這種持久性質即使不停地改變,由它顯現的東西仍意味著它們之間的一種性質上的差彆。傳統思想將現象性理解為光——不論它是自然之光,是理性之光,是世界之光,或最終是這個世界本身——,在其中,顯現與顯現者的差彆具有絕對無關緊要的形式,按照笛卡兒在《指導心智的規則》的第一規則裏所說的,在這種情況下,光對於它所照耀的所有東西都是無關緊要的。
但是,如果在現象中內容和它的顯現是不同的,以緻於一方對於另一方是絕對無關緊要的,如果它們每一方都從自己方麵減弱到另一方不再有任何共同之處,那麼它們的統一如何還能夠作為奠定現象的東西而保存在現象之中呢?盡管如此,現象的疑難還是不停地闡明那個現在影響著顯現與存在關係的東西,現象學曾希望建立在這種關係之上。如果內容、事物和存在者,對於顯現來說根本是無關緊要的,它們如何能夠被顯現,被它所固有的顯現的活動帶入到存在中?換句話說,如果存在本身作為現象的內容,不能還原為現象的現象性,它如何能夠從顯現中獲得自己的存在?是現象學的原理,即顯現與所達到的存在的內在聯係,是整個現象學,失去瞭它的路標,偏離瞭方嚮。
隻要顯現以及同時還有被還原為其顯現的存在本身呈現為純粹形式的概念,隻要現象學的根本原則仍處於一種現象學上的根本不確定性之中,情況怎麼會是另一種樣子呢?
如果人們不知道顯現意味著什麼,因此不知道存在——這樣一種存在,它的存在就是顯現——意味著什麼,那麼第一個原理能意味著什麼呢?能把一種什麼樣的意義賦予這種比例關係呢?(這種比例關係將存在與顯現聯結起來,並且變成在這同樣是未知的兩項之間的一種總是捉摸不定的比例。)
同樣,如果“麵嚮”所錶達的嚮事物的接近(這種接近不外就是顯現本身)在這裏仍然完全未被說明,如果人們既不知道事物如何顯現,因此也不知道為瞭把握和認識事物如何纔能達到事物,如果是這樣,如何理解第三條原理呢?關於要知道這些事物是否不同於通嚮它的這種純粹可能性,因此這種可能性是否能夠並且應該另外加以思考,或者相反,是否這些事物與接近的方式隻有並且隻是一種相同的本質,這樣的問題(這是決定由現象性來限定它的存在,甚至將存在還原為現象性的現象學的最後抱負的問題)仍然沒有答案。
同樣的不確定性也存在於第四條原理上。關於還原與給予之間嚴格比例的這種最新錶述,實際上將我們帶到現象學的根源上,帶到第一條原理上,至少是帶到我們所明確錶述過的第一條原理上。因為我們將看到,在現象學含義上所瞭解的還原,不外就是嚮顯現還原。不管這種還原按照一種或大或小的徹底性進行到多麼遠——如 “還原越多,給予越多”這個命題所意味的——也並不僅僅是要說,應當通過將顯現與很久以來思想將它與之混淆起來的東西,即與那個通過它而顯現的東西,區分開來的方法,嚴格限定這種顯現。如果還原的徹底性應該涉及到顯現本身,在這種情況下不應該認為,顯現不是和它在所有這些給定條件中嚮還原顯現的一樣簡單(這些給定條件與顯現的關聯就如同與唯一的單調的呈現方法的關聯一樣),即不應認為它相反地包含並利用一些根本的差異,並且超越這中差異,還包含並利用兩種異質的呈現方式之間的絕對差異(所有那些能夠呈現並且能夠永遠顯露齣來的東西,就是按照這些方式呈現的)。在這種情況下,顯現是不可還原的,它具有一種明確的單義的含義,顯現在它由以構成的純粹現象學的質料中,作為顯現是不同的。惟有考慮到這種質料,考慮到顯現的方式,纔能賦予那些依據於它的命題以一種意義,特彆是賦予現象學的諸原理以一種意義。隻是指嚮純粹現象性這種現象學實體性的意圖,纔能錶明這現象性是否與存在是同質的,是否能夠限定存在,並確定存在。
現在讓我們站到質料現象學的觀點上,以便更嚴格地考察現象學的基本原理。在這種情況下擺在我們麵前的甚至不是這種現象學上不牢靠的不確定性;由於這種不確定性,現象學曾使它的真實對象的內在性質處於模糊之中。相反,産生一種懷疑,正是由於這種不確定性,由於這樣一個事實,即顯現的現實的和具體的現象學樣態沒有被確定下來,某種現象性的概念,即那個首先並且常嚮日常思想呈現,並同時構成傳統哲學最古老而由最缺少批判的前提的概念,即從對世界事物的日常知覺中藉用的現象性概念,纔成為必要的——不是就這種現象性確實存在,即就體驗所特有的形式而言是必要的,而是作為一般顯現結構,因此是每一個現象(不論它是什麼樣的現象)的結構是必要的。世界的顯現與顯現的一般本質的這種災難性的混淆,幾乎敗壞瞭構成西方思想的所有哲學,以緻於於哲學的批判的理智經常從哲學公設的和哲學分析的原理上理解這種混淆。在鬍塞爾的現象學中,第二個原理最廣泛地顯示瞭這種混淆。
這個作為最根本原理提齣地著名原理,在其錶麵簡單性下麵隱藏著一種使這一原理變得矛盾的雙關論點。一方麵,它以明確的方式指嚮普遍性。在直觀這個題目下它所要說的就是,使一切現象和一切經驗,不論是哪個領域的,此外也不管這種現象與這種直觀的特徵是什麼,都成為可能的東西。因此這裏所涉及的是一般的顯現,這是現象的普遍條件,是在其原初的普遍存在的結構中的、在其本質中的現象性,它是以“原初給予的直觀”這個名字被指稱的。
然而另一方麵,在直觀這同一名稱下,所指的是顯現的一種特殊方式,而不再是作為尚未被規定的簡單概念的顯現。直觀在鬍塞爾那裏是指作為“對某物的意識” 的、即作為意嚮的意識的意識結構。當然,從嚴格意義上說,直觀概念所指的隻是已完成的意嚮性,但是,直觀應該將它的變成現象性的、以現象狀態確立的能力歸之於意嚮性本身。這樣地變成現象性,在其中意嚮性通過超越自身而指嚮那個作為它的意嚮關聯物,作為超越對象這樣地被拋擲到它前麵的東西。正是這個對象的超越性,它的相隔一段距離,構成這樣的現象性。
從現象性純概念的這種片麵的定義(然而卻是作為普遍定義提供齣來的)産生齣一種限製,它的意義甚至不是認識論的,然而卻是極其重要的。如果生活的本質不外是原初現象性的本質,如果那個在超越自身的世界之光中,在它的超越性中取得其內容的現象性起初就被排除的化,那甚至就不是象西方哲學最經久的命題所說的:認識具有難以剋服的局限性,並沒有被充分奠基起來;而是我們的生活本身被擱置一邊,被忘記瞭,被遺棄瞭。但是,直觀隻是這種超越性的名字,因此它在本身中包含這對於生活的這種無意識的但是徹底的摒除。
現象學求助於現象,以便能在現象上達到存在本身的這種最後抱負,在這裏不再僅僅遇到上麵已經指齣的睏難與矛盾,而且遭到瞭絕對的失敗。通過將直觀充作整個經驗和整個認識的本源,充作所有那些能為我們存在的東西的本源,現象學展示齣一種顯現,在那裏,存在決不“存在”於它的最初的本質之中:好像它作為這樣一種無限的生命溶化在我們之中,這種生命作為它在自己永恒的自我錶現中的自我産生,不停地將我們提供給我們,並且不停地將我們産生齣來。現象與存在的聯係在直觀中遠沒有建立起來,這種聯係在那裏完全被打斷瞭,以緻於在來自這種聯係的現象中,特彆是在自明性中,存在決不被呈現齣來,也不被提供齣來,相反是被排除瞭,或更準確地說,被取消瞭。因為要求存在在直觀中展現齣來,並且如果可能,在那種已達到的成為自明性的形式中展現齣來,這實際上就是否定與被直觀的東西或可直觀的東西不同的存在的可能,考慮到顯現同樣還有存在從生活中獲得的原初本質,這最終就是否定它的顯然的“實存”。第二個原理,實際上對第一個原理是一種損害。
這種由原理之原理對於作為生活自我錶現而構成顯現本身的最高啓示(I'Archi-Revelation)的東西的排除,首先錶明曆史上現象學的命運,因為曆史上的現象學從來沒有能真正與鬍塞爾現象學的根本前提決裂。正是這一點使海德格爾針對鬍塞爾現象學所提齣的批評變得無效。因為使存在存在的東西,恰好不是在直觀概念之下所理解的顯現,而是不可阻止地逃避直觀,這事實上是一種無休止地追尋,正如海德格爾的批評所錶明的,是一種解釋學,它被賦予的任務從來也不是去發現由疑問的東西,此外也不是去發現並非“存在的意義”的東西,而是去發現使存在存在的那種力量。隻有人們在各式各樣名稱下使之與直觀或與意嚮性對立起來的東西——“此在”,“超越”,“超越自身的真理”——纔是不停地說明這種直觀或這種意嚮性的條件:除去每一種直觀在其中展示齣來的那種超越自身狀態的現象性,任何其他的現象性在其純粹現象學的實在性中都既未被構想,也未被考慮。老實說,關於可感受的現象學質料的可能性(如象自我錶現的可能性)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就其悲愴(pathetigue)本質方麵而言,在任何時候也沒有嚮心智呈現齣來。
在鬍塞爾那裏,他的現象學的主要缺陷,即在它的原理中,特彆是在原理之原理中,缺乏構成現象學主要關心的先驗生活這個事實,我們可以說,一直被它所引起的問題的和研究的係統特徵掩蓋瞭。直觀一度被置於可能存在的一切形式的基礎之上,在這種情況下,一種需要普遍現象學本體論的哲學,就隻能通過對直觀的各式各樣可能形式的詳盡闡明而完成,並且與這些形式相對應,有同樣多類型的自明性,而自明性始終是人們能為每一種直觀的形式,因而為每一個存在領域追求的最完滿的直觀的樣態。對這個宏偉計劃的精心而頑強的追求,由於揭露齣新的直觀形式,而導緻對尚屬未知的存在領域的發現。但是,人類經驗以及它能夠達到的對象領域的這種極大的擴展,是與嚴重的限製並行的。因為熟練地辨認齣和描寫齣的所有這些接近的樣態,正是生活按其本性就要躲避的那些直觀形式。因此,現象學就引起一種對於它想要擴大與解放的東西的純粹否定意義上的“還原”:即對作為奠定在我們自己的生活之中的我們對於存在的關係的還原。
第四條原理的優點,就是它直截瞭當地指明瞭現象學地兩個關鍵概念,並在它們之間建立瞭一種賦予還原以真正肯定意義地比例關係。還原遠不是限製、縮減、省略或“簡化”,還原是開放,是呈現。它呈現什麼?呈現“給與”。因而還原導緻給與、還原的擴展與加深也就是給與的擴展與加深:“還原越多,給與就越多。”這是需要說明的。
還原在1905年和1907年《演講》中第一次齣現時,具有我們已指齣過的本體論-現象學的雙重意義。鬍塞爾在他緻力於“純粹現象”,“現象學意義上的現象”時,並沒有明確區分顯現者與顯現本身。這種意義雙關就改變瞭“絕對給與性”、“給與性本身”(2)概念的原意,它同時錶示給與性與它藉以給與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下,獲取這一類的給與性就成瞭研究的目標。因此,在1905年《演講》中,感覺材料構成這第一種還原導緻的絕對給與性,而所有那些超越這種主觀的無可置疑的顯現的東西,即從這些顯現開始構成的“超越的”對象,則受到一種不確定性的影響,因此通過還原使其失去作用。例如,聽覺印象與視覺印象是確定的,而通過它所指嚮的但實際上並未由它們給予的對象,很可能是不存在的。或更確切地說,直接達到的東西,即純粹現象,是指嚮對象的意識的現象,而不是由意識現象所指嚮東西。
然而人們不可忘記,正是在1905年《演講》中,通過明確指齣作為“處於方式之中的對象”(3)的現象學的對象,而齣現瞭被給與之物與其給與方式的決定性區彆,對象與其方式的區彆,而方式不外就是給與的方式,或給與本身。將確定的內容與那些被懸隔的東西分離開,這隻不過是一種嚮它們藉以給與的方式追溯的手段。這種方式,而且隻有這種方式,能夠錶明這些東西是確定的或不是確定的。盡管現象學還處於本體論的曖昧之中,從還原到給與的這個路程從1905年,從還原齣現時起,就已經走完瞭。
因此,還原的真正意義從來不是本體論的。這裏並不涉及在可靠的內容——例如認識能以之為根據的可靠的內容——與其他被認為可疑的內容之間建立一種劃分。從根本上說,還原是現象學的,而這是由於這樣一種最終的原因,即它與現象學的對象本身有關,與給與的方式有關。然而能夠要求確實性的內容究竟是如何被給與的?而那些不要求確實性的內容又是如何被給與的?在涉及第一種內容時,是在自明性種,並且通過自明性被給與的,在涉及第二種內容時,是在自明性之外,並且獨立於自明性被給與的。從來也不是確定的內容,隻有自明的內容纔能夠作為認識的根據呈現齣來,而隻有那錶明內容是自明的並因此是確定的東西,即自明性本身,纔能做到這一點。這就是需要談論自明性,並且唯有自明性纔是原理的那種意義,這就是原理之原理的意義。
對此這種分析已經反駁道:在這個原理的規定之下,唯一重要的東西即現象學的對象——以及與它一起,得到其原初顯現的確定性並且由此而取得其存在權利的一切本體論上的規定——消失瞭。因為生活的最高啓示從不在自明性的方嚮上呈現,而且也不與自明性相匯閤,而我們所是的作為從這種最高啓示中産生齣來的存在,作為有生命的存在,也同樣缺少自明性。如果鬍塞爾的現象學由於使一切本體論都從屬於先驗的自我,當它需要對這個“自我”的或能夠代替它的東西的“存在”加以限定時,就顯得完全失效瞭,這並不是一種偶然的事件。
在這個原理之原理下原初現象的消失,因此現象學真正對象的消失,迫使我們重新考慮還原,以便賦予它一種新的真正徹底的意義。現象學的諸原理以之為前提的東西,就是純粹的還原,這種還原利用顯現與本體內容的對立(顯現使內容顯示齣來),而最終將顯現變成主體,以便重新認識它是什麼。然而我們剛纔揭示齣,由於這種純粹的還原追求純粹的現象性,而不是將現象性充分地解放齣來,於是就掩蓋瞭它的最原初的能力。如果將純粹還原的工作加以延伸,將它進行到終點,這種徹底的還原就將純粹的顯現本身還原瞭,它將顯現中我們稱作世界的光亮這一麵擱置到一邊,以便揭示齣那樣一個方麵(如果沒有那個方麵,這個可見性的地平綫就永遠不會變成可見的),即揭示齣顯現的先驗外在性在生活的無限悲愴中的自我錶現。惟有一種徹底發揮其還原能力的,將可見性的超越自身的(extatique)有廣延的東西——所有可以想象的給與的直觀和自明性本身以及一切被看成可能的東西都被匯集到那裏——懸隔起來的還原,纔能揭示齣原初的給與,這種原初的給與,通過將生命賦予它自身而使它自己存活。並且它同時賦予它以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一切可能世界,因為世界的給與隻有在生活的自動給與中纔能完成。因此應該將還原按照“最大量”進行到底,以便這種給與按照自己的超齣部分將自己呈現齣來,這種超齣部分作為它的可能性本身屬於它,如果沒有這種超齣部分,任何東西,甚至最平凡的存在物,都不能給與。於是在第四條原理中嚮我們顯示齣一種按照更為奇特的比例關係將現象學的方法與對象聯結起來的特徵,這將第四條原理就是:“還原越多,給與就越多”。
這裏做3點評注是必要的。首先,錶明原初給與的這個“最大量”,並不限於指明古典現象學從前通常忽略瞭的其他現象,即與世界轉嚮我們的側麵不同的另外一個側麵——它不是任何的側麵,任何可以想象的麵貌,而是生活的看不見的本質的非麵貌。在最終重新認識現象的這種兩重性時,並不涉及對於自明性所利用的超越自身的或意嚮的給與方式的增補;這是未被想到的另外的方式,在那裏生活按照它自己的悲愴的情調而收到壓抑。這種新的給與的“最大量”意味著,按照這種方式,給與這種豐富性——它侵襲可見性的每一個超越自身的地平綫——的每一個它者都失去瞭它們的能力。但是在這個地平綫中,所有那些被看見的東西都退迴到未被看見的東西,所有那些真實的東西都退迴到非真實的東西,所有那些被給與的東西都退迴到非給與的東西,因而這裏所有的給與都是點狀的,暫時的,被未充滿的地平綫、未完成的潛在性圍繞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是這樣,它經受著流動、消失,同樣也經受著自負的希望;相反,在觸及到它存在的每一點的、任何地方都不可缺少的生活中,所有的東西都每時每刻完全在那裏,但是這所以可能,隻是因為在生活的這種最終給與中,既沒有概略,也沒有外觀,也沒有充實的地平綫,也沒有將要充實的地平綫的內容,在不可避免的不幸之外和之內沒有任何東西,而這種不幸的現象學材料就是悲愴,這種不幸的模態按照它們始終不可能的豐富內容屬於悲愴。
鬍塞爾認為,通過還原什麼也沒有消失,而是一切都在最高程度的確實性和閤法性上重新找迴來瞭。在他認為是對於世界本身的還原中的被思之物也是如此。在純粹顯現內部起作用,並重新認齣它的二重性,以保持生活的最原初給與的那種徹底還原,能夠顯示齣一種可比較的結果嗎?由於放棄可見東西的領域,即全部可想象的世界,還原不是受一種否定標誌的支配嗎?如果將這種異乎尋常的還原——它排除一切超越性以及所有那些由它給與的東西——進行到底,我們還能說:“還原越多,給與就越多”嗎?
然而這種錶現從來也不能由這個世界,因此也不能由一個存在無産生齣來,如果這種超越自身的錶現不在生活中自我錶現齣來的話,而生活不外就是這種原初的自我錶現。因為世界隻存在於生活中,因為世界隻作為生活的宇宙而“存在”,所以隻能徹底的還原——它在顯現中在內在與超越之間劃齣最終的分界綫——纔能保存那種通過對還原以及還原的條件發生影響而在這個原理中躲避開還原的東西。
因為例如一切看本身都伴有一種“不看”,無此不看,它就看不見任何東西:這是由它本身經常産生的一種內在不幸。此外這就是它為什麼是一種悲愴的看,一種處於願望之中,處於煩惱之中,處於衝動之中並感受到這些的看的原因。關於嚮純粹的內在性徹底還原,應該說,它既沒有忽略,也沒有取消任何東西,而且僅僅是由於還原,還原所放到括號裏的東西纔獲得瞭它們特殊的性質,而看、直觀和自明性本身,決不能闡明這些性質。
但是,甚至不是被看的東西的引起情欲的、醜惡的、令人憎惡的性質,而是看的活動本身,從生活中取得屬於它自己的能力。唯有嚮純粹內在性——鬍塞爾和現代現象學都未理解到這種純粹內在性——的徹底還原,纔完成瞭不失去任何東西的這種許諾,而嚮自明性的還原卻簡直就沒有接觸到生活,並因此沒有接觸到給與本身的原初內容。這就是我的第二點評注。
第三點評注涉及徹底的還原與純粹的還原的關係。純粹的還原,正如經常發生的那樣,首先是在能夠引嚮徹底的路程中齣現的。如果人們想重新認識顯現的二重性,認識顯現中這兩個領域的分界,最終理解它們的關係,理解有限給與性在那個排除一切地平綫,因此排除一切規定的東西之中的基礎,就應該使存在者失去作用,而思考顯現本身。
但是在這裏重要之點是:盡管有瞭第一種還原,純粹的還原還是不能真正完成,如果它局限於自身的話。這是因為,如果它是純粹的,它所離析的顯現就決不能憑本身而存在。當代現象學主要的和最有影響的錯覺就是:相信現象學上被規定為超越自身的由廣延的東西的存在,在有廣延的東西上發現瞭充分的現象學的條件——最終相信,超越在現象學上和本體論上是一種自律的本質。因為還原並沒有象嚮純粹內在性還原那樣進行到底,它要通嚮的那種給與性甚至不是受本質上的有限性支配的:事實上,它沒有給與任何東西,——它本身比所有其他東西都少。這正是因為它並沒有對它本身完成自行給與的原初工作,因為顯現並沒有作為自行顯現而發生,因此並沒有顯現,因為任何其他東西都不能在它上麵顯現。因為顯現的他者,特彆是存在物,隻能就顯現在它上麵顯現而顯現,並且隻能作為這樣的東西而顯現。
但是,它的自行顯現,即曆史上的現象學所依據的那種抽象的顯現,憑本身不可能産生齣來,而這是因為顯現未被按照其固有的因此可以說是內在的可能性思考,因為它總是被理解為與它不同的某種東西的顯現,——而這另一個東西本身作為顯現著的東西的顯現,作為存在物的顯現,與現象性無關。就算是在顯現中顯現齣來的東西首先並且必然是顯現本身,這也是古典現象學從來沒有清楚地領悟到的。古典現象學所限定的主體,即作為自身呈現的現象,還隻是意味一種抽象的顯現,它不能憑本身而存在,它作為這樣的東西,經常求助於它的反麵,求助於本體規定的晦暗的和死的因素。但如果不是因為它正是把存在者當作指導,為什麼古典現象學局限於存在者的顯現,以緻忽略瞭所有那些在涉及顯現時根本上是另外一個層次上的東西呢?
現象學的現象畢竟與希臘人的顯現沒有什麼不同,盡管有一些虛幻的意義被賦予瞭消失在對事物的關係中的所謂主體性。所有擴展到瞭我們的懸隔的對主體性的批評,都是沒有根據的批評:它們充其量隻能指責主體性概念不能很好地思考——例如它隻從本體方麵思考——它們所依靠地顯現,而這種顯現就是世間事物地顯現,它們從來也不思考與此不同的顯現。因此它們仍然囿於它們所批評的東西之中,但並未意識到這一點。正是在這裏,在要求還原的徹底性(它將存在物所固有的現象性懸隔起來)的同時,第四條原理將這條道路引嚮最原初的給與。
第四條原理,是由馬裏翁的問題産生的,但他事後迴顧時對它進行瞭闡明,並且賦予瞭他的革命瞭的意義。將本體論從屬於現象學(這種從屬規定瞭我們的整個分析),這是在鬍塞爾的第五研究的簡要的但是決定性的說明中明確提齣的。被海德格爾經常草率拿來反對他的老師的批評,看上去是靠不住的。確實,鬍塞爾被意嚮分析呈現於他眼前的這些新的現象領域迷住瞭,他常常寜肯將他的注意留給這些對象性,而不是留給在它的意義的普遍性中領會到的存在問題。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這些對象領域的整體,特彆是形式本體論的任何對象的領域,從原則上說,從屬於更高的另一個層次的事例。然而這個事例是現象學的事例:盡管它是以先驗的自我這個不恰當的名稱錶示的,但確實不防礙這個名稱將純粹現象性錶示為這樣的事例。這就是在1912年《觀念》的本文中明確地顯示的東西,在那裏,“奇跡之奇跡”——它被清除瞭在海德格爾那裏不停地受到稱贊的本體論上的關聯——就是“純粹意識”,“尤其是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提齣發對說,主體的“存在”仍是未規定的,以及鬍塞爾式的還原中的“事物”與“為意識之物”之間的區分或者還有形式本體論的任意對象的客觀性仍是未規定的,就再也不夠瞭。對於馬裏翁來說,這裏重要的是提齣這樣的問題,即是否這個“我”被“排除”在存在之外,是否它被安置在“存在之外”(這是這樣一個假定,它足以消除整個海德格爾式的存在問題),就它有什麼樣的最終徹底性奢望。
正是在與海德格爾的直接衝突中——這種衝突貫穿著整部著作,並在第六研究中達到瞭最高潮——為瞭以現象學方式進行思維的一種新形式,或許是為瞭一種新的現象學,完成瞭消除本體論的工作,在《存在與時間》中展開的對實在分析的必然超越,從根本動機上說,有一種本體論的先決條件,關於存在的思想經常是受這種條件製約的。不管此在如何是存在中這種唯一的存在者(關於它,這裏所涉及的是它的存在,並且最終是存在本身),仍然留下一個存在者——由此産生齣一種批評,按照這種批評,“存在的意義不能直接從存在者上顯露齣來,不論這存在者是什麼;存在者,甚至此在,從未隻讓人看齣存在者的存在。”
在經過深思熟慮使存在者不起作用的同時(因為存在者本身與純粹現象性是相異的),關於存在的現象學問題——它經過瞭仔細分析並完全被剋服瞭的諸階段(關於憂慮的分析,關於無的現象的解釋學)就導緻的“存在本身的突然闖入,它的‘聲音’直接將人招來”。在我們看來,正是在這裏,本體論從屬於現象學顯得是不可避免的,從最本質上說,這種從屬意味著現象學本身的更新,以及在將還原進行到底時將超齣一切可以想象的存在的這種給與顯示齣來。
就其現在服從於第四條原理而言,有兩個決定性的特點錶明馬裏翁的問題。首先它涉及由存在嚮存在的要求或呼籲迴溯,這種迴溯經常是在這些最終的分析中被需要並完成的。“要求在先,並産生唯一可能的存在。”“……要求——多於存在”。“此在隻是作為它對呼籲的聽從而暴露給存在,以便由存在變成現場(le site)。”必須“從要求此在的情況齣發,從整體上思考此在”。“這個這裏(là)仍是全麵地由呼籲決定的,既然它隻適閤於響應呼籲。”因此,還原的工作循著這條道路和這種曆史的現象學中的各種不同的形式化——從對象到“我”的意識,從“存在者”到此在,從全部存在者到存在——,它通嚮這些東西隻是為瞭使它本身從屬於某種更本質的,更在前的東西,從屬於要求和呼籲。
可是,這種要求為比它更根本更原初的存在增添瞭什麼呢?存在嚮我們發齣的這種呼喊是什麼呢?如果不是這個事實,即它來臨,它嚮我們顯示齣來,既沒有僞裝,也沒有迂迴,既沒有中介,也沒有拖延,以緻我們不可能避開它的呈現,同樣也不可能避開它直接包含的東西。存在的呼籲,這簡直就是它在我們身上的突然呈現,這是一種重壓,通過它,存在本身嚮我們呈現齣來,同時它也使我們存在。因此,如果沒有啓示——它是絕對者的啓示——的這種輝煌的突現,那就不會有任何東西。
這裏就是這個呼籲問題的獨特、令人驚異的,盡管不能說是令人驚恐的苦惱。事實上,在耐心地證實在最終按照其固有的意義主題化的存在中,隻有呼籲,呼籲藉以壓迫並支配我們的方式,隻有這個事件是重要的之後,在這裏這個問題就突然顛倒瞭。按照他的說法,在後一種場閤偶然發生並且本質化瞭的東西,如同在前一種場閤一樣,恰好不是存在,但也不是它的呼籲:這是另一種呼籲,它與存在的呼籲沒有任何關係,相反它將存在的呼籲消除,以便在它的場所和位置上確立起來並取得支配地位。在理解這種對存在的呼籲的拒絕的意義之前,讓我們看看這種拒絕是如何進行的,它是如何可能的,什麼樣的比存在更高、比它的呼籲更高的事例可能在這裏介入進來,並將它們擯退。
這種事例就是馬裏翁在一種完全新穎的問題中建議作為“反實存的”加以對待的煩惱:這種煩惱作為此在的結構不是鋪設我們進入存在的通路,相反地,這種煩惱的能力就是將我們從一切存在物引開。這是因為,它首先將我們從那個允許所有存在物存在的東西,即存在本身引開。更根本地說,因為存在不停地嚮正在煩惱中的“ 我”發齣的無聲呼籲已不再引起“我”的興趣,“不再嚮它訴說任何東西”,因此就發生瞭這樣的情況,這是具有最大危害和最大反感的非常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我”可以說不為任何東西,任何人存在於那裏瞭。
按照海德格爾的觀點,人們可能懷疑“我—此在”有可能在煩惱之中擺脫存在與它的呼籲。按照實存分析,如果此在本質上是由它與存在的關係構成的,如果它是在存在——由於這個存在它纔與一般存在有關——中的存在物,怎麼能消除這種與存在的關係而卻不消除此在本身呢?我們要注意,正是根據它的最固有的資本,此在纔“在存在的真理中確立起來,——存在的真理,它不外是存在的閃光,光照,藉助於它,此在本身從一開始就被照亮,並在一直被照亮到它的深處。這種照明的閃光就是呼籲。但是為什麼完全被它照亮,並從那時起就被安置在存在的光之中,被安置在存在的“那裏”的此在,竟能夠突然地不可思議地不再是它呢?為此不是需要停止是它所是的東西,即”此—在“嗎?但是這樣一種可能性不是被海德格爾明確地排除瞭嗎?不是簡直與”在那裏存在“,”不能不存在“這樣的此在定義相矛盾嗎?
馬裏翁的極大功績,是力圖在對此在的分析本身中證明此在廢除被認為是按其本質構成此在的那種呼籲的可能性。一方麵,是由存在引起的並完成與呼籲同樣功能的驚奇,這種功能就是“將此在給與預先規定它的東西,而這種東西如無驚奇就不能顯示齣來”,——這種驚奇至少包含著此在偶然給與它但也可能不再給與它的注意。呼籲植根於超越自身的閃光的本質必然性中,植根於存在的真理中,這並不防礙迴答的偶然性,而是以它為前提,況且盡管有這種呼籲,迴答也可能不齣現,這是由於無限的煩惱,事實上對所有呼籲的徹底拒絕可能使我們聯想到的隻是有關煩惱的觀念。另一方麵,我們還可以說明,如果在其最內在的存在上,此在是嚮真理敞開的,因此是嚮存在的呼籲敞開的,那麼給它留下的至少——按照那作為煩惱的另一種錶達—限製無疑是值得的東西——是“一種‘不是自己’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實際上重又“取消存在的呼籲本身”。
這裏所提到的這本讀物除具有獨創性,還顯示齣一種不可否認的批判力。這種批判力就在於將海德格爾思想的一些重要論題反轉過來反對海德格爾,或如果我們願意說的話,就在於提齣一種有關海德格爾思想的新評價。這就是對於不確實性的齣乎意料的和獨特的辯護。確實,這種不確實性的可能性不外就是消除存在的呼籲的可能性,這樣就否認瞭“退迴到存在是我所是的東西的最後可能性”。因此對於日常性的著名分析就翻轉過來瞭。因為,如果在日常的實存中,此在避開瞭它的此在的命運,避開瞭在它的“這裏”中被預定給它的存在,這不就是說,這種命運並不必然是它的,這不就是說,有另一種命運嚮它呈現齣來嗎?
可是,“我—此在”的與傾聽存在的呼籲並對它作齣反應的命運不同的命運的簡單可能性,從根本上動搖瞭《存在與時間》中有關它的本體論定義,它禁止將對於存在的超越自身的關係理解為可想象的這個“此”的本質,理解為能成為一種本質的可能性,因為在它上麵恰好隻能看到其它諸可能性中的一種簡單的可能性。對此在的分析,已不再構造那種培養人的人性的哲學瞭,它將自己限於指齣人的本性的諸種可能性中的一種可能性。
不管這種最後的還原——在其通過存在的呼籲規定我們的存在的這種抱負中使用存在不起作用——多麼背理,在任何情況下它的含義都是明確的,而最後的分析也錶明這一點:在以反實存的方式起作用的煩惱當中,存在的呼籲被取消瞭,這沒有彆的目的,隻是將我們嚮另一種呼籲敞開,或寜肯說,嚮“一切其他可能的呼籲”敞開,或更確切地說,不是嚮另一種呼籲,而是嚮“呼籲本身”敞開。在這裏就是“呼籲的樣式”或是“呼籲的純形式”——因此是“呼籲本身”——取代存在的呼籲。這種取代的原因就是:一切具體的,不論是什麼樣的呼籲,特彆是存在嚮此在提齣的呼籲,作為它自己的可能性,都以一種呼籲的純粹結構為前提,以它的“樣式”或它的“純粹形式”為前提。“在存在要求之前,呼籲作為純粹的呼籲就要求瞭。”還可以說:“存在的要求本身隻當具有這種純形式時纔能呼籲。”
這個界限問題由將存在的呼籲從屬於呼籲的純形式獲得雙重好處:一方麵,並不與它以之為營養的博大思想相矛盾,相反將這種思想——而這特彆涉及實存分析本身 ——容納進一種更宏大的目標中,這目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嚮與在“存在的現象”名義下所包括的那些經驗方式不同的經驗方式敞開著的。另一方麵,正是由於這種(但也是由於所有其他可能的)追溯到所有其他的呼籲,纔避免瞭對存在的呼籲的拒絕——這被解釋為嚮呼籲本身敞開的條件——錶現齣的有些形式化的東西,盡管不能說是未被規定的和空洞的東西。
這樣就違反瞭第四條原理。因為第四條原理把還原推進到極限,依次地將存在物還原為存在,最後還原為存在的呼籲,僅僅是為瞭不將我們導緻某個不確定的X,導緻樣式,導緻純形式、絕對和超驗性——這些東西本身都是以純形式的方式規定的——,而是導緻給與性,導緻它的最極點,導緻原初的顯現。在第四條原理中,一切都是現象學的。同樣還原也是現象學的,因為首先作為純粹的還原,然後作為徹底的還原,它明確地將現象性本身看作主題,而在現象性中,它的現象化的最原初方式,同樣它所導緻的給與性,既不允許當作形式也不允許當作樣式來思考,而僅僅是從這種原初的現象化方式開始進行思考。
馬裏翁的思想首先正是在這條道路上開始並嚮前推近的。因為如果不是為瞭在它上麵指齣首先來臨的東西,即嚮我們襲來的顯現的閃光(這種閃光由於它閃亮而使我們與它同時存在),為什麼用存在的呼籲或存在的要求代替存在呢?現在如果是這種存在的呼籲本身應該被拒絕,以使另外一種的並且是更本質的呼籲的可能性得以展開,那麼這最終的代替想要說明什麼呢?
對於這個問題隻能有一種迴答,這個迴答如下。如果存在的呼籲隻是它的顯現,如果對於這種呼籲來說,選擇與其不同的另一種呼籲是適當的,那麼這樣一種對立隻能意味著是兩種現象性的對立,因此是兩種現象學的對立。它意味著顯現的兩重性,並它錶示一種等級層次。
存在的呼籲是什麼樣現象性的名字?是它的超越自身的真理的名字。正是因為它在這種真理上發現瞭海德格爾式的存在的現象學基礎,這種存在纔可能並應該被批判,纔有一種“被排除在”存在“之外”的意義。萊維納的“屬於上帝的東西”,“不同於存在的東西”,馬裏翁的“在存在之外的東西”,對於存在來說可能意味著它被擯退。這僅僅是因為存在僭取瞭它的名字,因為存在隻體現(特彆是在海德格爾那裏)一種局部的事例。關於這個問題的這種未被想到但卻有決定意義的限定,將本體論從屬於現象學的思想一旦完成這種從屬,就發現瞭它。其呼籲可以被懸擱起來的這種存在的本質,就是世界的現象性,這個存在的有限性就是整個超越自身的地平綫的有限性。
擯退被如此理解的存在(它隻“存在”於對此在的理解中,而這個此在與它相關聯就如同與它所“包含”的東西,如同與“意義”相關聯一樣),隻有對於一種條件纔是可能的,即隻要它在生活的悲愴的本質中的非超越自身的自我顯現,無限地阻礙顯現在世界的地平綫中超越自身的展開。擯退存在隻有以現象學方式纔是可能的。擯退存在隻當在缺少一切超越自身的現象性,並且盡管有這種缺少,某種東西仍然可能,而不是什麼都沒有時纔是可能的,這某種東西,就是生活的最高啓示。 “不同於存在”,意思就是“以另一種方式顯現”。當存在緘默時,唯有生活還在通過其最高啓示“呼籲”,並且能夠“呼籲”。
僅僅因為生活的“呼籲”是以現象學方式規定的,僅僅因為在它的富有情感的肌體上,在激烈的情緒和愛情中,它不像任何其他彆的東西,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像存在者在世界中的展開,也不像存在者的超越自身狀態,——纔可能談論不同於存在呼籲的另一種呼籲。除去生活在我們身上悲愴地闖入之外,除去它的言談之外(言談的詞語是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激情,或我們的愛情)沒有,從來也沒有呼籲的純粹形式。沒有更高的或不同於這種悲愴結構的呼籲結構。
因為呼籲總是確定的。呼籲的規定性是現象學的,每次都在它實有的現象性中耗盡。但是後者永不耗盡。顯現總是重新湧現齣來,而且總是以它自己的方式湧現齣來。在其現象學上具體的實在性的方式中就其所是重新認識這種“方式”,並不是停留在不如呼籲的純粹形式或結構的階段那麼高的一般性階段上。相反,就其經常是按照呼籲和響應的兩極被描述而言,呼籲的結構是從顯現的確定方式藉來這種規定的,在顯現中這種對立是現象性的基本對立,而這種顯現恰正是世界的顯現。取代瞭古典的主體和客體二分法的呼籲和反應這個對子,要求通過排除這種二分法革新我們對存在的關係密,這並不重要:怎麼不看到,它隻是顛倒瞭一種在兩種情況下都被認為是現象性的創造者的關係,即是說事實上保持瞭這種關係。呼籲的結構遠沒有避開存在的呼籲,避開它的暗含的現象學,而是求助於這種現象學,並且正是從它那裏取得它自己的“結構”:超越自身狀態的對立物。
這後者被理解為自由的奠立者,實際上,說明呼籲的特徵的東西,就是它期待並引起一種人們能夠或不能夠給與它的反應。正是在這種反應的自由之上,在接受或拒絕的自由之上,馬裏翁建立起自我—此在“不再將存在的命運當作它的存在的命運來承擔”的最終可能性。
但是錶明生活所能及範圍的特徵,就是它先於所有的反應,而並不從它們期待任何東西,因為在生活的突然湧來中,在生活之流——它貫穿我們,使我們因它並因我們自己而激奮——中沒有任何間隔,沒有一點點後退所必須的距離,可以在那裏謀劃迴答的可能性,肯定與否定的可能性。這種一切退卻,一切反駁的不可能性,這種使自己陷入絕境,所有我們所是的東西都逐點地被瞄準的方式,這就是生活本身每時每刻産生的無休止的、不可避免的、不能減輕的、無偏私的不幸,這就是生活在我們身上造成的創傷,而這就正是我們的主體性本身,正是它將我們造就成有生命的東西。
如果說這裏沒有留下允許我們自行決定或拒絕存在的命運的迴答餘地,這是因為,嚴格地說,不再有呼籲。另一種呼籲,生活的呼籲,處於所有呼籲之外,它不嚮我們提供生活的建議。它已經將我們拋進生活,它壓嚮生活,壓嚮我們,使我們飽受不可抗拒地悲愴之苦。在我們傾聽呼籲時,呼籲已經使我們生活瞭,它的窺伺不外就是生活的聲音,它在我們身上的聲音,這是一種重壓,藉助於它,生活在唯一的並且是同一的給與中,嚮它自身呈現齣來,並將我們給與我們。
這就使得在所有生活著的東西上沒有任何不同於生活的東西,這是一種這樣的生活,即在以下意義上它不是它自己的生活,即它既沒有創造它,也沒有奠定它,也不要求它,但它是它自己的,不可還原地永遠是它自己的,由於同樣的原因:就是說,在它那裏沒有任何東西,沒有任何關於最細微的痕跡的不幸不是由生活本身引起的不幸,沒有任何一點它自己的東西不是生活本身。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我們是由生活産生齣來的,而這種産生是不間斷的,因為在自我錶現——它每時每刻都使我們意識到我們自己——中沒有任何不同於生活本身的自我錶現,即它的最高啓示的東西。
這也是為什麼這個在生活中産生的我,馬裏翁意義上的這個“我”,同樣也是一個“我”,一個“自我”,因為按照一些神秘主義者的奇妙警句,生活“不能少給與 ”,因為它不可能給與任何不同於它本身的,因此不同於自我性的東西,它在它的自我給與中不斷的在自身中以及在所有那些生活著的東西中將這種自我性産生齣來。
在存在之外,不同於存在,(所不同的存在是這樣一種存在,它與存在相關聯,並且隻在這種關係中存在,它隻是對於存在而言纔在“那裏”存在),隻有在基礎現象學條件下,在這種現象學所實行的徹底還原的條件下,纔是可能的。哪一種事例實行這種徹底的還原呢?——這種還原使存在的呼籲不起作用,而且使那種在其存在方麵由這種呼籲而規定的東西不起作用——煩惱,按照馬裏翁賦予其意義上的煩惱。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不是應該嚮煩惱提齣一個問題嗎?這個問題,《還原與給予》的作者曾就鬍塞爾的自我(它在鬍塞爾藉以構成本體論的“行為”本身中擺脫瞭一切本體論)嚮自己提齣過,這個問題就是:關於這個自我仍然能夠自我保持的場所,它居住的場所,總之是它的“存在”的問題。
或者還可以更確切地說,煩惱的還原能力依賴這樣一個事實,即它對一切,對存在本身煩惱,或更確切地說,依賴這樣一個事實,即在它對一切和對存在煩惱時,它並沒有因此而擺脫自己。因為任何煩惱都永遠不能將煩惱從其本身解脫齣來。如果不是在生活中(在那裏生活與自我的聯係是不能解開的),那麼這種煩惱呆在哪裏呢?正是生活的自我給與支撐一切,給與一切,當存在的呼籲沉默時仍將煩惱給與它本身,——因為存在已經解體,而與存在關聯的那個不同於存在的東西也再沒有什麼意義瞭。
“還原越多”:這種對存在和所有的存在者,對所有由它而來或嚮它而去的東西所要求的最終的和徹底的擯退,以它的名義,即以世界的名義說話和呼籲。“給予就越多”:這就是在缺少這種存在和它的呼籲,缺少超越自身的顯現的情況下仍然給與,給與一切——自我給與,生活以及生活中的一切生存者,和宇宙本身——的東西。
如象馬裏翁這樣錶述的第四條原理,提供給現象學的並不是對已經包含在其諸曆史前提中的各種發展的簡單充實。由於它為現象學規定瞭迄今未曾發現的目標和更為遠大的抱負,從而將現象學引嚮一些新的道路。
注釋:
(1)J.—馬裏翁《還原與給予,對鬍塞爾—海德格爾以及現象學的研究》,1990年法文版,第302頁。
(2)鬍塞爾《現象學的觀念》,1970年法文版,第60頁。
(3)鬍塞爾《關於時間的內意識的現象學演講》,1964年法譯本第157頁。
(原載法國《道德與形而上學評論》1991年第1期)
具體描述
讀後感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用戶評價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哈圖書下載中心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