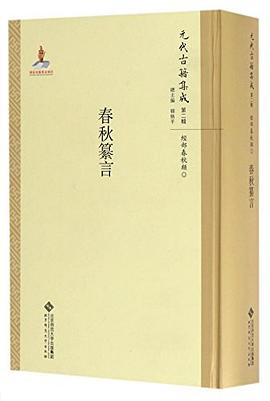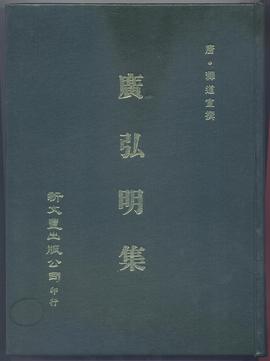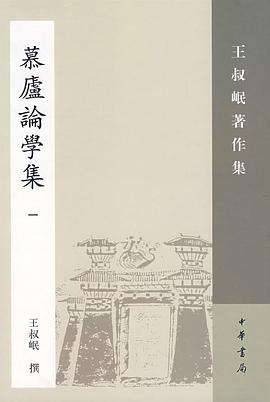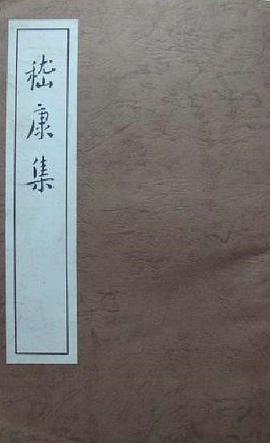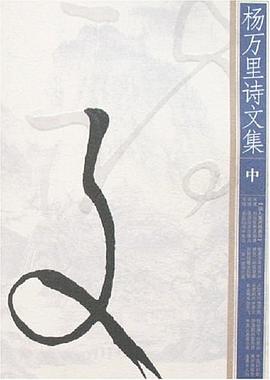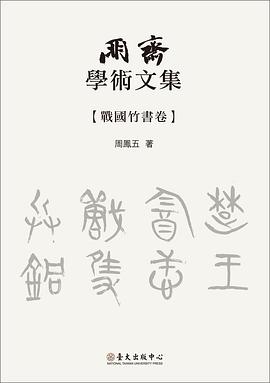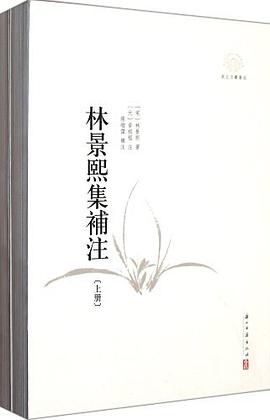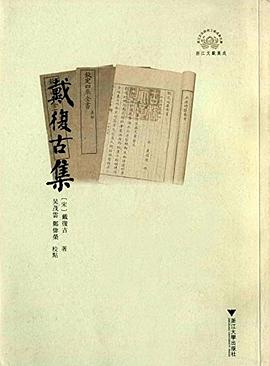具体描述
在改良和革命成为时髦思潮和洪流的时代,王先谦、叶德辉成为反面角色;在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他们因站在改良和革命的对立面而反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时至今日,改良和革命不再时髦,那么,回过头来重新审视王先谦和叶德辉,我们自身的认识视角和评判标准是否需要检讨呢?
一、王先谦事略
晚清的湖南人,说名儒必提及“二王”(王先谦和王闿运),说劣绅必不忘“二麻”(王先谦和叶德辉都是麻脸)。论怎么说,王先谦都榜上有名。
他生于《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年,祖籍江南上元(今南京市),一个桐城派古文家辈出的地方。先祖明代封官岳州府时迁居长沙。后家道衰落,其父王锡光只能课徒自给,并对三岁发蒙的王先谦以“扶世翼教”相期。父卒,十九岁的王先谦“糊口资”,曾三次佐幕于军营,直到1865年中进士。而后二十余年官运亨通,1885年补国子监祭酒,后放江苏学政。其间屡有建言,既想保和局,又不愿辱国体,流露出徘徊于洋务和保守间的两难心境。忽而以劾李连英获直声,又迅速以生病为借口辞官。在长沙筑居葵园,著述自娱,并主讲于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
王先谦崇拜曾国藩,他承袭了曾国藩合汉、宋的学术主张,因而他的大量著作具有既重义理又不轻视考据的特色,《续古文辞类纂》、《东华续录》、《皇清经解续编》、《荀子集解》、《合校水经注》及《汉书补注》都是这类名作。晚年他刻印了《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和《五洲地理图志略》,又赢得了通儒的声誉。
王先谦在做京官的得意岁月里,妻妾所生两男六女皆殇。或许是自怜影只,或许是伤于世变,隐居的王先谦纵情于声色,友人王闿运说他家“门多杂宾”,“人以为侈”。1904年,友人费某三饮于王宅,六十二岁的王先谦身边始终有“雏伶侑酒”,费某将王比为李渔和袁枚,王颇不快。所谓“惟把书度日”的真相被人窥破了。
1898年前后,王先谦认定梁启超等“志在谋逆”,率门生苏舆、叶德辉、宾凤阳等呈递《湘绅公呈》,要求禁遏维新言论,以端学术。1906年,门生梁鼎芬奏请擢用乃师,王以“名心素淡”辞。次年,王因头眩而跌跤,宣布闭户谢客,但仍身膺湖南学务公所议长职,以致颇想取而代之的王闿运背地里讥责其“贪居议长”。1908年,王被礼部聘为礼学馆顾问,被朝廷赏以内阁学士衔,随即又任湖南谘议局筹办处会办。王自称一向不愿干预官事,这些职衔都是怎么也推托不掉的苦差。而旁观者则发现,王先谦好请托有头脸的门生,还受人钱财。
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起,王先谦栽了跟头。湖广总督瑞澂奏劾王领衔电请更换湘抚,有挟饥民压官府之嫌,王被降了五级。王声称从未参与其事,湘籍京官亦联名为他辩诬,未果。这一年,恰是他的虚岁七十寿辰。
辛亥革命后,王先谦改名为“遯”,此字今作“遁”,意为逃避。这很鲜明地表达了他对社会变革的态度和立场。为了逃避,他更换了多处寓所。但他终法逃过疾病,1917年,七十五岁的王先谦死于凉塘寓所。
以上所录为我的旧文,原标题为《晚年改名的王先谦》,载于1996年1月4日《新民晚报》,为该报专栏“名流寻踪”之一种,字数限于一千之内,未注引文出处。记得当时栏目的策划者兼编辑张晓敏先生谓其他名流都是正面形象,从王先谦开始刊出反面人物。
十八年之后,检视相关研究成果,可谓今非昔比,仅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就蔚然壮观。但可信度和深度呢?是否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对王先谦政治思想的评断,从“湖南顽固派之魁首”,到“温和保守派”,再到“处于维新与保守之间的中间地段”;肯定其“有一定的爱国主义”,又“始终停留在封建的水平上”。而对王先谦学术思想和成果的研究,近年更趋之若鹜,既有对王先谦整体学术的探究,也有对其专门著作的研判。其头上的桂冠,已叠加到“一代杰出学人”、“汉学大师”。
这样的研究,是否从相反的方向得出了同样经不起历史检验的结论?限于篇幅,前引小文只是点出了王先谦在历史关键处的选择和自身的矛盾,当然也限于史料,法揭开其谜底。困扰于胸的一些问题,也并未因为近年的相关研究成果而得以解惑。正好借此机会,提出以下问题,以请教于高明。
一、在苦尽甘来、仕途一片光明之际,王先谦为什么决意辞归?
时至王先谦的父亲一辈,家道衰落不堪,其祖父为县学生出身,以课徒为生,“不善治生”;两个伯父或能或败家,家中事唯有其父王锡光担当,终日劳碌,“四壁萧然”。家族振兴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王锡光育有四男四女,本来复兴有望,孰料长子、次子在咸丰年间二十多岁病故,幼子后亦在同治十年(1871)亡故,大女、三女、幺女皆未逾岁而夭折。长子一表人才,学问亦好,早熟顾家,是给诸弟上课的小老师。王先谦一岁出痘疹,成为麻脸。奈的王锡光把宝都押在王先谦身上,三岁发蒙,期许于“扶世翼教”云云,那是功成名就后的追忆,镶嵌在政治正确的光环里。直截了当地说,他实际肩负的是光宗耀祖的重任。
王先谦长相不如其大哥,但资质一流,秀才、举人、进士,都一试而过,且后两项连捷而就。可惜王锡光未及看到儿子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的这一天,在王先谦十九岁时病故,年五十一。
1865年二十三岁中进士,王先谦可谓少年得志,扬眉吐气。而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疑让王先谦深感遗憾。更令人感叹的是,一年之后,王先谦妻子、周寿昌侄女难产,与双胞胎女儿同亡,王先谦在《悼亡诗》中写道:“十日之内,三口并殒。家难之剧,不可为言。”
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仕途畅顺与家庭巨变交织,但并未影响到王先谦的从政志向。即使其弟在1871年病故之后,老母人照料,王先谦续弦后一月,即偕妻子和老母一同北上,“余家老者、幼者、疾者、亲戚贫者,皆率以行”。这表明,此时的王先谦丝毫没有退隐的想法,在仕途起步之际,他也不可能退隐,否则回籍之后的生计以维持。
一大家子居京城不易,王先谦更揪心的是后的恐惧:1874年,两岁四女殇。翌年,长子出生,王先谦喜极而泣,“每怀先泽宜昌后,及到中年转自疑”。未料长男一年后夭亡。1877、1878年,三岁的五女和两岁的七女相继夭折。1879年,一岁的次子再离人世。王先谦如何自处,更难的是如何面对他的老母?我们的历史学家有过同情的理解吗?
与家庭惨剧相对应,王先谦仕途可谓一帆风顺。按照十年一个阶段算,前一个十年从编修升到翰林院侍讲(从正七品升到从四品),后一个十年再到国子监祭酒、学政(仍是从四品),但再往上走,就进入高官行列,起码位至从二品。而外放过学政且在学政位上获得优秀政绩者回籍之后,至少能轻易在省城书院占据一介教席。王先谦是在弹劾“清流”和大太监李连英之后辞职,他既获得了敢言的声誉,又头戴著名学政的光环,此时辞官回籍,等待他的不只是一介教席,而是书院山长。这个位置上的收入远远高过京城的正一品大员。在膝下后、老母为此近乎精神崩溃之际,辞职回乡,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选择吗?
二、在“清流”人物行情见涨之际,与其见解并非南辕北辙的王先谦为什么挺身抨击?与康、梁的对垒,是出于政见的分歧?还是维护自身的利益?
王先谦首次在言路发声,是在1879年,即“清流”人物开始活跃之际。而此前三年,王先谦一方面儿女连续夭折,另一方面本职和兼职政绩优异,皇帝降旨表彰,并赏加四品衔。而王先谦此时上折,称“言路宜防流弊”,指责同僚张佩纶“迹涉朋比”,实为罕见。在最小女儿夭亡之后,王先谦已是“强颜破涕以慰老母,然肝肠寸断矣”。随后王先谦又上一折,痛斥刚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崇厚,其见解则与同样攻击崇厚的“清流”人物并二致。接下来的王先谦奏折,聚焦于洋务弊端、军务废弛,痛斥贪腐,讲求外交策略和船舰机器制造,都切中时弊,他应该是“清流”的同调。那么,他对“清流”的抨击,就不是观点之争,他只是看不惯他们的做派。而家事不幸,让他脾气变坏。
这些言论说明王先谦并非头脑不清的冬烘先生,而是勇气和见识兼而有之的政坛后起之秀。替换崇厚的赴俄交涉大臣曾纪泽看中王先谦,实在是水到渠成之事。但正好王先谦老母去世,他不必再强装笑颜,也失去了光宗耀祖的动力。加上自身身体出现问题,“脑后虚惊晕眩之症”,他婉拒了出使差事。这一时期的王先谦既不保守,也不顽固,而是引人注目、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
王先谦比“清流”幸运,躲过了中法战争之劫。所谓不幸中之万幸,他因母丧而在籍守制。这两年多时间,他在乡编文集,刻史书,初尝文人的乐趣,或许从中发现了度过余生的有效手段。丧期过后,王先谦仍然按期返京,他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三年学政,隐形的收入至少过万,多则三四万。(参见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49页,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有了这笔钱,王先谦后半生不仅衣食忧,而且还可雇人著述、刻书。
1888年,三年学政期满。返京的王先谦再次因上折名震京师,奏折不长,只有三百余字。弹劾的是慈禧身边的红人、太监总管李连英。有关王先谦此举的动因当时就有多种猜测,在我看来,他需要制造一个体面离开官场的事件和借口。
1888年,四十六岁的王先谦返回长沙,随后被乡贤、主张西化的郭嵩焘聘为思贤讲舍的主讲,年薪六百,这收入是京城一品大员的三倍。次年在地方大员力邀下接任城南书院院长。到1894年,转入湖南最著名的岳麓书院,担任山长。在戊戌变法之前,王先谦并没有显露出守旧的态度,相反,他是与时俱进的。后来处于舆论风暴中的长沙时务学堂,其创始人实际上是王先谦,时在1897年。而创办这一新式学堂的动机,是为自己的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培养人才。计划上报后获巡抚陈宝箴批准,陈为学校取名为时务学堂,并改为官办。后来熊希龄任总理,聘请谭嗣同、黄遵宪,梁启超则任中文总教习,都是从这里开始的。王先谦并非西学的门外汉,否则曾纪泽、郭嵩焘没有理由对他频施青眼。对王先谦来说,他对康、梁的敌视,一开始也不是“主义”之争。看着自己的创意被人拿走,变了样,王先谦心情能好吗?当然,同行相轻,都是吃张口饭的教习,少年梁启超在长沙的风靡一时,对年老的王先谦是不是一种威胁呢?
与叶德辉相比,王先谦不太喜欢抛头露面,政治敏感度也远不及叶德辉。在自定年谱中,王先谦坦言,他一开始积极参与湖南的维新运动,听陈宝箴的演讲,自己也登台宣讲,他是维新事业的追随者、参与者。如果不是叶德辉的提醒,他真不知道康、梁的用心:“叶奂彬吏部以学堂教习评语见示,悖逆语连篇累牍,乃知其志在谋逆。”到了这时,王先谦才与叶德辉联手。要说顽固、保守,也是始于此时。
二、叶德辉事略
叶德辉长得不好看。从1915年湖南教育会出版的《经学通诰》所载五十一岁的叶德辉“小景”看,脸上麻子不明显,反而是一口龅牙喧宾夺主。古话说,“丑人多作怪”,说明古人就懂相貌与心理之间的连带关系。今网民说,“不作不死”,更凸显后现代式的调侃和嘲讽。行事高调、言辞犀利的叶德辉或许就是因这两句话而死吧。
仅仅把叶德辉的“作”归结为相貌,当然不靠谱。与王先谦相比,叶德辉的家族连衰落的资格都不具备,这是从科举做官的角度讲。一直到叶德辉中进士为止,上溯六代,一人金榜题名,也一人留下著述。换句话说,论是在祖籍地苏州,还是在迁居地长沙,叶家都算不上耕读之家,其父祖辈的官衔多为捐来的。1911年,叶德辉编族谱,“其笔下的祖上变成了诗书史家,世代簪缨,从未间断。这种闪烁其词的描述,反映出他对家庭背景及出身异常敏感”。
叶家于道光末年避乱而迁长沙,迅速致富。据《郋园先生年谱》,富了之后的叶家“豪侠好义,又喜藏书”。身处民风彪悍的湘中,前者当然有收买人心的用意,后者则疑是向诗书人家靠拢。在那个时代,仅仅有钱是不好意思拿出来炫耀的。
叶德辉生于1864年,号焕彬,又号直山,别号郋园。为长子,两岁“患痘症几殆”,捡回一条命,脸上却落下麻子。四岁发蒙,显露顽童特性,叶德辉回忆,“顾性好侮长,论其为亲、为师,皆侮之”。除了秉性,这也与母亲宠惯有关。一直到十三岁,以读书为天下至苦。十四岁忽然开窍,“试为文,亦颇成章段。持以质前塾师,极称誉”。
1884年,叶德辉娶长沙九芝堂劳家二小姐为妻,显示出叶家财富的激增和在省城富室大户中的地位。次年二十一岁中举。1891年,其妻因生产而患痧症亡,从此叶德辉未再续弦,这殊为罕见。叶德辉后来种种与女优、妓女间的交往纠葛,自然与他的单身相关,不可一概以道德名义骂倒了事。1892年二十八岁中进士,同年中有屠寄、张元济和蔡元培等人。时隔七年才科举如愿,对别人属于正常,自负如叶德辉,一定嫌来得迟缓。名列二甲,不仅未能入翰林院,且朝考后以主事用,签分吏部,这样的龙门更像是鸡肋。高调的叶德辉从此再也不提这一段经历。日后叶德辉以“叶吏部”闻名,在他人是尊称,在他自己则是调侃和嘲讽。中试后约一月,其长子五岁而殇。叶德辉随即乞养回籍,其原因,实必要猜测。仕途开局不利,殇子之痛,都给他提供了回家的理由,家资之富,藏书之丰,当然对嗜书如命的叶德辉更有吸引力。
这一年,叶德辉只有二十八岁。但在长沙,他俨然以湖南第一藏书家自傲,同时也以目录学家、版本家、刻书家称雄。不仅省城的名绅大儒争相交结,就连湘抚也不敢忽视。也是巧合,叶德辉回家不久,新任巡抚竟是江苏同乡、金石版本名家吴大澂,官学名流,“从容游燕”,“谈文考古”,“极一时缟纻之欢”。晚两年接湖南学政篆印的江苏同乡江标也是名士,擅长旧学,且与叶德辉学术兴趣相近。“佣书卖字总寒酸,太息沿门托钵难。散尽千金仍作客,更书札到长安。”这是江标抵任后次月叶德辉赠其扇上的题字,颇堪玩味,自谦自嘲之下,是财富的自雄和对权力的漠视。两位高官既是同乡,又是学问雅人,这时的叶德辉运气真好!为吴大澂鉴画,助江标出书,都是官学交往的佳话,难怪那位同时期同样博学而怪诞的名士王闿运在日记中以“噪妄殊甚”评论叶德辉,实在是嫉妒得可爱有趣。酒桌上称兄道弟,人处恨不得取而代之,凸显出的正是年少得志的叶德辉在湘省学界和政坛的深厚人脉和强大影响力。
1896年,京师刷新政治的氛围浓厚,叶德辉为谋进会典馆而进京活动,该职最后给了另一个湖南人萧文昭,他是康有为保国会成员且懂西学,有人推断这是叶德辉后来“白眼新政的原因之一”。
此次在京逗留并非一所获,首善之区的京剧热,传染给了叶德辉,促使他回湘后投资湘剧,进军娱乐业,成立剧团,培养演员,凭借其雄厚财力、人脉和学术素养,十余年之后,叶德辉成为该领域的龙头老大,其与伶人关系之密切也令人侧目。戊戌维新之后,叶德辉更显浪荡忌,弦歌诗酒终日,湘剧名角侍陪。史家常以此痛斥叶德辉生活腐化,其实有厚污古人之嫌。捧角乃同光间京师流行风尚,自慈禧太后至潘祖荫、翁同龢甚至不得志的李慈铭都热衷于此,王文韶抚湘时所欣赏之红角曾随其入京达半年之久,然后以厚赀遣回。既不违纪,更不犯法,在位者尚且如此,为何要责备闲居在家、自掏腰包消费的叶德辉呢?而他确实是戏曲行家,曾指导日本留学生写出博士论文。至于说他在年近六十带弟子在上海宿娼染疾之类,终究是孤证。当然,叶德辉自称隐身平康北里,意在断绝官方往来的韬晦之举,显然也是自我拔高之词。
叶德辉遭恶评,当然不只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其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的表现,当时就被批为“保守”、“守旧党”、“顽固”。“主义”之争属于人各有志,只要是出于己见,不曲学阿世,应该获得后人的尊重。今日凭情而论,倒是康、梁难逃以学术附会政治之讥。叶德辉与主张维新的新巡抚陈宝箴起初关系并不坏,陈三立与叶德辉甚至走动频繁。梁启超初到长沙,“新旧各派人物一致欢迎,叶德辉亦常与文燕聚首”。江标倡西学,并未影响其与叶德辉的友谊。宗今文学的皮锡瑞与叶德辉也时有过从,尽管有过不快,但友谊得以终生维持。
如前所述,叶德辉与湘省官方一向关系融洽,由此而有“权绅”之目。1898年做《〈轩今语〉评》,向时任学使徐仁铸开战,并非私人之怨、意气之争。徐仁铸在1892年“分校礼闱”,又是江苏宜兴人,既是同乡,又是叶德辉承认的师辈,早有交往,两人实交恶的理由。以叶德辉的脾性,事关“主义”和湘省学子的未来,便不妥协。本来唇枪舌剑,往复辩论,乃叶德辉的强项,用王闿运的话说,“叶焕彬声名甚盛,以能折梁启超也。梁之来此,乃为叶增价耳”。有风度地争论,非叶德辉所擅长,于是趋于人事冲突,《湘绅公呈》便脱离了理性的辩论。连一直忍让的皮锡瑞此时也失去了耐性,斥王先谦和叶德辉为“两麻”。维新失败之后,叶德辉借苏舆之名编《翼教丛编》,名重天下。这一年,叶德辉只有三十四岁。
1900年,革命军兴,反洋教起。奉湘抚俞廉三命,叶德辉编成《觉迷要录》,辟康、梁保皇,斥唐才常党人。朝旨驱外国传教士,叶德辉建议湘抚谨慎从事,并嘱湘潭县令保送传教士出境。由此可见叶德辉并非不了解西方。1903年日本人来湘创办汽船会社,开拓长江航运,得到叶德辉的帮助。叶德辉所宣称的不与官方往来,绝不可信。
叶德辉的厄运于十年后降临。此时的湘抚为广西人岑春蓂,长叶德辉一岁,颇为彪悍,与保守湘绅不洽。1910年春长沙爆发抢米风潮,王先谦和叶德辉的名字都列于湘绅联名驱岑信中,湖广总督、满人瑞澂上奏,称叶德辉“性情狂妄,武断乡曲,包庇倡优,行同赖”。旨下,叶德辉革去功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这样的结局,叶德辉一直喊冤,因为他本人并未具名,系他人冒用。但他也深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承“顽皮,所谓煮不烂也”。因言而招祸。
但叶德辉秉性难改。武昌起义前一月,新任湘抚余格诚、布政使郑孝胥来访,转述瑞澂好意,为其谋开复。叶德辉不领情,竟笑言:“吾辈归田之人,家居异革职,是何足惜?窃恐不出二三年,中原官吏皆革职矣。”此话极具洞察力,不幸而言中。但在湘省大员面前戏言,终令人不快。
进入民国后,各省首脑多为武人出身。叶德辉再口不择言,性命危矣。这一点,连他的日本弟子盐谷温也看了出来,极力劝其东渡。叶德辉不得意地说,革命党里的浙江人章太炎说过,“湖南有叶焕彬,不可不竭加保护。若杀此人,则读书种子绝矣”。1912年,叶德辉因父丧阻挠湘剧艺人前往江岸迎接荣归故里的黄兴,反对将长沙闹市的街道以“黄兴”命名,都是极为危险之举。翌年,反对捐护国寺建女校,被人称为“惯痞”。又作《光复坡子街地名记》广为散发,讽刺当道,遭都督府军政部部长唐才常之子唐蟒逮捕。乘隙逃脱,又得章太炎等说项,躲过一劫。1913年,新任都督汤芗铭有意罗致叶德辉为督府顾问,叶不仅坚拒,且致信湘籍京官,揭露汤督不法行径。此信在报上披露后,汤大怒,发兵抓人。叶逃脱,躲在京、沪。到1914年春,叶德辉以为风头过去,返乡途中,在汉口被密捕,押回长沙。在京湘籍官员出力营救,终得袁世凯援手,很快获释。叶德辉未屈服,星夜赴京,再控汤芗铭,要求政府践行“军民分治”。叶德辉入民国后的言论更趋忌,在于他对民国的言论环境的认识,他不止一次在致友人函中提到民国有“言论自由”。
就在获得人身自由不久,叶德辉被长沙商绅推举为长沙、善化两县总团总,湘岸淮湘公所所长,盐业公会会长。1915年,又被选为湖南教育会会长。再次凸显叶德辉在商、学两界的影响力。同年,因《二十一条》而引发的反日风潮也波及长沙,叶德辉被推为排日会会长,他将自家房舍作为排日会总部,免费提供饭食。当然,这年夏他还被推为筹安会湖南分会会长,据说是为了报答袁世凯的救命之恩。
叶德辉对待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态度,似没有第一手文献可征。此时湖南省长为张敬尧,在湘名声不佳,却很受叶德辉青睐。1920年,叶德辉在自己的照片上题字:“少年科第,为湘劣绅。谤满天下,人故鬼新。贞元进士,庆元党人。自作新耒,颇拟于伦。”自比“贞元进士”,表明其反对白话文的立场;以“庆元党人”自居,则为自己因维护“道学”屡遭迫害而鸣冤。
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风云诡异多变,叶德辉仍口遮拦,1924年,他反对湖南自治,主张取消省宪,被人抢白为“帝制余孽,不配讨论省宪”。1927年,是叶德辉生命的终点。年初,二十九岁的长沙导盲学校校长陈子展为筹款而前往郋园拜访叶德辉,问他是否知道铲除土豪劣绅的宣传,叶德辉答道:“知道的。我是书豪,不是土豪。我是痞绅,不是劣绅。”像是对自己的盖棺定论。这年的三月七日,叶德辉被农协会会员执获,三天后被杀。刑前问自己的书如何处置,答曰放在图书馆里。叶德辉连道三个谢,从容就死。两年后,叶家标价三万欲将藏书卖给长沙中山图书馆,省主席鲁涤平只批了三千元,结果绝大部分书籍被日本人购去。1930年,入藏长沙的叶德辉精品藏书因战火而尽毁。
三、王先谦、叶德辉异同论
王先谦比叶德辉长二十二岁,属于两代人。即使自负诡异如叶德辉,晚年行文仍谦称王先谦的“门下晚生”,坦言:“余田居三十余年,与长沙王阁学太夫子葵园先生过从最密。”此话自然不错,但两人风谊绝非亦师亦友,私下叶德辉并不佩服王先谦的学问并屡有非议。这些非议颇值得追究,从中可了解王先谦做学问的方式和水平,可惜历史学家并未措意,仍然闭眼夸赞王先谦为“大师”云云。
两人的共同点,都是自江苏客居长沙的移民,而祖居地的思想与文化对两人的政治态度和学问取向都有重要影响。王先谦深受桐城派的梅曾亮、管同和中兴名臣曾国藩的影响,其门生陈毅在乃师文集序言中称其“一以姚氏宗旨为归”,“主持正学”,另一门生苏舆亦引此为同调。而1882年,王先谦因母丧回乡守制,刊印的第一本书便是《续古文辞类纂》,王先谦在《例略》中称:“学者将欲杜歧趋,遵正轨,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这既是王先谦的学术取向,也是他的政治取向,学生陈毅和苏舆对其师的评价是准确的,论是强调“正学”,还是赞其“卫道爱国”,都是对其政治和学术“正确”的双重肯定。
但若问王先谦的代表作是什么?恐怕难以回答。“续纂”、“续编”之类的大部头著作难以称之为研究,而“集解”、“集注”之类的汉学类著作又难以确定成之于王先谦一人之手,他在其大部分著作中所起的作用类似于今天的“主编”。
而叶德辉是拿得出过硬的学术专著的,而且都是成于一人之手。只举《书林清话》、《藏书十约》两种,他便以目录学家和藏书家而傲视同侪。故王先谦和叶德辉的文字此次虽编在一书,两人的思想有相同之处,但两人的学术则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要说到两人的不同之处。从家庭背景看,王先谦生于破落的耕读之家,考中进士之前,父亲亡故,“家徒壁立”。叶德辉则出生于富裕的商人之家,家中藏书丰富。从为官经历讲,王先谦在朝二十四年,从编修到祭酒再到江苏学政,四十七岁退出官场,熟知朝廷的教育、文化体制运作,尤其是在江苏学政任上组织编纂《皇清经解续编》,让他通晓集资、组织编写人员从而众手成书的全过程,这种经验疑复制他在长沙的编书、刻书事业里。
王先谦于1888年年末回籍修墓,次年请湖南巡抚代为奏陈开缺,三月获批。而此时的叶德辉则忙于会试,两人正好行进在相反的方向。1892年中进士并辞官返乡之后,叶德辉才与王先谦定交,王先谦极为欣赏叶德辉,说服他加入自己的著述“团队”,并介绍他认识名流黄自元、孔宪教等人。叶德辉遂参与到王先谦所主持的校勘、出版事务中,“逐渐熟悉长沙刻书工匠及刻书工序”。翌年,叶德辉与皮锡瑞也开始交往,交谈中,叶德辉“不甚以二王为然”,而皮锡瑞竟然表示赞同。连王闿运都看不上,王先谦当然不在话下。
第一次见面,叶德辉便以王先谦为第二知己,同时又不甚佩服其学问。王、叶之间,除了学术上的合作,还有生意上的竞争。从1895年起,叶德辉介入出版业,生意迅速扩大,与苏州、上海印书机构都有合作。王先谦对此有何反应?其年谱只字不提,深可玩味。而作为藏书家和学问家,叶德辉的名声也远远超过了王先谦,此时的外国门生,除了一批日本人,还有英国人、德国人。更难得的是,叶德辉没有任何的头衔和教职,“一生不作书院山长,不就学堂监督,亦从不就府县志局之聘”,这并非他没有资格,人招揽,而是他严词坚拒。而王先谦一直在长沙最有名的书院如思贤、城南和岳麓任职——这是他的饭碗。值得注意的是1917年叶德辉给缪荃孙的信中写道:“葵园老人刻书必附以己注,注又未必高,甚或以其族人王先慎、门下苏厚庵之注参入,其人均不知注古书之法,纯乎俞曲园之应课材料。”此话也有话外之音,因为王先谦所注《水经注》、《世说新语》、《汉书》等,大量采用叶德辉的研究成果,再者,叶德辉认为王先谦并未遵守刻书的“古式”。王先谦在自定年谱中绝口不提与叶德辉学术上的往来,而叶德辉晚年所撰回忆则正好相反,极为有趣。如1900年,京城大佬瞿鸿禨商之王先谦,劝叶德辉复出为官,未料王先谦反对:“叶某是吾之行秘书,吾所著书,非经叶某参校,不敢自信。叶去,则吾书不成矣。”半真半假之言,却不乏实相。1917年,王先谦去世,叶德辉在给缪荃孙的信中,还是道出了真话:“田居廿余年,与此公共事讲学,时复参差,然矜而不争,和而不同,实愧古君子之谊。”两人的“不争”和“不同”,更多的是在学术方面。
论世要知人,论人的思想观念也要知人。从政治史的角度看,王先谦、叶德辉疑保守,但并非一直保守,再说保守并不等于顽固和反对;从学术史的角度看,王先谦、叶德辉疑是反对今文学派的,但反对今文学派不等于泥古不化、拒斥西学。在那样一个政治风云变幻不定的时代,王先谦和叶德辉的变与不变,需要详细梳理,多方解读。本书所提供的文本,希望能为这样的梳理和解读提供方便。而了解王先谦和叶德辉的身世、经历和交往,疑有助于对他们思想行为的梳理和解读。
四、版本与校勘
本书“王先谦卷”,除《〈尚书孔传参正〉序》选自光绪三十年虚受堂刊本外,文集选自光绪二十六年刻本《虚受堂文集》,奏议选自光绪三十四年长沙王氏刻本《王先谦自定年谱》,书札选自光绪三十三年刻本《虚受堂书札》。以梅季标点《葵园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6)为校本,偶有参考其他版本者,则随文注出。原文中所有引文都核对了出处并加以校勘。
本书“叶德辉卷”选自《翼教丛编》的篇目据光绪二十四年刻本标点,选自《郋园论学书札》的篇目据光绪二十四年长沙叶氏刻本标点,《藏书十约》据宣统三年长沙叶氏观古堂刻本标点,《经学通诰》据民国四年湖南省教育会活字本标点,选自《郋园北游文存》的篇目据民国十年财政部印刷局活字本标点,选自《郋园山居文录》的篇目据民国十一年长沙叶氏刊本标点,选自《观古堂文外集》的篇目据民国二十一年刻本标点。部分上述文本中未收的序跋从他人文集里辑出标点。另据《叶德辉集》(王逸民主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叶德辉年谱》(王逸明、李璞编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补入6篇文章、54通书札。原文中所有引文都核对了出处并加以校勘。
“王先谦卷”的点校工作由李骛哲先生承担,“叶德辉卷”由黄田先生承担,最后由我汇总核对。感谢他们的不倦努力,为我减轻了工作量。当然,标点和注释中的谬误,理所应当由我一人承担。
最后必须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琬莹女士的联络和督导,我一再拖延而她从未失去耐心,让我深感钦佩并坐立不安。
衷心期待着方家的批评指正。
王维江
2014年12月29日于沪
作者简介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祖籍江苏上元,迁居湖南长沙。1865年中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曾放江苏学政。1888年辞官回籍,主讲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岳麓书院。主持编著《汉书补注》、《荀子集解》、《尚书孔传参正》等,辑选或校刊《东华录》、《东华续录》、《皇清经解续编》、《郡斋读书志》、《合校水经注》等。王氏一生著、编、校、辑、刊刻著作五十余种,计三千二百余卷。
叶德辉(1864—1927),字凤梧,号焕彬,别号园。祖籍江苏苏州,迁居湖南长沙。1892年中进士,分派吏部主事,以乞养回籍,不再复出。以藏书、刻书而名重一时,并以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而载入史册。戊戌变法时反对湖南学政徐仁铸和在长沙时务学堂任教的梁启超,政变后编《翼教丛编》、《觉迷要录》,由此被指为“旧派”、“劣绅”。1927年,为湖南农协所杀。治学广博有趣,代表作有《书林清话》、《藏书十约》、《园读书志》等。
王维江,复旦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汉堡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有《王先谦与“清流”:晚清的政治与学术》(德文版,东亚出版社,2008年)、《“清流”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上海的德国文化地图》(合著,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1年)。译有《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合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合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1945—1968年日本与西德的“历史清算”》(合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
李骛哲,云南昆明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专门史博士研究生。
黄田,江西宜春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
目录信息
文集
科举论上
科举论下
海军论
工商论
天地论
群论
《国史河渠志》序
《云南乡试录》后序
《江西乡试录》前序
《浙江乡试录》后序
《东华录》序
《东华续录》跋
《天禄琳琅》跋
《皇清经解续编》序
《续古文辞类纂》序
《郡斋读书志》序
《魏郑公谏录》后序
《曾子辑注》序
《苇野诗文合钞》序
衡阳《陈氏谱》序
《悔全堂诗集》序
《寿梅山房诗存》序
《磨绮室诗存》序
《坦园诗存》序
《溶川诗钞》序
《庞濬卿时义》序
《王氏塾课初编》序
《孙渔笙时文》序
《读均轩馆赋偶存》序
《国朝试律诗钞》序
《师竹吟馆诗存》序
《试韵举隅》序
书《彭烈妇行状》后
书苏东坡《论范增》后
《刘氏传忠录》序
宋《刘屏山先生文集》序
《紫石泉山房文集》序
《集句训子诗》序
《四书文豳》序
《姓略》序
重刊《儒门法语》序
《杨丹山试艺》序
《劫余存》序
《张乳伯文集》序
汲古阁《说文校勘记》序
《宗子相先生诗集》序
行素堂汇刻《经学丛书》序
《密庵自治官书》序
重修《泰兴县志》序
《堵文忠公集》序
《频罗庵遗集》序
《金忠节公集》序代
重刊《新安志》序代
《留云山馆文钞》序
《思益堂集》序
《江左制义辑存》序
《南菁书院丛书》序
《磵东诗钞》序
《麋园诗钞》序
《诗余偶钞》序
《大学章句质疑》后序
《中庸章句质疑》序
重刊《世说新语》序
《周易集解纂疏》序
《荀子集解》序
《方言》序
《方言》序代
《查毅斋阐道集》后序代
《读礼丛钞》序
《盐铁论》后序
《祁氏三世诗文集》序
《晚香堂赋钞》序
《合校水经注》序
《滇诗重光集》序
《五塘诗草》序
《畹兰斋文集》序
《养知书屋遗集》序
重刊《风宪约》序代
吴中丞《游桃源洞记》书后
《柈湖文集》序
浏阳《娄氏族谱》序
《心言》序
重刊《南华九老会唱和诗谱》序
《庄子集释》序
《释名疏证补》序
顾竹侯所箸书序
《葵园校士录存》序
《韩非子集解》序
《汉书补注》序
《约章分类辑要》序
《丹溪全书》序
重刊《景教碑文纪事考正》序
重刊《景教碑文纪事考正》后序
《日本源流考》序
师范馆讲义序
《舆诵录存》序
三田《李氏谱》序
宋梓侪诗集序
送何镜海之官广东序
送王夔石尚书序
赠杨性农先生重宴鹿鸣序
赠赖子佩大令之任邵阳序
杨云桥先生八十寿序
吏部左侍郎杨公传
河南汝州知州杨公传
梁刚节公传
黄忠壮公传
蒋果敏公家传
赠知府衔署惠州海防通判高明县知县许公家传
皮先生家传
龙孝子传
张节母李孺人家传
周宜人传
章贞女传
故明督师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忠正公传
刘观察传
欧阳磵东先生传
毛青垣先生传
始祖子泉公传
五世祖若水公传
先伯兄会廷府君行状
先仲兄敬吾府君行状
季弟礼吾行状
金匮华氏新义庄记代
向家冲先墓记
仙人市先墓记
重修寄园记
永慕庐记
江阴学使院续刻题名记
南菁沙田记
怀翼草庐记
捐建福尹二公祠记
水月禅林记
慕莱堂记
珠晖塔记
枫山致悫飨堂记
定香亭图记代
祭张树人文
祭阎潜邱先生文
春秋二仲祭阎先生文
湖南省城开北门外新河祭水土神文代
告大兄墓文
丁次谷司马寿颂
郭筠仙先生西法画像序赞
《十家四六文钞》序
《徐骑省集》序代
《骈文类纂》序例
仁寿堂记
《边疆行役图》记
《尚书孔传参正》序
奏议
言路宜防流弊请旨饬谕以肃政体折
徐之铭情罪重大请严旨查办折
敬陈管见折
通饬各省选将练兵折代
会议事宜筹虑宜周折
东三省防务宜特派大员督办兼辖地方以一事权折
会议防俄未尽事宜折
招商局关系紧要宜加整顿折
各口及外国请设立公司招商运货出洋片
太监李连英招摇请旨惩戒折
书札
与缪筱珊
又与筱珊
又与筱珊
复萧敬甫
复某君
与曾袭侯
与翁叔平前辈
致左侯相
致刘岘庄制军
与吴筱轩军门
与某君
与陈子元观察
复钱晋甫观察
复毕永年
复吴生学兢
致陈右铭中丞
再致陈中丞
复洪教谕
三致陈中丞
四致陈中丞
与徐学使仁铸
致俞中丞
复日本宗方北平
复周榕湖
复杨世兄彦深
与但方伯
与蔡伯浩观察
再与蔡观察
三与蔡观察
与俞中丞
复万伯任
致朱莼卿太守
致俞中丞
同冯莘垞给谏与陆中丞
与张雨珊
与张孝达制府
与张筱浦廉访
再与张廉访
三与张廉访
致庞中丞
四与张廉访
五与张廉访
六与张廉访
七与张廉访
八与张廉访
与瞿羹若教谕
致张冶秋尚书
复黄性田舍人
与陈佩蘅
与吴自修学使
复岑中丞
与朵生书
与王实丞书
复阎季蓉书
上胡筱泉师启
与梁武卿书
王先谦年谱简编
叶德辉卷
文集
《孟子刘熙注》叙
《淮南万毕术》序
校辑《鬻子》序
光绪壬辰科叶氏考卷
辑《郭氏玄中记》序
《颜氏学记》后跋
《瑞应图记》叙
《轩今语》评
《明辨录》序
正界篇
《长兴学记》驳义
《读西学书法》书后
非《幼学通议》
《阮氏三家诗补遗》叙
《六艺论疏证》序
新刊《华阳陶隐居内传》序
刊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序
《金陵百咏》叙
《曝书亭删余词》序
《古今夏时表》序
《觉迷要录》叙
重刊《辛丑消夏记》序
重刊《宋真宗御注四十二章经》序
重刊《宋司马温公七国象棋》叙
重刊宋本《南岳集》序
《消夏百一诗》序
《消夏百一诗》后序
《佛说十八泥犁经》序
重刊《诗坛点将录》序
《桧门观剧绝句》序
《宋忠定赵周王别录》序
《两汉名人印考》序
《曲中九友诗》序
《曲中九友诗》后序
重刊《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序
重刊《避暑录话》序
《宋赵忠定奏议》序
重刻《燕兰小谱》序
《游艺卮言》序
藏书十约
《书林清话》叙
《广切音法》序
《佛遗教经章句》序
《陆军新书》序
叶德辉启事
光复坡子街地名记
答孔道会宣言书
《光复军志》序
《观古堂藏书目》序及序例
经学通诰
省教育会长宣言
《顾亭林先生年谱》序
龙启瑞《古韵通说》书后
《星命真原》序
《常熟顾氏小石山房佚存书目》序
《岁寒居士制艺》序
《大鹤山人遗书》序
与诸桥辙次笔谈
《续书堂明稗类钞》序
《韩诗外传疏证》序
《联绵字典》序
重印《胡石查手拓观古阁藏泉》序
《龚定庵年谱外纪》序
《说苑集证》序
《新序集证》序
《洗冤录参考》序
《墨子正义》序
《三秀草堂印谱》序
《曲学概论》序
重刊《八指头陀诗》序
重印钱曾《述古堂影宋抄本说文系传》跋
广《说文统系图》说
郋园字义说
《明万历丙辰进士履历》跋
《明万历丙辰己未天启壬戌三科进士履历》总跋
《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序
《前巷派叶巷支谱》序
《瞿文慎诗选》书后
张文达《退思轩诗集》书后
《天放楼诗钞》序
《虚受堂文集》后序
《虚受堂诗集》后序
重刊《助字辨略》序
《于飞经》序及自传
戏拟大菊国大总统罗雪逊位新选大总统曾运诏
戏拟大菊国新选大总统曾运答前总统罗雪逊位诏书
戏拟大菊国大总统就职大赦天下令
戏拟大百谷国大皇帝贺大菊国新选大总统就职国书
戏拟花国大总统贺大菊国大总统就职国书
戏拟百草百木百果百药四藩部贺大菊国大总统就职表
郋园六十自叙
书札
致钱康荣
致叶昌炽
与邵阳石醉六书
致熊希龄
致石陶钧
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
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
答南学会皮孝廉书
与戴宣翘校官书
答人书
与段伯猷茂才书
与俞恪士观察书
答罗敬则大令书
与罗敬则大令书
明教
西医论
致俞廉三
致吴庆坻
再致吴庆坻
与缪荃孙
再与缪荃孙
三与缪荃孙
四与缪荃孙
五与缪荃孙
六与缪荃孙
七与缪荃孙
八与缪荃孙
九与缪荃孙
十与缪荃孙
十一与缪荃孙
十二与缪荃孙
十三与缪荃孙
十四与缪荃孙
十五与缪荃孙
十六与缪荃孙
十七与缪荃孙
十八与缪荃孙
十九与缪荃孙
二十与缪荃孙
二十一与缪荃孙
二十二与缪荃孙
二十三与缪荃孙
二十四与缪荃孙
二十五与缪荃孙
致章士钊
二十六与缪荃孙
二十七与缪荃孙
二十八与缪荃孙
二十九与缪荃孙
致刘承幹
三十与缪荃孙
三十一与缪荃孙
再致刘承幹
三致刘承幹
致夏敬观
再致夏敬观
三致夏敬观
四致刘承幹
四致夏敬观
五致刘承幹
五致夏敬观
六致夏敬观
七致夏敬观
八致夏敬观
九致夏敬观
致瞿启甲
与舒贻上论星命书
再与舒贻上论星命书
三与舒贻上论星命书
四与舒贻上论星命书
致王秉恩
与瞿良士借印四部宋元善本书启
与张鞠生同年论借印《四部丛刊》书
与日本白岩龙平借印宋本书启
与日本松崎鹤雄论文字源流书
答松崎鹤雄问钟鼎彝器文字书
与日本后藤朝太郎论古篆书
与吴景州论刻印书
叶德辉年谱简编
· · · · · · (收起)
读后感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用户评价
这套书简直是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大门的钥匙。我一拿到手,就被它厚重的装帧和典雅的排版吸引住了。每一位思想家的思想脉络都被梳理得井井有条,从他们的早期探索到晚年的成熟体系,那种层层递进的感觉非常棒。读起来,仿佛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激荡与挣扎,他们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对社会改革的迫切呼吁,都深深地烙印在字里行间。特别是对于那些经常在历史课本上匆匆略过的名字,这套书给了他们丰满的血肉和立体的思考过程。我尤其喜欢其中对一些关键概念的深入剖析,比如“救亡图存”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物思想中的演变,那种细致入微的考据和独到见解,让人不得不佩服编纂者的学识与功力。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记录了思想,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观察和理解现代中国转型的独特视角。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读完其中几位核心人物的部分,但每一次合上书本,都会有一种心满意足的充实感,仿佛自己也参与了一场深刻的精神对话。
评分这套文库的选材范围之广,远超我的预期。我原本以为它会集中于几个耳熟能详的“大咖”,但惊喜地发现,许多在主流叙事中相对边缘化,但对特定领域(比如法律思想、教育改革、甚至早期科学思潮引入)有独特贡献的思想者,也被纳入其中。这种“补遗”和“重估”的价值,对于真正想建立一个完整现代思想图谱的人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我特别留意了其中关于早期留学群体回国后的思想交锋,那种“西学为用”与“中学为体”的争论,在书中有极其细致的文献支持。它不是简单地罗列观点,而是通过引用当时的通信、日记,还原了这些争论的真实语境和情感张力。读完之后,我对中国近代的思想转型,有了一种更加立体、去神化的理解,知道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宏大叙事,而是无数个体艰难摸索的结果。
评分说实话,最初我对这套书抱有保留态度,毕竟“思想家文库”听起来就容易陷入艰深晦涩的学术泥潭。然而,实际阅读体验却出乎我的意料。它的编排逻辑非常人性化,不再是简单的年代排序,而是根据思想的核心主题进行了巧妙的组织。比如,关于“国民性改造”的讨论,不同人物的观点被放在一起进行对比,那种思想的碰撞和交锋,简直比看精彩的辩论赛还要引人入胜。作者的注释系统做得极其到位,对于那些晦涩的古籍引用或者当时的政治背景,都有清晰的注解,极大地降低了阅读门槛。我发现自己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地去追问:“如果我是他,在那个环境下我会怎么想?”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让枯燥的历史文献焕发出了鲜活的生命力。我甚至开始将书中的观点带入到对当下社会现象的思考中,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正是优秀思想著作的魅力所在。
评分我必须承认,这套书的阅读过程是一场智力上的马拉松,但绝对是值得的。它没有采取那种歌颂式的叙事口吻,而是非常公允地呈现了每一位思想家思想中的局限性、矛盾点,乃至他们后期的自我修正。这种不回避矛盾的严肃态度,让整套书的学术品格非常高。特别是其中收录的几篇手稿的影印件,虽然辨认起来需要耐心,但那种亲手触摸历史的质感,是任何电子版或转录文本都无法比拟的。我发现,很多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社会概念,在他们那个时代是需要用生命去论证和捍卫的。这种厚重感,让人在阅读时必须放慢节奏,反复咀嚼每一个词语背后的重量。它不是一本能让人快速扫过的小册子,而是需要你沉下心来,用一杯好茶、一个安静的下午去细细品味的珍藏之作。
评分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套书给我的感受,那就是“启发性”。它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将那些原本只存在于专业研究领域内的珍贵文本,以一种相对易懂且具有强大思想穿透力的方式呈现给了普通读者。我最喜欢的一点是,它不仅仅是展示了“他们想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他们是如何思考的”。那种严密的逻辑推演,对既有观念的质疑,以及面对时代困境时所展现出的巨大精神能量,是极具感染力的。看完一些关于社会改良派的文章后,你会觉得自己的思维框架都被拓宽了,对当下的问题也会多出几层历史维度的审视。这已经超越了一般历史读物的范畴,更像是一本关于如何进行高质量思考的教材。每次在工作或学习中遇到瓶颈时,翻开其中任何一卷,总能找到一丝灵感,仿佛与那些伟大的头脑进行了一次跨越世纪的会晤。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wenda123.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目录大全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