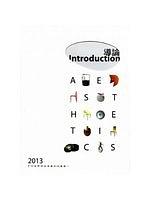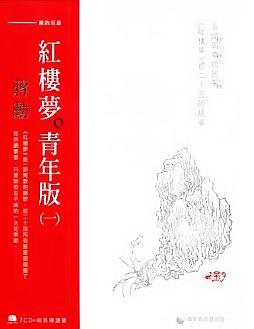具体描述
帶著季節所有的芬芳,日光、雨露、土地、雲和風,都在畫裡
★ 蔣勳池上駐村油畫創作全收錄,縱谷之美盡收眼底
★ 精美印製,限量發行,具收藏價值的油畫藝術之作
我要畫池上了,好像心裡忽然有一種篤定
每當日頭翻過海岸山脈,天光大亮時,他就走進佈置簡約的畫室,站在畫布前,想大波池沒有日光時的寧靜,想水渠裡錚錚淙淙的水聲,想春天苦楝散發的香氣,想相連至天邊的搖曳稻浪;雲水天影、錚淙流水、土地芬芳……蔣勳用顏料一點一滴地累積池上記憶,縱谷之美,在畫布上留下永恆。
「我好像只想畫一張畫,畫裡重疊著縱谷不同季節的景象,春夏秋冬,空白的畫布一次一次改換,彷彿想留住時間和歲月。」—蔣勳
作者简介
蔣勳
福建長樂人,一九四七年生於西安,成長於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藝術研究所畢業,一九七二年負笈法國巴黎大學藝術研究所。曾任《雄獅》美術月刊主編、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聯合文學》社長。
多年來以文、以畫闡釋生活之美與生命之好。寫作小說、散文、詩、藝術史,以及美學論述作品等,深入淺出引領人們進入美的殿堂,並多次舉辦畫展,深獲各界好評。著有散文《池上日記》《捨得,捨不得─帶著金剛經旅行》《肉身供養》《此生─肉身覺醒》《此時眾生》《微塵眾》《少年台灣》等;藝術論述《新編美的曙光》《美的沉思》《天地有大美》《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卷》等;詩作《少年中國》《母親》《多情應笑我》《祝福》《眼前即是如畫的江山》等;小說《新傳說》《情不自禁》《寫給Ly's M》;有聲書《孤獨六講有聲書》;畫冊《池上印象》等。
目录信息
蔣勳‧池上‧台灣好
◎柯文昌(台灣好基金會董事長)
我是在屏東潮州成長的「莊腳囝仔」。年輕時,我在美商公司做事,因為工作的需要,跑遍全世界。不管在哪個城市,晚上睡覺時,眼睛一閉,首先浮上眼前的經常是綠油油的水稻田,和一張張台灣莊腳人質樸、樂天、認命的臉孔。中年以後,我開始有了很難跟在都會成長的家人說明白的鄉愁。
二○○八年,長年禮佛修行,經常提醒我要佈施的母親在高齡九十三歲時於午睡中往生。我想起母親要我「利益眾生」的期待,體認到時間的無情,對台灣的掛念和關心不能再空談,第二年的春分我邀了蔣勳、殷允芃和徐璐等好友,成立「台灣好基金會」。我們一致認為要台灣好,要從鄉鎮做起。東部資源較少,我們決定從台東著手。我們創辦鐵花村,讓原住民青年可以在故鄉高歌。莫拉克颱風後,「台灣好」全力投入嘉蘭村的復建。後來我們也在苗栗倡導小學生種菜,吃有機午餐的「神農計畫」;在我故鄉潮洲的小學推動「潮書院」。但,我們用力最深的是池上。
一百七十五公頃的美麗稻田,有機耕種的農友讓人感動敬佩,我們希望透過藝文活動為這個稻香的村莊注入人文氣息。七年來,「台灣好」邀請許多藝術家造訪,與鄉民互動。年年舉辦的「池上秋收藝術節」已經成為許多池上人家廣邀親友歡聚的節慶。二○○九年,陳冠宇在稻田中鋼琴演奏的照片上了《時代》雜誌網站。二〇一三年,我委託林懷民以池上為題材編作《稻禾》。雲門帶著這個舞作巡迴歐美各國;《紐約時報》用半版篇幅刊登舞者在稻浪前起舞的畫面,池上的朋友奔相走告,引以為傲。
三年前,我提出「池上藝術村」的構想,馬上得到蔣勳熱情的擁抱,並且自願擔任總顧問及首位駐村藝術家。我的好朋友復華投信董事長杜俊雄也毫無保留地支持,承諾以十年的獨家贊助實現這個夢想。這些能量催生了「池上藝術村」。
我們在池上老街到處走看,蔣勳一眼就挑上了大埔村池上國中一間閒置的老宿舍。他說「這老房子跟我記憶中小時候住的宿舍很像。」池上藝術村的第一棟房子就這麼定下來了。我們只做最小的整修,保留了老宿舍的感覺,也把旁邊另一個房間闢為畫室。蔣勳就在前年十月正式開始駐村生活。
長期駐村的蔣勳已經成為池上的文化風景。每次到池上找他,和他一起在村裡逛,會不停聽到「蔣老師好!」的問候。鄰居們都很寵他,隨時送來自種的水果和特別的蔬菜。蔣勳天天畫畫,天天寫作。我不時會收到他傳來的簡訊或者照 片,有些是他在池上的所見所聞與心情感受,有些是他隨手拍下的天、地、山、雲、綠苗、稻穗……,全然地放鬆,讓我羨慕。
我不斷在聯合副刊讀到他的「池上日記」,因此認識了我沒注意到的池上景觀和池上的朋友。我也曾多次到他的畫室,欣賞創作中和已完成的畫作。駐村後,他的畫有了不同的風格和氣勢,在畫中都可以呼吸到池上鮮美的空氣,感受到池上多彩的四時變化;我經常清晨去運動的大坡池,在他畫中也活了起來。蔣勳告訴我,以前很少畫大尺寸的畫,可是在池上寬闊的天地裡,忍不住畫了好幾幅大畫。他說:「我們真正的老師其實就是大自然,不是技術的學習,而是心靈的學習。」
在大美的池上,蔣勳把心中的感動淋漓暢快地寫出來,畫出來;一本讓人心曠神怡的《池上日記》,二十九幅令人凝神讚嘆的畫作。感謝蔣勳過去一年多為池上創作出如此豐美的作品。愛台灣是要用雙腳一步一步去認識它,用文字一句一句去歌詠它,用畫筆、色彩一筆一筆去描繪它,使得任何人只要一說起我們的家園,都會讚聲:台灣好!
寧靜致遠的風景
◎阮慶岳(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教授)
一九八九年在敦煌藝術中心發表首次個展,相隔七年後的一九九六年,蔣勳推出了第二次個展,並開始他爾後的二十年間,大約以兩年為期的持續創作╱發表週期。整體回顧觀看,蔣勳的畫作一直圍繞著山水、花與人物╱身體,這三個看似互不相干的主題間移走尋思,雖然書法、詩作與對於宗教的企望,也穿梭其間做牽引,但若歸根要細究的話,依舊是落在山水、花與人物╱身體,三者內隱意涵的分合辯證上。
這三個主題的創作手法與軸線,不管在技法、美學,與其中所透露的藝術觀,確實有其各自分歧的源處,尤其是油畫與水墨的並列同行,分別對映了東西繪畫的兩種主要藝術創作脈絡,也顯現蔣勳創作背景的多元共存特質。
若是以最近(二○一三年)在「谷公館」畫廊展出的《春分》,以及今年(二○一六年)在台東美術館推出的大型個展《池上日記》系列畫作,來做近期的觀看與比較,依舊可以見到如上述在創作主體與技法脈流上,對於過往自我風格的承續,然而整體的濃郁厚實感加大,在筆法與意旨的輕╱重、濃╱淡之間,益發堅定也分明,顯現出作品的堅實成熟,以及風格揮灑的自信自如。
在近期的這些作品裡,值得注意的變奏轉變,首先是《春分》裡,最是耀目的四件聯作〈夏至〉、〈白露〉、〈春分〉與〈立秋〉,有著異於往昔的獨特態勢。這四件大小接近、尺寸卻各異的油畫作品,脫離了先前以具象與畫意為主的風格,展現蔣勳過往少見的抽象畫風,尤其其中的〈白露〉與〈春分〉,顯露在油畫裡揉合水墨皴法的意圖,令人期待其後續可能。
也就是說,將山水畫的皴法及墨色,做為處理量體與畫面分割的美學手法,輕巧也不露跡痕地移轉到油畫中,確實是令人目光一亮的轉折。這兩件介於抽象與具象間的油畫作品,不僅有著些許蔣勳形容他所喜歡的:范寬的挺拔大器、郭熙的婉轉迷霧,與李唐的谿壑肌理,也同時化解了蔣勳過往顯得分歧的繪畫多元個性,將之轉化成合一的嶄新語言可能。
這樣的試探與前行,在《池上日記》的系列裡,得到更完整的呈現。這批以池上做為現實底蘊的畫作,其中幾幅令人矚目的大尺度作品,立刻展現創作者的氣度與企圖。〈野燒〉與〈雲淡風輕〉可做為其中的代表,畫面裡天地視野遼闊、事物肌理分明,對於其中扮演視覺中心的山脈,尤其有著特別引人的蓄意處理。
相對於《春分》裡的抽象畫風,《池上日記》系列裡的山脈,相對有著回歸寫實的跡象。然而若是細看,同樣渾活的量塊與筆觸,依舊是埋藏在整體輪廓的寫實山體裡,像是騷動而不安的生命力道,永遠蠢蠢地欲動待發。這樣勁道鮮活的筆觸與量體風格,同樣可以在其他更顯靜態收斂的作品中見到,譬如〈薑花〉與〈荷花〉裡面的妖嬈葉脈,或是地景與林木枝幹的構圖處理上,都有著相同的塊體跡痕,應該已然是蔣勳的一個印記了。
其他作品則延續著蔣勳整體畫風裡,一貫具有的寧靜祥和的恆久感。相對於天地顯現的有情寬慰,山脈的處理則宛如人間多變,以及因此的必須渾厚沉重,更藉此顯得其他生者(人物、花木與貓)的輕盈飄渺,彷彿生命一如盛開的繁花,皆有著瞬間燦爛的宿命哀悼與感傷。
這樣對人間依舊回眸的不捨心境,在〈林木深處〉的畫作裡,更是隱隱可見。那個彷彿正要獨自入林的僧人,立在滿佈著分歧枝葉的林間,看似方向堅定卻又步履不移,徬徨怔忡之間,尤其引人好奇。
蔣勳的創作一直持恆堅定,其間的變化隱晦幽微,探討的主軸引人也重要,譬如水墨與油畫的自在合一,生命與美的糾攪辯證,都能逐步見到路徑清明顯現。而貫穿其中的,是一種相當清澄素樸的心境。蔣勳寫說:「所以,走在那洪荒的風景中,可以與江山素面相見,彼此都沒有心機成見。」
素面相見與寧靜致遠,應當是蔣勳創作的底蘊,也是歸屬他一人的獨特風景與姿容吧!
自序
林木深處-二○一六年台東美術館畫展序
島嶼東部的風景常在心中浮起。
因為地殼板塊擠壓隆起陡峻的山脈,騷動不安,彷彿鬱怒被激動起來的野獸,向天空嘯叫著。一望無際的大海,波濤洶湧,擊打著堅硬的岩岸礁石,大浪澎轟,這樣狂野肆無忌憚,鋪天蓋地而來。
有時候覺得,風景其實是一種心事。
走遍天涯海角,我為什麼總是記得島嶼東岸那樣的海和那樣的山。
年輕的時候常常一隻背包,遊走於東部海岸。在一個叫做靜浦的地方住下來,只有一條街,一間小客棧(彷彿叫元成旅社)。夏日黃昏坐在門口、面頰脖子塗粉的婦人,穿著薄薄背心,汗濕的棉布貼著黝黑壯碩的胸脯乳房。她搖打著扇子,笑著說:「來坐。」
滿天星辰,明亮碩大,我看到暗夜里長雲的流轉,千萬種纏綿,千萬種幻滅。
附近營房的充員兵赤膊短褲,露著像地殼擠壓一樣隆隆的肉體,跟婦人調情嬉鬧。
在一個一個黎明,揹起背包,告別一個又一個小鎮,告別婦人和充員兵。他們有時依靠親暱環抱著,像一座山和一片迴旋的海。
靜浦,或者許多像靜浦的小鎮,都不是我流浪的起點或終點,我畢竟沒有停留,這樣走過島嶼東部的海岸和縱谷,學會在黎明時說:再見!
二○○九年至二○一○年擔任東華大學中文系駐校藝術家,在花蓮美崙校區住了一年。覺得好奢侈,可以半小時到七星潭看海,半小時進到太魯閣看立霧溪谷的千迴萬轉。
我時時刻刻在想要去東部了。
台灣好基金會在池上蹲點,我參加了幾次春耕和秋收活動,看到那樣肆無忌憚自由自在的雲,更確定要到東部去住一段時間了。
特別要謝謝台灣好基金會柯文昌董事長,如果不是他有魄力承租下一些老宿舍,提供給藝術家到池上駐村,我到東部去的心願還是會推遲吧。
也謝謝徐璐,開著車帶我從台東找到池上,一家一家看可以居住的地方。最後他們帶我到大埔村的舊教師宿舍,紅色磚牆,黑瓦平房,有很大的院子,我忽然笑了:「這不就是我童年的家嗎?」我想到《金剛經》說的「還至本處」,原來找來找去,最終還是回到最初,回來做真正的自己。
因為是自己的「家」,沒有任何陌生,二○一四年十月一住進去就開始畫畫了。十月下旬是開始秋收的季節了,我走在田間,看熟透的稻穀,從金黃泛出琥珀的紅光。在畫室裡裁了畫布,大約兩公尺乘一公尺半,在台北很少畫這樣大尺寸的畫。在縱谷平原,每天看廣大的無遮蔽的田野,回到畫室也覺得要挑戰更大的空間。
從秋收畫到燒田,從燒田看到整片金黃的油菜花,我記憶著色彩裡的繽紛絢爛,記憶著一片一片繁華瞬間轉換的變滅,領悟著色相與空幻的關係—色相成空,空又再生出色相。歲月流轉,星辰流轉,畫裡的色彩一變再變,畫裡的形容一變再變,那一張秋收的畫變成田野裡的紅赭焦黑,不多久又變成油菜花的金黃,然後,立春前後,綠色的秧苗在水田裡翻飛,畫面又轉變了。
第一季稻作,我彷彿只坐在一張畫布前,讓季節的記憶一一疊壓在畫布上。
我好像只想畫一張畫,畫裡重疊著縱谷不同季節的景象,春夏秋冬,空白的畫布一次一次改換,彷彿想留住時間和歲月。
一年時間,創作二十九件作品,想起有一天看到「林木深處」,絳紅色衣袍的僧人愈走愈遠,樹林搖曳,林木高處的蟬嘶、鳥鳴,樹影恍惚,樹隙間的日光和月光,沙沙的風聲雨聲,人的喧譁,都被他遠遠留在身後了。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春分後八日
· · · · · · (收起)
读后感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用户评价
蔣勳的畫很濃,看著想念池上啦 @2018-11-14 20:26:02
评分蔣勳的畫很濃,看著想念池上啦
评分走马观花吧
评分蒋勋先生受柯文昌之约作为驻村艺术家驻扎于池上乡 此册为其间的油画创作集 《是身如焰》和《林木深处》两幅很有意思
评分蔣勳的畫很濃,看著想念池上啦 @2018-11-14 20:26:02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wenda123.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目录大全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