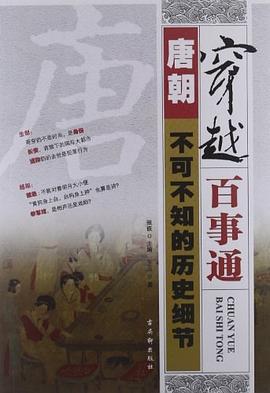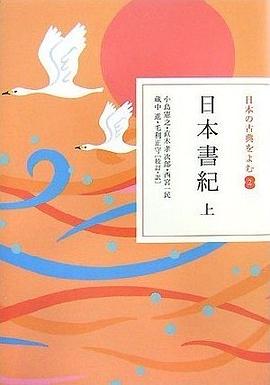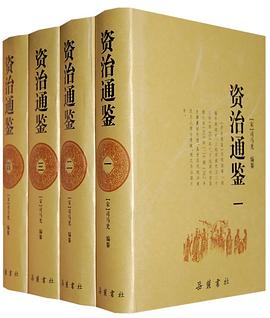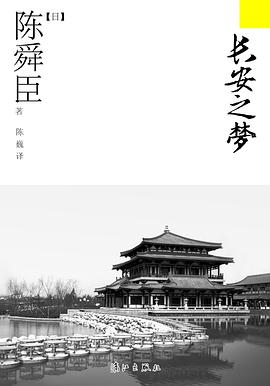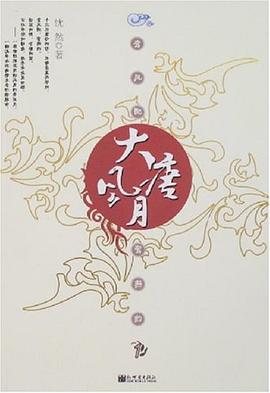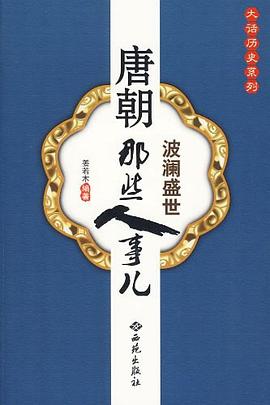第一章我这样管理部下
放死对头的党羽一条活路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我、建成、元吉之间的恩怨在玄武门了结,可要如何处理建成和元吉的上百位党羽?斩尽杀绝吗?有人大声高喊——刀下留人!
利益集团间需要最佳牵头人
河北和山东,自古以来便是天子的粮仓库府,帝王的肇业之基。然而这里也是我李唐天下最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因此,我必须用好安抚河北山东的最佳人选——魏征。
精选自己人进领导班子
玄武门之变,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势力取代业已老朽的政治势力的过程,整个国家的权力,在转瞬间移交到了我手中。拟出一份新的东宫官员名单成为我的当务之急。
必须组建最贴心的智囊团
打天下,离不开武将猛士,而治天下,却需要文人学士。我设文学馆于秦王府西侧,聘请四方饱学之士共十八人。文学馆解散后,他们便立刻成为我在东宫的智囊。
用《氏族志》打造新贵族身份
传承了数百年的门第观念,在所有人心中已根深蒂固,但到大唐初年,许多门第早已失去了冠盖云集的气势和存在的价值。要重新整合门第身份的新秩序,真正确立皇权的无上地位,就靠这本《氏族志》了。
第二章我只用这样的人
人才就要考出来
开科取士本始于隋代,无论门第出身,皆可以入选,但招考人数指标非常少。因此,要广揽天下人才,我就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并且还要把这条路拓得更宽。
抓住小机会上位
马周出身寒门,虽满腹经纶却无用武之地。他远赴长安,只做了中郎将常何的清客。贞观五年,我诏令文武百官上书进谏政事得失。武夫常何写不了,马周站了出来。
看准时机,用性命换信任
我把刚松绑的猛将尉迟恭单独请进了卧室之内。众人被卫士拦在外面干着急:卧室内只有秦王和尉迟恭啊,万一动起手,秦王性命难保……
没有立场,非死不可
单雄信骁勇过人,被誉为“飞将”,可他却几度弃主。虽然良禽择木而栖,轻于去就并不能定为大罪,但单雄信的问题在于,他实在是太缺乏职业道德了。
放对地方了就是人才
打天下靠武功,长孙无忌对此明显不擅长,到了治天下的时候,长孙无忌在治国理政上也只差强人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我赐予了位极人臣的地位和尊荣。
第三章我搞懂了身边的几个能人
魏征不是忠臣
魏征算是忠臣吗?我从来不觉得。其实,就连他自己也不那么想。有一次,魏征在拜相之后,表情恳切地对我说:“我宁愿做陛下的一位良臣,而不愿做一位忠臣!”
和熟悉自己的人斗法
魏征深知劝谏的艺术,而且对我了解颇深。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逐渐发现,这位 “良臣”,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不要把事儿做绝了
我取消了衡山公主与魏征长子的婚事,还亲自下令磨掉我为魏征撰写的碑文。这一切,全都因为魏征把事儿做得太绝了!
让手下那群人乱一点
总有一些出身寒微的人才,被排挤在既有的权力圈子之外。不拘一格地提拔他们,他们自然会与原来的既得利益者势成水火,并抓住一切机会来证明自己。
被同僚排挤的人更好用
刘洎在官场的人缘差到别人一有机会就想整死他的地步,但我还是要保护他,因为他只有一条出路——死心塌地跟着我。
假话也有利用价值
褚遂良在我面前毫不掩饰地诬陷了刘洎,而我给出的处理意见是:赐刘洎自尽!难道聪明如我,真会相信褚遂良的一面之词?
第四章我不在乎官场小人
不露痕迹的马屁最受用
“今天陛下忙里偷闲,假如我这做臣子的还不能顺从圣意的话,您虽贵为天子,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啊!” 宇文士及如是说。
官场里要放一根刺头
我用权万纪为治书侍御史,所凭借的也正是他那无所畏忌的名声,让他狠抓当时朝廷上的坏风气。果然,权万纪一上任,便捅了马蜂窝。
烫手山芋只能冷处理
我最讨厌的人就是裴寂。但我登基后,对裴寂,就好像当年父皇对他一样,宠幸有加。因为,裴寂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动的。
心事就要让一两个人猜透
封德彝是官场权术之集大成者,以他的揣摩才能,可以对我的每一条意旨心领神会。在朝廷处处有谏臣的环境下,听话而又能干的封德彝就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臣了。
宽容坏脾气
萧瑀出身于当时一只手就数得过来的名门望族之一,脾气大、人缘差。然而这样一个老顽固却能五落五起、位极人臣,这一来得益于他的身分背景,二来则是因为我莫大的宽容。
第五章好官都是这样“逼”出来的
贤能是被折腾出来的
房玄龄尽管一直大权在握,但他活得并不轻松。他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遭到我的责备。其实,如果没有我这样折腾他,便没有这位贞观第一贤相——房玄龄。
一打一拉更能服人
尉迟恭在酒席之上趁着酒兴居然打了同僚!第二天,我把尉迟恭叫到面前,一番严厉的斥责令他不寒而栗。敲打完了尉迟恭,自然还得拉上他一把。在这一打一拉之间,尉迟恭明白了自己的定位。
受罚之后的赏赐才有甜头
贞观四年春,李靖一举荡平东突厥,立下盖世奇功。然而回朝之后,等待他的不是封赏,而是御史大夫的弹劾和我的责罚。李靖一下子懵了,难道真的是“狡兔死,走狗烹”吗?
善用手中大权保护新人
马周出身寒门,在朝中没有奥援,又要承担我交给他指摘时弊的重任,无形之中肯定会得罪一批人。我必须运用我的权力给他上一道保险,这样才能让他尽心效力。
用最独特的东西收买人心
贞观十五年十二月,兵部尚书李世勣突患暴疾。药方有云,此疾须得人胡须做药引。而这副做药引的胡须,却在李世勣心中掀起了波澜。
聪明人,不能太一帆风顺
侯君集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然而,他内心过于浮躁、目光过于短浅,总有一天会被这份聪明害了。他的仕途虽然一帆风顺,但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第六章我为官员定规矩
并非腐败打垮了杨广
隋炀帝即位之初的大业五年,隋朝仓廪丰实。不过在杨广看来,他的成就未可限量。有的人从不停下来想想,有的人从不想停下来,杨广同时是这两种人。
分权是为了更好地掌权
自古以来,一直有两条帝王之路供我选择。一种是“乾纲独断”,独尊帝王意志;一种是“垂拱而治”,可谁愿意把自己亲手打下来的江山,分给别人去管理?
律法才是长治之本
人是活的,官职是死的。每换一茬人,势必就要在大唐的政府机构中折腾一番。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就不能靠人,只有靠制度。
卖人情就要做到滴水不漏
我家的患难之交党仁弘贪污敛财达百万之多,定为死罪。但我最终决定演一出戏,法外开恩,免其一死。不过,这样的天恩,可一而不可再。
儒法道的真实用途
帝王之术,须得杂糅儒、法、道三家之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外儒内法,济之以道——正是历代英主御官的不传之秘。
第七章我才是好官的官
在所有人面前显露慈悲
我赦免三百九十个死囚,是要用慈悲感化全天下之人。人心,是君主长治久安的基石。仅仅凭借刑罚威慑万民还远远不够,必须使仁义德行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去。
关键时刻就得用强权
我敬畏史官,不为别的,只为他们手中那一管毛锥。皇帝的一言一行,无论贤愚不肖,都会被他们如实记录,皇帝自己还不能翻阅。但在贞观十六年,我下决心要打破这一铁律。
不能传位给能力太强的人
李泰聪明但肤浅,而且心肠够狠。若是立了李泰,承乾和李治均不免一死。尽管李治懦弱,但立他为太子,却可以避免日后朝堂喋血、大唐倾覆的可能。
《帝范》就是我的遗嘱
辞世前,我要为儿子留下一份遗产。这份遗产,不是大唐的万里江山,而是我毕生心血的总结——《帝范》,想要寻找治国治官之道的人大可以从这本书中去寻找答案。
书摘及插图
放死对头的党羽一条活路
玄武门,玄武门!
在天下人眼里,它不过是都城长安的众多城门之一。
在我眼里,它就是天下!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我、建成、元吉之间的恩怨,终于以这种方式画上了句号,在元吉接连射出的三支弓矢从我耳边呼啸而过之时,我就知道,大局已定。在决定生死的一瞬间,建成懵然地看着我。也许他以为我的下一个动作将是抽箭还射元吉,而他,只是无辜的旁观者。
他错了,我一箭射穿了他的咽喉。一直到死为止,建成都没想明白,我和他最大的差别,是在于我不出手便罢,一旦出手,我只有一个目标,最关键的目标,制敌死命的目标,心无旁骛,如此而已,这,是我十几年来纵横天下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
不过,走到今天这一步,事情远没有结束,只是刚刚拉开序幕。这个赌上身家性命的宝座,我夺到了手里。
但是,我轻声地问自己,我守得住它吗?
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随我一起举事的秦府部将们正群情激奋,他们怒吼着,要求不但要诛灭东宫和齐王府之人,还要连带诛杀建成和元吉的一百多位僚属,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因为在这天以前,这帮人朝夕在我的两位兄弟面前出谋划策,商量怎样除掉我这个秦王,现在,是建成和元吉的这帮党羽为过去的举动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不过,有一个人改变了我的想法。他,就是尉迟恭。
这个魁梧剽悍的莽汉在愤怒的众将中坚持自己的意见:罪孽只及于建成、元吉二人而已。如今大势已定,再株连余党,那就不是与东宫和齐王府为敌了,而是与天下为敌!
此言一出,众皆哗然,大家纷纷斥责尉迟恭是妇人之仁,甚至有人怀疑他刻意标新立异。太子和齐王已死,其党羽一蹶不振,放眼四海,还有什么人可以与秦王一争雄长呢?
不过,这番话是由尉迟恭口中说出的,而这个赳赳武夫,前一刻还手持大戟,目光如炬,肃立于我父皇身旁,以比死还可怕的沉默来暗示我父皇:“陛下,您老了,国家大事也应当放手让秦王去处理了。”现在,他却在我面前,以一如既往的固执坚持着自己的意见:刚才还不共戴天的东宫和齐王府僚属,一个也不能杀。
不能不说,他的意见开始使我冷静下来。
李世民,李世民。从这一刻起,你不再是那个百万军中纵横来去的天策上将,你也不再是那个豪气干云快意恩仇的秦王殿下。如今,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久还将成为天下万民顶礼膜拜的圣上,大唐帝国唯一的天子。
天子,当有天子之道。不能为个人恩怨所左右,也不能为群臣的情绪所左右。这是玄武门事件在为君之道上教给我的第一课。
我很快便接二连三发布出数道善后命令,使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
第一,赦免玄武门事变中曾与我血战的东宫、齐王府将士。这其中,最为有名的乃是建成的部将冯立、谢叔方、薛万彻三人。建成死后,我本以为宫府兵会自动土崩瓦解,没想到冯立却扬言:“哪有在主人活着时受其厚恩,而主人遭难时却避之唯恐不及的畜生呢?”他和谢叔方、薛万彻麾兵猛攻玄武门,支持我的将领如敬君弘、吕世衡等都死在他们手上。秦王府众将早就对他们恨得牙痒痒的,必欲诛之而后快。如今赦令一出,让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大家议论纷纷。
仅仅如此吗?不!这只是个开始而已。很快,我做出了第二件让更多人看不懂的事情:魏征,原东宫太子洗马,负责掌管东宫经史图籍,曾多次劝告建成痛下杀手将我除掉;王珪,原太子中允;韦挺,原太子左卫率,在武德七年的杨文干事件中,他们执行太子的命令,策划令杨文干起兵伺机加害于我。
在赦免了他们的罪过之后,我再次将这些老对头召回朝廷。
如果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话,这些人未必算得上是整场夺嫡大戏中的胁从。以魏征为例,他曾不止一次主动向建成献计将我除掉。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教唆犯。而教唆犯,理应受到更重的责罚,天经地义。
朝堂上,我厉声质问魏征:“你那时为何要离间我们兄弟?”
他的回答很淡定:“先太子如果听我的话,肯定不会遭到这场杀身之祸。”
在场的很多人都冷笑起来,也有人开始为魏征担心,担心大辟之刑马上就要落到他身上——如此狂妄的家伙,光砍头岂非便宜了他,至少也该是车裂之刑,以儆效尤,看还有没有人敢将秦王殿下如此不放在眼中。
我也笑了。魏征,在这个脑筋急转弯的智力抢答游戏中,你回答正确。我要给你的,不是加十分,而是一道新的人事任命。
王珪、韦挺、薛万彻,你们也都一样。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很简单,我需要几条活蹦乱跳的鲶鱼,放到秦王府这个水桶中去。
玄武门,不是我的终点,而是我的起点。然而,前前后后参与这场夺嫡大战的秦王府众臣们,却不一定这样想。他们中间,有这样几种人:
第一种人,原来提着脑袋,整天出生入死为你卖命的人。要知道,死于夺嫡跟死于打天下是两码事。后者是大唐的功臣,享有无上的荣光。而前者,根据成王败寇的残酷定律,只能在身后领到一顶“乱臣贼子”的破帽子而已。成本如此高昂,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我一旦继承大统之后,那数不尽的荣华富贵作为回报?
他们将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饱食终日,不思进取。他们会在飞鹰走犬酒足饭饱之后,怀念一番过去激情燃烧的岁月,然后继续飞鹰走犬酒足饭饱。
这,不能怪他们。人的本性便是如此。当一个在鬼门关前走过一遭的人突然有一天发现,人生这辈子想要的都有了,该有的也都得到了,他还期望什么呢?
第二种人,为我抛头颅,洒鲜血,一旦事定之后却居功自傲,甚至不惜犯颜抗上。他们跟第一种人的区别在于,他们有时候太有自己的性格,太有自己的主张——大爷我当初豁得一身剐,敢于拥戴你黄袍加身,难道还没有摆摆谱,在你面前放肆一下的资格么?他们并不清楚,哪怕一个再有涵养的普通人,恐怕也难以容忍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拿出过去的功绩来摆脸色,更何况言莫予违,将脸面看得比天还要重要的天子。
很可惜,我最为看重的部下之一,恰恰就是这样的人,就在以后犯下了这样的错误。
第三种人,原来不属于秦王府嫡系,而是从父皇和建成、元吉身边拉拢过来的人,比如常何等,他们会庆幸他们慧眼识人,投机成功,把底牌聪明地全数压在了我的身上。
那么,下一次,他会押给谁?他会以怎样的方式押下赌注?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认为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上天眷顾而在赌桌上第一次大赚一笔的家伙,一定还会寄希望于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有一天,他们在赌桌上输得精光为止。而这输掉的,恐怕还不只是身外之物那么简单。
秦王府里不都是这样的人,但,秦王府里有这样的人,而且还不在少数。他们都是一等一的精英,要不然,也没有资格走进秦王府的大门。
不过,若是就此放任这种情绪潜滋暗长,使得他们不再安于职守,终日缅怀往日荣光,或是贪图侥幸之功,无论是对他们,或者对我,还是对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看不见的巨大损失。
因此,我才会不顾他们的疑虑与不满,授予原来的对手魏征、王珪等人新的官职。我要借这些人来向他们传递一个信号:我用人施政,看的不是过去的功绩和关系,而是才能、品行、忠诚。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即便是我昔日的仇敌,我也会不拘一格地任用和提拔他,与我的旧部一视同仁。这无疑是向玄武门事件中的功臣们敲响了警钟,让他们牢牢记住,今天的功劳,并不是一辈子的长期饭票。当然,这层道理,聪明如房玄龄等人,立刻就领会于心。而有些迟钝的人,在多年以后终会为之付出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当然,落实到具体的任命政策上来,还是大有学问可讲的。首先说说魏征,他从我这里得到的,乃是太子詹事主簿一职。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任命。因为我这个太子,也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职位而已。至于王珪、韦挺等人,则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参议朝政。
太子詹事主簿,掌管东宫印信、文书、纸笔,是正七品的小官。其直接上司是正三品太子詹事,也就是说,他等于是太子詹事的文案助理。这个职务看似品级低微,却十分关键。因为在玄武门事变后,到我正式登基称帝的这两个多月时间里,一应军国大事,实际上都要经由魏征之手。
不过,自始至终,魏征都需要在我的眼皮底下工作。
谏议大夫,正五品上,掌管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事则上封事。也就是说,王珪和韦挺是我在国政事务上的参谋,有贡献建议、出谋划策的责任,然而没有具体的决策权和执行权。
也就是说,魏征、王珪和韦挺这些人,属于观察使用的对象。他们来自于原先势成水火的宫府一方,我自然不可能立刻将最为关键的决策权、人事权或执行权交之代行。只能先将他们放在秘书或参谋之类的岗位上,先进行磨合,再进一步考量其才干和忠诚度。而这对于刚刚死里逃生的魏征等人来说,像太子詹事主簿和谏议大夫这样的职位,可以掌管机密,或随时向我提出他们的意见,已经属于莫大的信任,夫复何求?
饭,要一口一口吃;官,要一点一点升。
封赏来得太急太猛,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我,都没有好处。此中的学问,就像一个掌勺的大厨,自然对什么情况下该用文火,什么时候该用武火了然于胸。
而现在,正是该用文火的时候。
不过,这个局面很快便被打破了。因为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蠢蠢欲动。若是处理不当,必将使得天下瓦解,十数年征伐辛苦毁于一旦。
为此,我发布了第三道让众人震惊的命令——封魏征为巨鹿县男、谏议大夫,以特使的身份,出巡安抚河北、山东等地。
任命一出,整个天策上将府都为之沸腾了。
利益集团间需要最佳牵头人
建成和元吉已被杀,既成事实,父皇默认。但这并不意味着天下已经牢牢地掌握在我手中了。许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在他们看来,一切水到渠成。
真的如此吗?尉迟恭那天说得很对,他说,你要小心,小心全天下的人都与你为敌。我知道,他一点也没有夸大。
来自北方突厥的压力与日俱增,他们已经得到消息,大唐朝堂之上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要不了多久,他们便会像一头狡诈的恶狼一般开始掂量,这一事件会给他们带去什么意外的礼物。
然而最大的危机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大唐的心腹之地——河北和山东。
河北,说的是黄河以北。山东,指的是华山以东。这里物产富饶,民风强悍,乃是天子的粮仓库府,帝王的肇业之基。隋代大业七年,便是王薄在齐地的长白山首先举事反抗隋炀帝的暴政。正是那曲《无向辽东浪死歌》使得天下人为之鼎沸。继之又有窦建德、刘黑闼在这里旋起旋落,一度竟有西向与我大唐中分天下之势。那场唐夏虎牢关之战,至今还令我大唐许多武将忆之胆寒。我还记得,我父皇曾因刘黑闼等人的屡次死灰复燃而恼恨不已,竟令建成将山东十五岁以上的壮丁尽数杀光,将老弱妇孺迁入关中之地。在这里,我李家留下的是刻骨仇恨。
另外,河北和山东也是建成在地方上最有力的支持者。当时我为国家剿灭窦建德、刘黑闼,向来都是以强硬手段来对付当地人。而建成则听取魏征的劝告,出兵征讨刘黑闼残部时,将俘虏全部释放来换取人心。可以说,我栽下了大树,乘凉的却是建成。在这里,他比我的威望更高。幽州大都督李瑗便是建成的心腹,玄武门事件后,许多东宫和齐王府的党羽首先便是逃往他那里避祸。而王利涉劝李瑗造反时也是这样为他分析形势的:
“山东地区,人们先跟随窦建德起事,豪族雄杰,都曾为窦氏之部属,如今全部被废免为寻常百姓。这些人一直在寻找机会试图再次为乱,其迫切心情就好像是旱苗期待甘霖一般!”
我李唐天下,倘若要出问题,就一定会出在这里,时机紧迫,如箭在弦上。为此,才有了前面那一道让所有人都惊讶与猜忌的任命——派魏征安抚河北和山东。
当然,在此之前,我已经派出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射,镇守洛阳。这是一步先手棋。行台,也就是行台尚书省,是临时性的地方行政机构。“诸道有事则置行台尚书省,无事则罢之。”而我当年便为陕东道的最高长官——大行台尚书令,正是借这里控制东都洛阳,与李建成互成棋劫之势以相制衡。后来又留下温大雅担任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代我镇御此地。不过,温大雅乃是一介书生,在这乱世初定的时候,要想镇服人心,还得下猛药。
而这猛药,就是屈突通。
屈突通,著名老将,隋代时便以刚直忠勇、智勇足备而闻名天下。他后来归降大唐,一直跟随我转战南北,论功行赏时,这位老将位居第一。他又曾两次出任陕东道行台仆射。这时我再次请他出山镇守东都,可谓人地相宜。有了他的赫赫威名,河北山东诸雄豪纵有反心,又怎敢轻举妄动?
当然,我很清楚,要应付关东如此复杂的局面,光有武的一手,还远远不够。我更需要的,不是慑服人心,而是安抚人心。虽然严刑峻法足以让人生畏,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因此,安抚河北和山东的重任便落到了魏征肩上。很多人想不通,秦王府舌辩纵横之士何其多,聪明才智之士又何其多,为什么单单把这样的重任交给一个曾经被视若仇雠的魏征?
其实,这里面大有文章。
魏征,河北巨鹿郡曲城县人,出身孤贫,豪气过人。他年轻时不治产业,曾出家为道。隋朝末年,天下板荡。他很早便留意纵横之术,以辅佐帝王诸侯为己任,他所侍奉过的主人,便是曾经不可一世的李密,然而他自始至终却得不到重用。后来魏征随李密降唐,长期默默无闻。后来,他自己请命安抚山东,仅凭口舌之利,就说服李密旧将李世勣来归。窦建德击败李世勣后,魏征被俘,于是他又成了窦建德的起居舍人。直到窦建德为我所擒,魏征这才返回长安,得到建成的赏识,委以太子洗马之职。他倒是想就此好好大展一番拳脚,没想到时乖运蹇,建成命丧玄武门,自己又变成了戴罪之身。
从这份不长的简历里,能看出什么?
我看出了两个字——坎坷。一个胸怀大才,欲安天下,却屡遭蹉跎打击之人的坎坷仕宦之路。
在魏征还是建成属下的时候,我们没什么机会,也不可能面对面在一起聊些什么。不过,在建成事败之后,我当面责罚魏征,他那不卑不亢的反应却使得我开始认真打量起这个人来。
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诚惶诚恐,表示今后定当痛改前非、尽忠于我。从他那天的回答中,我听到的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冷静,以及叹息良谋不用宏图不展的悲哀。
这个长着山羊鼻子、其貌不扬的男人,他胸中装着的,不是对某一人的耿耿忠心,也不是对身前身后名利的汲汲渴求。他藏着的大抱负,就是拥有一个能尽情展示自己才情的舞台和机会。
这样的人,可以为我所用!
另外,从魏征过去的经历来看,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山东河北安抚特使这个任务了。魏征本来就是河北人,年轻时便在这里广交各路豪雄。建成与我争夺皇位之时,他也曾利用这层关系,多次劝谏建成接纳山东豪杰,以张羽翼。派本是建成心腹的魏征出使这一地区,才能更好地表明我既往不咎、咸与维新的大度胸襟。
魏征啊魏征,你到底是个郁郁不得志的二流说客辩士,还是智虑过人、独当一面的雄才,我倒是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看上一看。
果然,魏征一到地方,就掀起了波澜。当他宣抚至磁州时,正好碰上押解前东宫千牛李志安、齐王府护军李思行的囚车。这两个人都是建成和元吉的党羽,玄武门事变后千里迢迢从长安一路奔逃至此,没想到却成为地方的阶下囚。
这件事本来跟魏征无关,不过,他却对副使李桐客表示:“在我们奉召出京的时候,朝廷就已经宣布赦免所有东宫和齐王府的僚属,前罪不究。可如今却又把李思行他们当成罪犯往京城押解,这岂不是等于向天下宣布朝廷的赦免诏令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吗?那你我二人出京安抚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岂不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吗?国家的大计方针,就因为这么一件事,便全部被破坏了。既然是符合国家利益之事,便可以大胆去做。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得失,而损害国家大计。如果立刻释放李思行这些人,免除他们的罪名,那么普天下的臣民,无论远近,都会从这件实事中看到朝廷的诚意。我们奉召出使,如果经过深思熟虑,确定是有利国家的,不应当畏首畏尾,而是勉力担当,以报效皇上对我们的信任!”
说完这番话,魏征便以朝廷的名义,将李思行等人尽数就地无罪开释。这本来是越权的行为,然而消息传来,我不怒反喜。
好,好!好一个魏征,我果然没有看错!河北山东,自此定矣!
不过,此时的国家,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我的帝王之路,还有很长的征途要走。
· · · · · · (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