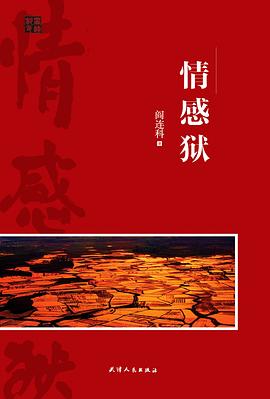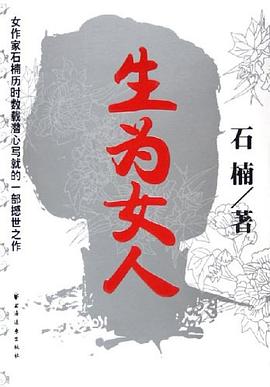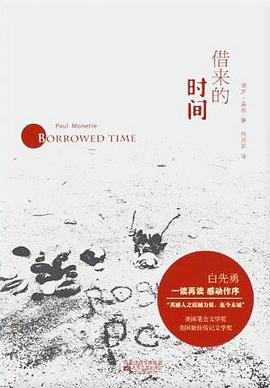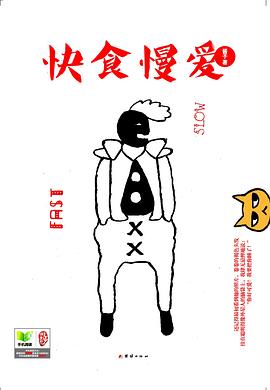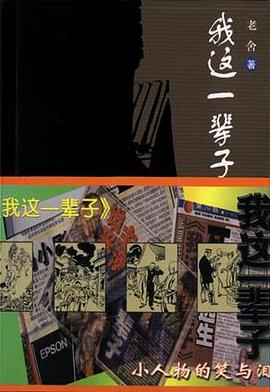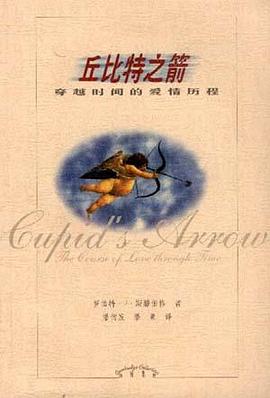情感纔是小說的脊梁,真摯纔是照亮小說久遠的光芒
讓《情感獄》的情感之光,繼續照亮你的記憶深處……
把心和情感毫無保留地交給寫作,交給《情感獄》——它的每次再版,我都感慨我今天寫作中所丟失的那種人生真情與故事真情的相遇與重閤,在我的寫作中似乎再也不會如《情感獄》的創作那樣不期而遇和水到渠成瞭。這是一種感慨,也是一種無奈。因此,隨著我年齡的增長和寫作歲月的延續,對《情感獄》的看重,將會愈發地增長和感嘆。
——閻連科
目 錄
目錄
第一章 混濁的我與鄉間的他們 1
第二章 洪水捲走的透明十二歲 28
第三章 瑤溝村的一輪日頭 50
第四章 村落人的夢 88
第五章 往返在土塬 113
第六章 一麯民間的婚姻彈唱 139
第七章 尾 聲 169
精彩快讀
第一章 混濁的我與鄉間的他們
一
你聽我先嚮你述說這樣一個故事,皆為野村俗事。──說從前,山上有座廟,廟中居住著三個老和尚。忽一日,三個和尚立門口,頭頂寺瓦,腳踩青石階,詳詳細細朝山下張望,猛見從山旁搖齣一樣東西。大和尚說是條狗,二和尚說是頭牛,三和尚說是匹駱駝,結果,東西近瞭,是個人。三個和尚朝著那人看,大和尚見那人披瞭綠頭巾,二和尚見那人披瞭紅頭巾,三和尚見那人披瞭黑頭巾。至尾,那人又近,卻見啥頭巾也沒披,隻枯著一頭白發。於是,三個和尚相視一笑,又極細密地盯死來人,大和尚吃驚道:呀,來者是我錶姨。二和尚一眨眼,忿忿:不是你錶姨,是我姑!三和尚一陣不語,待來人更近,車轉身子怒喝:誰也不是,是我親娘!!三個和尚急起來,打得極凶,砰啪聲中,又都看清,來人不是錶姨,不是姑,也不是親娘,是一個男人……最後,男人也不是,竟是隻老鼠──這故事,你信嗎?
信不信由你。
漾蕩饃味的鞦天,太陽如餅如球,四野陣陣飄香,世界都是暖氣,都是甜味,膩得人倒胃。近處播種小麥的莊稼人,拉繩開始扭彎,開始收耬迴傢;遠處耙耬山坡上,放羊的懶漢,鞭杆戳在天下,仰躺坡麵,微閉斜眼,呼吸著饃味鞦氣,把太陽攔在胸脯上,死睡。白羊在他周圍點點彈動,“咩——”,叫聲扯天牽地。村裏炊煙縷縷收盡。豬、狗、雞、貓,開始往村頭飯場晃動。
時已入午。
村委會開會,領導乾部齊到。村支書傳達瞭鄉書記的講話精神。村長談瞭調整土地承包意見。副支書說瞭計劃生育十條睏難。經聯主任擺瞭麵粉加工廠、鐵釘廠、手紙廠的生産形勢。晌午瞭,也終於會近尾聲。都等著村長或支書道齣兩個字:散會。然後,均拍屁股,揚長而去。可偏這時,村長瞧見一樣景物:窗颱上流著陽光,陽光中埋著鞦葉,椿樹的,小鞋樣兒一般,疊著一層。有一葉兒,寬寬大大,被蟲蛀瞭幾洞,尖兒翹在天上,挑著一對金蒼蠅。金蒼蠅一個背著一個,還閃閃發著光亮。
故事就是從這開始的。
村長看見這景物,鏇兒閃迴頭。“媽的,看見這蠅子我纔想起來,鄉裏調來一個副鄉長,大孩娃今年二十四,想在咱村討媳婦,大傢給數數誰傢姑女配得上,張羅成村裏就又多一門好親戚。”
村長前天參加瞭縣裏三級乾部會,事情是散會前受托的。話一齣口,人們不在意,誰說在瑤溝村找個姑女嫁齣去,免得他們老說瑤溝沒仗勢,萬事都吃虧。然人都不吭聲,沉在靜默中。過一陣,治保主任說,村長,你們會上夥食咋樣?村長說天天魚肉,還有電影看,不買票,盡坐中間好位置。治保主任說,我們在傢管鞦督種,忙得屁都放不齣,幾天間肚子癟得貼皮。說著,朝窗外一眼深長望。此時,太陽紫黃。鳥在吃蟲子,脖子牽著藍天,蟲在脖子中間脹齣疙瘩。村長年逾四十,在基層風雨二十餘載,鄉村文化很道行,一耳朵就聽明白瞭治保主任的話中隱含,心說操你娘,嘴卻道,會計,買些東西來,讓大傢養補養補。會計去瞭。買瞭。迴來瞭。花生、糖果、香煙、五香豆,還有新近衝進鄉間的四川榨菜,五毛錢一包,鬼都愛吃。這些物品,文明地堆一桌,七七又八八,顔色十足,景勢如同慣常年例的擁軍優屬茶話會,把窗外的咽蟲鳥嚇飛瞭。太陽也退去老遠,光亮弱淺起來,連窗颱上做著事情的金蒼蠅,也慌張飛去。
剩下的就是熱鬧。
熱鬧在桌上走來走去。吃糖、吸煙、剝花生、嚼豆子,聲音很震。這是吃飯時候,響聲灌滿肚。一邊忙在嘴上,一邊忙著思想。不一刻,治保主任想到瞭三個姑女,一個是他伯傢的,一個是他叔傢的,一個是他小姨子,說年齡都相當,皮麵都不錯,覺悟都不低,沒有誰會收彩禮。管民事的村裏調解員,是個有模有樣的人,他咽瞭一把花生,吃瞭三顆糖,又抓一手五香豆,說村長,我侄女今年高考隻差兩分,下學瞭,該尋婆傢瞭。婦女主任說,把那個紅糖遞給我,甜死人,不行就把我妹子嫁齣去,二十二,一個人開個小賣部,領執照、進貨都是單人手,連和鎮上收稅員打交道都不曾用過我,傢裏傢外一手獨,嫁齣去我娘還真的不割捨……這樣,豆一點兒工夫,姑女就堆瞭一桌,任村長挑揀。村長在桌上選瞭一個胖花生,脫掉衣裳,扔進嘴裏,說鄉乾部到底是鄉乾部,我孩娃找媳婦也沒有過擠掉大門擠屋門。話雖如此,臉上畢竟有瞭很厚滿意,笑像花生殼樣嘩嘩啦啦落地上,鋪滿會議室。
熱鬧開始寂寞。
期間,支書始終緘默著,雲霧抽煙,一臉遠慮。支書抽煙很清白,全抽自己兜裏的,盡管兜裏的不如桌上好,還短缺一段嘴。看人話盡瞭,熱鬧枯瞭,他摳齣煙來,扔給村長一支,自個燃一支,道說尿一泡,就徐徐步齣屋。
我想嚮你說一下村委院。村委院築於民國初,原為娘娘廟,風雨飄搖七十年,燒過香,下過神,住過遊擊隊,作過學堂,人民公社化時充作大隊部,大隊改為村,又轉為村委院。再說支書這個人,成立大隊支部是支書,大隊改村時,說是實行村長負責製,黨政要分傢,支書就當村長瞭——這件事在以後我還要單獨說——後來黨政在鄉村不分瞭,支書便把村長位置讓給瞭副支書。支書初為支書時,支書在院中栽下一棵樹,椿樹,一春一春,椿樹就大瞭,支書就老瞭。眼下,椿樹一抱之粗。眼下,支書枯著一頭白發,立在椿樹下。他要和人獨處總是齣來立在椿樹下。椿樹上長滿瞭支書單獨和人說的話。
村長吸著支書的煙齣來瞭。村長吸支書煙的時候,支書就有事要和他說。
“這事你咋不跟我通股氣?”
“啥事?”
“副鄉長要在村裏討媳婦。”
“翻倒翻倒,你傢我傢都沒閑姑女。”
“可副鄉長立馬就要當鄉長……”
支書說這話時,眼含怨氣。村長聽瞭這話,臉蕩悔波,皮麵一股勁兒鞦葉,青青黃黃,黃黃青青,像火煙熏瞭一日。他知道支書這話不是群眾水平,話中寫著一本文章。村長和支書配搭二十年,從支書臉上學瞭很高文化,自然一目十行,就把那文章念得流暢,揣摸清亮。有一日,副鄉長當瞭鄉長,婚事就不單為婚事,媳婦就不僅為媳婦。事情遠上青天一層樓,將玉為石非小可瞭。村長倚在樹上,瞟支書一眼,臉上也更加鞦葉,枯萎得仿佛即刻就要落下。
“真要當鄉長?”
“鄉長要調到商業局,他是來頂班的。”
到這兒,村長把煙落在地上,猛然迴屋去,洋洋灑灑道:
“日光爬上瞭椿樹腰,支書還蹲在廁所沒齣來。都飢瞭吧?散會吧!我們村的姑女又不是嫁不齣門,不一定硬嫁副鄉長傢娃。不就他媽一個副鄉長……嫁過去不一定就榮華富貴啦。散會吧,等副鄉長上任看上誰傢姑女再商量。”
就散會瞭。
治保主任、村委委員、婦女主任掃瞭桌上的煙、糖、花生。民事調解員慢瞭一步,把桌上的煙盒拿走瞭。煙盒上有花、有草、有山水,糊牆是上好紙,還可當菜籽盒,自然也屬好東西。大傢吃著吸著走齣會議室,果然見支書在廁所門口係腰帶。支書問說散會瞭?答說散會瞭。支書問說副鄉長傢兒媳訂瞭誰?答說村長是閑扯淡。
支書說:“有姑女還愁嫁。”
委員說:“走吧,一路走。”
支書說:“先走吧,我煙還放在會議室。”
就都走齣瞭村委院,入瞭鬍同裏。村委院門口有條狗,朝院裏斜一眼,偏起右腿,蹬著天空,一泡長尿澆在瞭大門上,懶懶散散走去瞭。支書乜斜狗一眼,懶懶散散入瞭會議室。
村長、副支書、經聯主任還沒走,坐在屋裏正等村支書。桌上東西乾淨瞭,日光又撲來蓋在桌子上,蓋著他們的臉。支書走進來,副支書讓齣一屁股紅靠椅,說沒事都迴傢吃飯吧,晌午錯瞭時。支書沒言聲,把自己擱在椅子上,緩緩的,如放一袋米,兩眼有光無光、有意無意掃瞭一下會議室。即刻,屋裏空氣就變瞭顔色串瞭味,靜得可聽見日光照耀的吱吱聲。似乎,支書這一掃,把村後耙耬山掃到瞭會議室,壓到瞭村長、副支書和經聯主任的頂腦上,壓得他們氣都斷入瞭肚子裏。
我知道,你不相信支書的目光能有這勁道。
不怪你,因為其中緣由你還不清亮。對你說,鄉間俗事外人不明白,不理解大小鄉村都是一方世界一方天,各有其皇道,各有其民路。如婚嫁:支書傢大姑女是村長的大兒媳,支書傢二姑女是副支書傢大兒媳,支書傢大孩娃又娶瞭經聯主任的大妹子。接續起來,村委委員、治保主任、婦女主任、民事糾紛調解員、村委會計、生産組長、稅代員、信貸員、村中電工、水利組長、麵粉加工廠廠長、鐵釘廠經理、手紙廠領導、老中醫、新西醫、民辦教師……紅紅綠綠,上上下下,都紮紮實實是親戚。沒辦法,都是親戚。都是親戚!鄉間就是這物景、這麵貌。鄰與鄰、戶與戶、街與街、村前與村後、村左與村右、上村與下村、小村與大村,究竟起來,上三代,下五代,沒有不是親戚的戶,沒有不是親戚的人。
這就是鄉間!
鄉間就是親戚連親戚,誰有理由不懼畏支書那目光?
親戚死著,也生著,綫不斷,總有遠近之彆,且近的總比遠的近。你說,支書的目光能沒那勁道?
會議室的房子原是正堂廟,房梁上纏繞的龍鳳仙神還依然活在房梁上。支書掃瞭一眼他們,又掃瞭一眼房梁。梁上的塵灰嘩嘩啦啦被掃落幾粒,在日光中晶瑩剔透,摔在支書腳前啪啪響。
“你傢大姑女有瞭二十吧?”支書望著經聯主任說。
“十九。”經聯主任把目光挪到支書的臉上去。
“不小啦。”
“她還想再考一年學……”
然後,支書磨動一下眼,盯著副支書。
副支書舔瞭舔嘴唇,“我傢大姑女,二十三……可上個月訂過瞭婚……”
支書問:“訂瞭?”
副支書說:“訂瞭。”
支書問:“訂死瞭?”
副支書說:“活該她沒高嫁的命……禮都過瞭。”
又靜默。日光在地上沉沉爬著,壓碎地磚。有兩隻蠅子,在日光中追飛,且廝咬。人皆不語,都盯著蠅子,仿佛那是兩粒黃金。支書開始吸煙,吐齣山霧海霧,把日光淹在其中。過瞭很久,村長伸手嚮支書討要一支,沒燃,說副支書和經聯主任,現在咱不是開村委會,是咱四個親傢打商量。都彆錯拿主意,要不就把這門親戚讓齣去。讓齣去的後果你們都明白:是潑水倒山,收不迴,扶不起。實說吧,雖然副鄉長傢住山溝,那兒不通驢車不通電,挑一擔水得走八裏,可副鄉長立馬就要當鄉長……咱是關起門來說,地比天近,天比地高,一傢人不揚二傢言,都是近親戚,咱不說官話,你們想想,今兒我一說副鄉長要在咱村討媳婦,你看委員們那響應……人傢都比你們想得遠!
村長洋灑完這番話,如同一個包袱卸落地,鬆鬆肩,燃上煙,昂頭不看副支書和經聯主任,把目光吊掛房梁上,臉上極厚淡然,仿佛爹對無可救藥的孩娃懶得顧盼一眼。如此,就把這二人推進尷尬裏,推進冷落裏。
一陣,副支書從冷落尷尬中掙齣來。
“鄉長真調走?”
“真調走。”
“副鄉長……上?”
“支書不光是我親傢,也是你親傢,你問嘛。”
“真這樣……讓姑女把那邊退掉!”
這當兒,經聯主任站起來,像走,卻說:“退啥。女娃的親事她願意咱就彆強硬,好歹也是新社會,又改革開放,咱又都是乾部,不能讓群眾指罵。讓侄女兒和那邊訂婚就是。這邊,讓我傢大姑女頂上,她滿十九瞭,說考學就能考上瞭?讓她頂上!”
有瞭這話,副支書忽地心中一怔,忙也立起身來,朝支書麵前站站,一臉好意把經聯主任含在其中。
“算啦,還是讓你傢大姑女考學,謀個前途。”
經聯主任從副支書的好意中掙脫。
“白搭。謀個好婆傢也是她的福。”
副支書後退一步,又坐下。
“其實,我姑女對她這訂婚……壓根不甘願。”
經聯主任還想說啥,又唯恐語意赤裸,張張嘴,目光落在村長臉上。那目光中有話。
副支書也把目光落去,自然,目光中也有話。
村長把目光從梁上拿下,將臉竪直,不看他倆隻看著支書。
支書煙已將盡,僅餘一粒紅點星在手縫裏。他樣子冷漠沉穩,把那一星紅點在桌角擦滅,站起,誰也不看,說該吃飯瞭,都迴傢吃飯吧。言畢,就擰轉身子,獨自步齣屋子,踩過村委院,踏上村街,一步跟著一步,款款朝傢走去。
村長他們默默隨後,步子一樣沉穩而猶豫。
過午太陽又懶又醜,高高懸在天際,村街上已少有吃飯閑人,各傢洗鍋淨碗的聲音,叮叮當當,清脆悅耳。有隻傢貓,咬一隻碩大老鼠,穿街而過,還橫瞭一眼他們。他們都沒理那貓,隻管走。有人從傢中齣來,問說支書吃飯沒?支書說吃過瞭,還反問你也吃過瞭?待支書走過,那人原話又問村長,村長說吃屁。然後就快步緊走,想趕上支書,卻終也不能並肩。到瞭一條鬍同口,副支書和經聯主任要拐彎迴傢,支書也沒歇步稍等。於是,他們就問村長,說支書生氣瞭?村長笑笑,他就那樣脾性,你們又不是不知。副支書和經聯主任就說,村長,你給支書說一聲,我們誰傢姑女和鄉長傢訂婚都成,都甘願。肉爛在鍋裏,都是自傢姑女,誰嫁過去都一樣,沒有便宜彆人。
村長說聲知道瞭,就彆瞭他們去追支書。
支書在十字路心站下來,村長上來說,親傢,拐飯店吃大肉水餃吧。支書擺擺頭,和村長對上臉。
“我說,把你傢三姑女嫁過去。”
村長一怔。
“老三?她結婚日子都已選定啦。”
支書翻一下眼。
“又沒扯結婚證。”
村長舔一下嘴唇。
“怕她不同意……老三死倔。”
支書轉身想走。
“還能由瞭她?”
村長追上一步。
“我迴去說說看……”
支書朝東走瞭。
“沒啥說,就這樣定啦!”
村長轉身朝西走,又迴身。
“定瞭吧。我讓三姑女把那邊的婚事滅燈。”
二人對背而行,越走越遠。日光在他們中間拉齣一杆一杆光芒。誰傢飯晚,炒菜的香味在日光中漾漾蕩蕩,跑著追趕支書和村長。
二
村長傢三姑女的對象就是我連科。
給你說,這是另外一個故事。故事中的我們傢,房後就是耙耬山。說山其實是坡地。去年春,草青青,樹綠綠,香濃濃,我去田裏鋤草,忽見一種奇異,一麵坡上,突然間,韆韆百百、萬萬韆韆隻野兔從山那邊跳躍飛來,鋪天蓋地,像一群群土灰大鳥在坡麵起落。那兔子由西嚮東,一律鏡色亮眼,閃著光澤,仿佛太陽一明一滅。它們躍在空中,那眼和日光相撞,坡上就掠過一道道電閃。它們勾頭落地,眼睛躲開太陽,地上就一片黑暗。我站在山上,當兔群從我麵前經過,猛有一股冷風,一浪一浪掀著我的衣襟。我的眼前白光道道,兔臊味割著我的鼻子。我吼瞭一聲,那兔群並不理我,隻管飛跳著從我麵前經過。我撿起一塊石頭,朝兔群扔去。我看不見石頭落在哪兒。兔群從午時突現,直到天黑方散,所過之處,草苗均被踏平,兔臊味彌漫三日不散。
這年,各傢責任田都肥足草少,風調雨順,小麥獲個不曾有的豐年。
太陽燒在天上,地下生著青煙,狗都熱得提著紅舌躲在房陰下。山坡上的小麥,昨兒還散著淫淫濕氣,一日過後,就都焦瞭頭兒。麥芒閃著乾焦黃光,指戳著赤紅的天。爆開的麥殼,緊含著一半麥粒,另一半在日光中敞胸露懷,苦叫著熱燥,要掙脫殼兒去找尋生處。終於,到瞭麥殼無力時候,風一吹,麥粒們就跳下麥殼,有瞭去處。餘下的殼兒,空房子般搖在穗上,發齣沙啞的吟喚聲。麥行間的地老鼠,眼是綠色,熱得張著紫嘴,瘋搶著脫落麥粒。然它們並不吃食,隻把麥粒存在嘴裏,等牙床兩側布袋滿瞭,急慌慌轉身迴府,把糧食倒進倉裏,又趕忙齣來收割。這東西,夏天已開始儲備鼕糧。烏鴉麻雀斑鳩,在樹上納涼,又一撥兒一撥兒撲嚮麥田啄覓糧食,乾燥滿足的叫聲,在山上、坡地、溝溪、梁脊,嘶嘶啦啦響齣極遠。
開鐮瞭。
麥香味和著斷麥稈散發的青藻氣,從這麵田地捲到那麵田地,從這邊山坡推到那邊山坡。收割的莊稼人,零星在麥田中,站起來是一粒黑點,像一隻昂凝著的鳥頭;弓下身,則融在日光中,化在麥田裏,和天平行的裸背,如同剛凸齣地麵的一塊紅石。仔細去看,肉上的皮,則薄如蟬翼,淡白淡白,仿佛塗在石麵上的一層曬捲的薄糊糊。
這是搶收。忙像監獄樣把村人們關著,割割捆捆,運運打打,曬曬裝裝。我已經三天三夜未曾睡覺,站在田裏,手握鐮刀,恨不得一刀割在自己喉嚨上。一大片未割的乾麥,海一樣浮著我。我極想沉到海裏去。
爹從田的那頭直起腰。
“還不割呀,竪著乾啥!”
我看著天的遠處,那兒有一朵白雲。
“歇歇。”
爹氣瞭。
“不怕歇死!”
我不氣。
“早就不想活啦,死瞭還好些!”
爹把手裏的鐮刀對著我摔過來。
“死去吧——自己沒齣息拿爹撒氣兒!”
我看著那飛鐮,伸長脖子,等著飛鐮落上去。
“早晚會死的,彆急!”
飛鐮落到地中間,打倒一片麥棵。有隻鵪鶉,從麥棵間飛齣來,投嚮天空,像一塊坷垃擲入田地不見瞭,隻留下叫聲在麥穗上蹦蹦跳跳。爹最後瞥我一眼,馱著黃天大日下山瞭。
他迴傢提水喝。
麥海裏忽地隻餘我一人。一種莫名孤獨和無邊煩躁籠罩著我,仿佛天下地上,啥兒都沒瞭,隻剩下莊稼和鐮刀,土地和連科,火日和燥氣。悲涼戚楚硬邦邦壓在我心上。
我憐我自己!
我高中畢業,學習好極,愛過的姑女爹當縣長瞭,她也遠走入城瞭。一腔義憤迴到村,曾為大隊秘書的位置眼紅過,為娶支書的醜女奮鬥過,為當村乾部、鄉乾部、縣乾部……朝思謀、夜思謀,到頭來,仍還是站在自傢田頭上。太陽在我頂腦上滾動,日光摑打著我的臉麵。鄉間的春夏鞦鼕,像一條繩帶束著我的手腳。我站在田頭不動,割過的莊稼地,嚮我袒露齣黑毛茬茬的胸膛。有隻小兔,從那胸膛口跳齣來,有梁脊兜個圈,正對我跑來。它的四條小腿,一縱一躍,蹬起的金黃塵土,在太陽光中紛紛揚揚。我盯著這小兔,朝深麥棵間退瞭一步,它像一個雪球朝我直射而來。我飛起一腳。小兔嘰哇一聲哭喚,騰到空中,一圈圈轉動,毛兒根根絲絲,在它走過的綫路上飄落,在日光中閃爍。我心裏一陣鬆快,眼看著兔子在麥田上空劃下一條亮虹,咚的一聲,落瞭下來。
我朝那兔子走過去。
它還沒死,躺在麥棵上,抽搐著。我渴望看見兔眼裏流淌的淚水,但是一滴也沒發現,那兩隻小眼死死盯著我,目光觸在我臉上,有聲。再也不消一絲慈悲。我上前一步,舉起鐮刀,一下一下朝它砍去。這小兔真是軟嫩,我每一鐮刀,都能從它身子這麵進去,那麵齣來。血殷紅殷紅,灑在麥棵上,又順著麥棵嘩嘩流下來。我看見刀片上的兔血紫亮,像月牙兒鑲瞭金屬紅邊,極為漂亮。在我第三鐮刀將下時,小兔的前腿動一下,雙眼射齣兩束清清涼涼的光,我便把鐮刀朝它眼珠砍下去。從這眼珠進去,從那眼珠齣來,還又紮進麥田一半。當我拔齣鐮刀時,有一顆眼珠,晶瑩透亮,如一兜兒清水,吊在鐮刃上,在日光下閃閃發光。它終於死瞭,再也不那樣看我瞭。我的鐮刀在它身上進進齣齣,自由自在,仿佛小刀在一片一片削著黃瓜。血味十分新鮮。空氣也跟著潮潤起來,如深鞦早上村鬍同中流溢的白色氣息。至尾,我停刀細看,小兔不見瞭,麵前隻有一堆肉醬。還有四條小腿,齊齊全全,伸在肉醬一邊。我端詳一陣,發現很像四條貓腿,想分齣差異,終是沒能找到,就舉鐮將這四腿劈瞭。兔腿骨在鐮刃上哢哢嚓嚓,聲音清脆艷麗,像支書開會時握手關節的聲響。我看見過支書握關節,四個手指,砰砰砰砰,像四聲槍響,最後,大拇指“啪”的一響,總結瞭。我想用鐮刀把兔腿割下來,又嫌血醬上泥土麥粒太多,就用鐮刀在兔頭上一穿,提起,用力一摔,死兔割著日光,朝田頭溝中飛去,天空中哩哩啦啦,留下一條溫暖紅綫。
我立下,等著聽兔醬沉入溝底的聲響。
“連科——乾啥?”
這是三姑女的聲音,我木木轉過身子,見村長傢三姑女站在我身後路上,手裏提一個瓦罐,便凝望著她不動。
“你乾啥?”
“不乾啥。”
“喝水吧?”
“不喝。”
“不渴?”
“渴。”
“來喝吧……我又沒得罪你。”
我朝三姑女走過去。忽然感到我的嗓子乾裂得見火就燃。她站在一團樹蔭下,自己也像一篷涼陰。立馬,我身上缺瞭氣力,想倒在樹蔭下喘息。到她麵前,抱起水罐灌滿肚子,我就把自己扔在地上。她挨著我身邊坐下來。我看見麵前天空,有一朵白雲,像一塊白綢移動。我問她,你不割麥?她說割完瞭。我說這麼快?她說有人幫著割。我笑笑。
“到底你爹是村長。”
三姑女瞟我一眼。
“我爹對你不好?”
“好……好也不會把村長的位置讓給我!”
“你那麼想當村乾部?眼下種地也一樣過日子。”
“一樣過日子……那你去縣化肥廠當啥工人呀。”
她把目光從我身上移開去,盯著麵前槐樹。一個一個蟲包,吊在半空,東蕩西蕩。“我迴來瞭,被人擠掉瞭。”她頓一下,又道,“爹在村裏是村長,齣門也是百姓。花瞭三韆塊錢,我照樣迴來種地。對象看我又迴農村,說咱倆的事咋辦?我說不牽纍你,吹吧。他說那就一刀兩斷,橫竪誰也不欠誰啥。我們就吹瞭。我就迴來瞭。”
聽著三姑女的話,我在下頦上拽瞭幾根鬍子,放眼前看看,扔掉,起身去倚著樹身,點點滴滴看她一遍,發現她比以前秀麗。我伸手拉著一根低矮槐枝,把身子半係空中、半站地上,晃來晃去。
“你想找啥樣對象?”
她用樹枝在地上劃著。
“不知道。”
我凝著身子不動。
“看我咋樣?”
她抬起頭來,樹枝僵在手裏。
“你看上瞭我哪?”
我說:“那你彆管。”
她問:“是長相?”
我說:“你長得不漂亮。”
她問:“是人品?”
我說:“你人品好?”
她說:“我知道你看上瞭我哪。”
我問:“哪?”
她說:“看上我爹是村長。”
我說:“對。看上你爹是村長。”
然後,就誰也不語。她起身,拍拍屁股上的灰。我又去抱罐喝瞭幾口水,把罐遞給她。她接過罐兒,放在一邊,去麥地邊的土裏踢踢,踢齣一塊鏡子,迴來說,我看半天,以為是啥兒。我道我們傢地裏不會有金條。她不接腔,過來學著我剛纔樣兒,雙手抓住槐枝,把自己半吊空中,盯著我看。
“看啥?”
“你長得好。”
“好你也看不上。”
“看上瞭……”她說,“有一天你當瞭村乾部、鄉乾部、縣乾部……你會對我咋樣?”
“可我當不瞭……”
“我爹不齣三年會把你拉到村委會。”
“三年……三年我都老啦!”
“這是大事,最快也得兩年。”
“兩年內辦成我憑著良心侍候你。”
“行。可咱得先結婚。”
“結婚?”
“我二十多瞭,要抱孩娃。”
“要結瞭婚你爹辦不成……”
“我在你們傢牛馬一生,侍候你,侍候你爹娘。”
“說死瞭?”
“說死瞭。”
“不變?”
“不變!”
“你哩?”
“也不變。”
“你不給你們瑤溝村人打商量?”
“用不著。他們會同意。”
“爹娘呢?你那隊長三叔呢?”
“也不用。誰也管不瞭我的事!”
“你連科是一個瑤溝的連科……”
“就是為瞭一個瑤溝我纔這樣兒。”
提上水罐,她轉身就走瞭。我在樹蔭下站定,望著她離去,忽然覺得事情很便宜,不值錢,幾句話我們就終身議定,仿佛過程太簡化。於是,我朝前追瞭兩步,把自己曬在太陽下。
“喂——我們傢可沒錢送彩禮!”
她扭轉身子。
“我一分彩禮不要,結婚時花萬兒八韆的,都不讓你們傢齣錢。可結瞭婚你要對我不好……”
“我是你孫子!”
“天打五雷轟!”
“行。可你爹要當真讓我進不瞭村委會……”
“你說咋樣?”
“他是我孫子,你天打五雷轟,每個瑤溝人都是你祖宗!”
她認瞭這話,又轉身走去。我注視著她的背影直到慢慢消失,然後,拾起鐮刀,朝麥田看一眼。麥浪一浪壓一浪,如湖麵漾蕩。又看遠處山脈,青青黛黛,再看頭頂高天,蒼老暗黃。接著,站在田頭,用力把鐮刀摔嚮天空。我看見鐮刀割破天空,留下一道一道光亮,心中立馬暢快。
滾你媽的鐮刀!
滾你媽的莊稼!
滾你媽的山坡!
滾你媽的黃天老日!
滾你媽的不絕的牛馬豬羊狗!
滾你媽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鄉間村野!
……
三
三姑女和我看的好日子是農曆八月十六,中鞦節過後一天。這一天在鄉間你不明白我明白,是黃道吉日中的上佳日子。八月十五姑女在娘傢圓月,八月十六月圓時,又到婆傢團圓。一人圓雙戶,婚後兩戶人傢和和睦睦,親親熱熱,相處至死都無缺。
村長傢住在田湖鎮正中,傢有三間新起的大瓦房,自然是農村改革以後新起的,磚鋪地,灰糊牆,木頂棚。正間牆下放條桌。條桌上七七八八擺雜物:電視機、收音機、針綫筐、泥香爐、茶水瓶、少角鏡,還有一本被撕瞭一半的啥書。也許是早年“四捲”中的哪一捲,也許是三姑女下學後不用的舊課本。最醒目的當屬條桌上方牆上貼的像——老壽星。老壽星占的位置很有曆史。在鄉間,解放前那位置一般歸屬他。後來,那位置歸屬毛主席,又後來,曾歸屬過一陣華主席。至今那位置就又歸屬他。他在那失而復得的位置上,頭頂肉疙瘩,手拄疙瘩拐,日日夜夜笑著享受。兩邊還有一副通俗對聯,一說你便知,是“壽比南山不老鬆,福如東海長流水”。這套東西,是國營新華書店專賣的,鄉間傢傢戶戶貼。
這就是村長傢中的風景。
村長心中一有事,就總默在屋裏看風景。
這一日,村長吸著煙,把風景看舊瞭,仍那麼死心塌地地看。兒媳說,爹呀你看啥?村長說去把三姑女叫來。三姑女就來瞭。屋裏僅存父女倆,兩個人對坐著,把空氣都坐成瞭死死闆闆硬塊兒。
姑女問:“有事爹?”
村長說:“沒啥事。”
姑女說:“沒事我去燒飯瞭。”
村長說:“讓你嫂子燒,你陪爹坐一會兒。”
於是,三姑女移瞭闆凳,坐在村長對麵。村長吸煙,有聲,每吸一口,眉間就鼓起方方正正一塊紅肉,像關瞭門的一間紅房子。每吐一口,那紅肉就分迴到臉上各處,如房門開瞭,一切都敞亮開朗。三姑女看爹吸煙,看完一支,又看完一支,纍瞭,眼往下一移,忽見爹的腰上有一紅點,隨著爹的動作,影影綽綽,仿佛時明時滅的紅星星。三姑女疑惑,過去撩開爹的衣襟,原來是係在腰帶上的一段紅布條。
“乾啥爹?”
“你娘說避邪。”
“避啥邪?”
“都是迷信。說今年男人災多,明年女人災多。”
“你也信?”
“我咋能信?好歹你爹是村長。”
“那你咋還係?”
“反正又不沉。”
三姑女又坐迴原處。有瞭這話題,村長就想到瞭該說的一件事。他把煙頭在凳腿上擰滅,起身倒上一杯白水,又放半把白糖,把手中留的幾粒抖進糖瓶,把指頭塞嘴裏嘬幾嘬。
“給爹實說,”村長道,“你到底喜愛連科哪?”
三姑女瞟一眼爹,“哪都喜愛。”
“可爹哪都不喜愛。”
“他日後準會有齣息。有一天他進瞭村委會,慢慢村委會就成瞭他的村委會,村子就成瞭他的村。”
“那時候你爹和支書都成他鞭子下的老牛啦。”村長說,爹也看齣他連科有能耐,可他心太陰。說昨兒天,我和支書去各生産組的田裏轉,看鞦莊稼收得咋樣兒,到伊河邊的大灘地,沿著大渠的旁兒走。那時候,鞦水嘩嘩流,深處能夠淹死人。我和支書一前一後,說說話,天氣好,風涼爽,渠邊腥鮮香濃,不知不覺就走到連科傢責任田頭。他正在拿鋤刨玉蜀黍茬,老遠見我們,就笑臉迎上來,喚伯叫叔,又熱情,又懂事。因為支書正和我商量大隊成立一個手套廠,讓誰當廠長,話在熱處,就沒顧及彆的。他說支書,不坐一下?也許支書壓根沒聽見,徑直從他麵前過去瞭。他又叫瞭一聲我,我也哼一聲就走瞭。這種新親戚,哪有話兒說?可你猜咋?無法無天啦!我們走齣好遠,我聽到身後有動靜,迴轉一看,他連科把鋤架在肩上,將鋤當槍瞄,一會兒瞄支書的腦殼,一會兒瞄我的腦殼。我說你乾啥?他把鋤往地上紮,說你們就是這下場!我想摑他一耳光,要是在幾年前我就捆他一繩子。可這時,支書扭迴頭,不小心一腳踏空,掉進瞭水渠裏。水有齊腰深,凍得嘴哆嗦。彆的群眾一見支書落水,都忙不迭兒救,可他往玉蜀黍地裏一鑽,扯著嗓子喚,打住瞭一隻兔子!打住瞭一隻兔子!到末瞭,把支書拉上來,我朝那地方看看,發現是誰用鋤把渠旁挖空瞭,等著我或支書跌進水。你想想,這麼乾的除瞭連科還有誰?
話畢,村長望著三姑女,“連科是壞傢夥”的錶情烙在他紅銅色的臉皮上。
“這事齣在昨兒天?”
“昨兒後晌。”
“昨兒後晌我和連科一道收拾新婚房……”
“記不太清時間啦……也許是前天。”
“前天一整日我們去訂做新傢具。”
“大前天連科乾啥?”
“不知道。”
“那事情就該齣在大前天……對,就是大前天。”
“爹,我冷丁想起來,大前天連科和我一道進城購嫁妝。我們買瞭蘇州被麵、上海床罩、太平洋床單、鈞瓷蓮花菜盤……統共花瞭2300塊錢。”
“咋?你不信連科能乾這種事?”
“信。村裏除瞭連科彆人乾不齣。”
“信就成瞭,彆管事情齣在哪一天。”村長說著,把目光從姑女臉上移開,投到老壽星的臉上去。這時候,陽光鮮鮮活活,鞦風蹦蹦跳跳進屋來,老壽星的蒜頭鼻在日光中窩著一團塵灰,村長拿布擦瞭,迴來說姑女。
“你真願意嫁連科?”
“村裏沒有誰比連科更閤適。”
“村外有。”
“誰?”
“新調來一個副鄉長,他孩娃今年二十四,想在咱村討媳婦。”
“叫啥?”
“不知道。”
“人啥樣?”
“也還不知道。”
“哪村的?”
“詳細是哪村還沒顧上問。”
“那你知道啥?”
“副鄉長馬上就要當鄉長。”
“他當鄉長又不是他孩娃當鄉長!”
這句話從三姑女嘴裏爆齣來,她一甩手,捷步齣瞭屋子。村長在一聲聲叫著,也不答不理,仰頭長望一陣高天,說今兒天氣真好,便徑自朝院外走去。傢狗在她身後,嬉笑著咬她褲角。
望著姑女背景,村長把那杯糖水潑地,說,媽的翻天啦,屁猴都想從如來手中跳齣來!話完,他將空杯往桌上砸,迴屋躺床睡瞭。
時日如水,一天天潺潺流過,有聲有色。期間,支書去過一趟縣城,迴來問村長,說三姑女事情咋樣?村長說不咋樣。支書輕看一眼他,你連姑女的事都管不瞭,還咋管一個村的事!村長說三姑女死倔。不會想個法兒?言言講講,兩人在村委院椿樹下議計一晌。村長迴來罷瞭夜飯,脫衣上床,把三姑女叫到床前,從衣兜掏齣一樣東西。三姑女接過東西。是手巾包著的一件硬貨,打開來,裏邊又用紅綢包瞭,解開紅綢,又是一層綠綢,打開綠綢,是一層生白布……這麼一層一層,共解瞭七層,最後那東西就亮在三姑女手裏。三姑女望著那東西,先還不覺如何,後就臉色漸白,先從嘴唇開始,直白到脖兒。且額上還有細細汗珠,在燈光下晶明。繼而她的雙手,開始微微抖動,那東西在她手上晃擺,綢布吊在手上,像水樣漂動,最後,就終於有瞭淚,在眼邊生著。
村長說:“包上吧。”
姑女說:“哪來的?”
村長說:“你彆管。”
三姑女瞟爹一眼,臉上掛著悔悟,青紫淡淡,像一層早霜。她雙牙咬唇,穩住情緒,一層一層又照原樣包瞭手中東西,起身去給爹倒瞭一杯水,實實在在放瞭一把白糖,用筷子攪勻,敬到爹的麵前。
村長沒有接水,看瞭一眼桌角。
三姑女把水放在瞭床頭桌角,爹一伸手即可拿到。
村長看瞭一眼屋門。
三姑女去把屋門掩瞭,迴來又把裏屋簾子放下。
村長看瞭一眼凳子。
三姑女手托那樣東西,端端正正坐在凳上。
“和連科的婚事……”村長盯著三姑女的臉。
三姑女低頭看著手中包瞭七層的東西,“聽爹的。”
“爹說吹瞭。”
“吹瞭吧。”
“和副鄉長傢孩娃……”
“聽爹的。”
“爹說訂瞭。”
“訂瞭吧。”
至此,村長起身從床頭摸齣一包煙來,吸瞭一支,屋外這時開始落雨,嘩哩啦、嘩哩啦,打在新屋青瓦上,像落豆子。一時間,天也開始陰冷,屋裏燈光明鋥,村長的煙頭在燈光中如將熄的燈頭,然卻總是保持原樣,似乎永不熄滅。好在終於還是滅瞭。他又端起水來,未喝,冷三姑女一眼。
“那東西咋辦?”
“聽爹的。”
“埋瞭吧,撿個好地場。”
三姑女緩緩站起,撩開布簾走齣。雨滴砰砰砸在臉上,地麵水亮水亮。傢狗沒有進窩,在院中淋雨,看見三姑女齣來,它上前用舌頭舔著她的腳腕,腔裏哼齣一種莫名聲響。三姑女用手撫撫狗頭,那狗就臥在門口不再動彈。房簷水跌在狗頭上,像捶鼓般響亮震耳。三姑女彎腰護著手中東西,到院中央看看天色,拿起一張鐵鍁朝後院走去。
村長傢裏兩截院落。後院落半畝有餘,空空蕩蕩,有幾棵泡桐樹在雨中喚喚叫叫,吵吵鬧鬧。兩畦鞦菜則在雨中安靜睡下,任雨水擦洗。三姑女冒著雨,把那東西放在簷下乾處,到後院中央挖下一個深坑,約為寬尺深米,把那布包東西埋瞭,找些樹葉撒上,覺不妥,用一捆玉蜀黍稈散亂扔在上方,然後就坐在稈上哭起來,聲音喑啞嘶嘶,其實極揪心裂肺。雨水和著淚水,從她臉上澆下。有一隻鞦蛙,在她麵前水中,仰頭迷惑地看著,如看一場淒慘大戲。蛙的雙眼,圓圓亮亮,如兩粒落地星星,灼灼閃閃。這時候,有風走來,自西嚮東,又扭嚮西南。三姑女渾身濕透,她感到水從她衣上落下,滲入黃土,流入地下,終於淹瞭那七層布包裏的東西。後院此時奇靜,除瞭雨聲,彆無一絲雜音,仿佛萬物死盡。
她聽到爹的咳嗽聲,很微弱,便起身往前院走去。
進屋。
“埋瞭?”
“埋啦。”
“在哪?”
“後院。”
“還有一件事忘給你說瞭,副鄉長傢孩娃長得不好。副鄉長傢男女孩娃長得都不好。”
“不好就不好。”
“那去睡吧。”
三姑女就去睡瞭。三姑女一夜未眠。
她爹睡得很香實,有鼾聲陣陣,彌漫在屋裏,淹沒瞭傢中一切風景。
鞦雨連綿,一夜未斷,招引著白露時節。
白露走後是鞦分。鞦分將和寒露、霜降一道來。那時節,地下埋的東西都將不見瞭。
· · · · · · (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