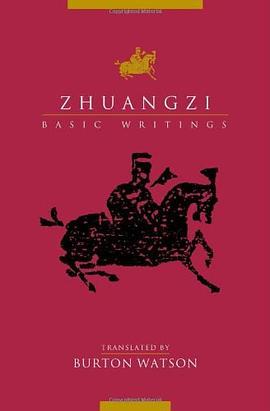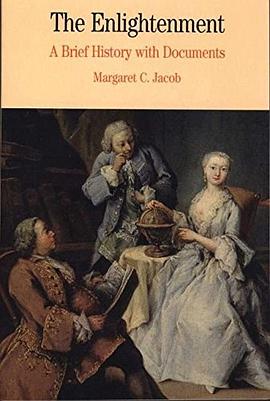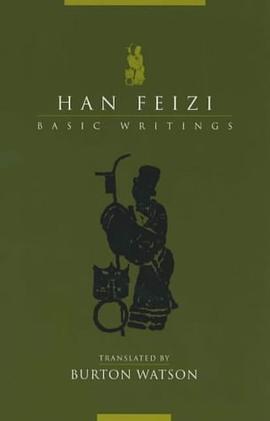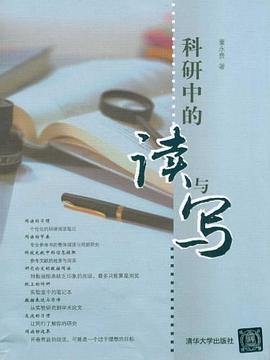具体描述
徽州文书被誉为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等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它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的交往过程中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是徽州历史、文化、社会发展以及生产、劳动、商业、社会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状况的最真实、具体的反映,具有唯一性的特征。
《徽州文书》(第一辑)共10卷,影印了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和黄山市祁门县博物馆所藏徽州文书5000余份。这些文书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发现的,其最大的特点是突出文书的归户性:以户为单位,以文书本身产生和形成的自然顺序编排。第一卷~第五卷收录了“伯山书屋”藏黟县文书十户,第六卷~第十卷收录了祁门博物馆藏祁门文书五户。
《徽州文书》是我们进行中国传统社会多维实态研究的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献学等领域都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前 言
——徽州文书的遗存与整理
刘伯山
徽州文书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发展与交往过程中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它是徽州历史、文化、社会发展以及生产、劳动、商业、社会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状况的最真实、具体的反映。其大规模的发现并获得确认最初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事,当时就发现有近10万余件,其数量之多,研究价值之大,曾被誉为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 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极大影响。之后,徽州文书还在不断发现,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徽州文书的发现几乎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数量不断在增多,徽州文书的抢救工作仍在进行。
一、徽州文书遗存的数量
徽州文书遗存至今的数量到底有多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徽州文书类目》推测是“流传至今的徽州文书的总数当不会少于20万件。” 这一推测,指的是“流传至今”的徽州文书总数;而周绍泉先生在《徽州文书与徽学》一文中的估计是“已被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收藏的徽州文书,以卷、册、张为单位计算,恐怕不下20余万件。” 这一估测,指的是“已被”“收藏”的徽州文书总数。
实际上,关于徽州文书的数量问题,笔者认为至少有五个层次的概念需要区分:
其一是徽州文书本身的数量。这是指历史上所有真实形成的徽州文书的数量全部,可以说它数量之巨大是今人乃至后人永远都无法统计与估测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其数量远远大于以后遗存和已发现的数量。
其二是遗存下来的徽州文书数量。这是指经过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而被徽州人一代代地保存、保护下来,至今还客观存在的徽州文书的数量,它们有的已被发现,有的还未被发现,其未被发现甚至是包括一些文书的客观拥有者其主观上也不知它们的存在,因此,其真实的数量,至少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是无法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它的数量必然大于已发现的和已收藏的数量。
其三是能够发现的徽州文书数量,它包括已发现和尚待发现两种情况。“发现”是个主体性很强的相对概念,它应具有被积极的主体寻得、确认价值、社会认同等几个方面的属性要求。所谓已发现的徽州文书是指已经获得并得到社会的确认与认同、已经或可以进行研究的文书,它的数量一般是可以确定的;而尚待发现的徽州文书则是指目前还不为人们知晓但通过努力可以发现的文书,它的数量到底有多少,难以确定,但一般地,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摸底予以估测,至少可以确定一个上下限。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能够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数量总是要大于已发现和已收藏的数量。
其四是已发现的徽州文书数量。这又包括过去已发现了的和新发现的两种。所谓过去已发现了的徽州文书往往是指已发现且已被登记收藏的文书,它的数量应该说是比较确定的;而所谓新发现的徽州文书则是指暂时还没有被收藏单位登记收藏但已获得社会确认其存在的文书,它的数量尽管还不能十分确切具体,但也能大致确定。应当指出的是,已发现的徽州文书未必就是指被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组织收藏的文书,还应包括一些个人收藏;同时,已收藏的徽州文书也未必就等于已经发现并得到登记公布的文书,这其中还存在了一个再发现、再公布以期成为新发现的问题,特别是一些个人的收藏,如果得不到公布,则社会无法知晓。实际上,不管是单位还是个人,其收藏的徽州文书如果得不到社会认同与采用,则永远是潜在而非实在的,无法归入已发现范畴。由之则又可以肯定,已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数量必定是大于已收藏登记及公布的徽州文书的数量。
其五是已收藏登记和公布的徽州文书数量,这又包括组织结构的收藏登记和民间个人的收藏公布两种情况。被一些组织结构收藏登记的文书,其数量是明确的;个人收藏的文书,只要其公布,数量也应该明确。因此,在以上五个的徽州文书数量的概念中,只有这个概念的数量理论上最为确定,但数值量也最小。
那么,到底至今还遗存的徽州文书数量是多少呢?应当说明的是,对徽州文书的统计,由于过去一直没有严格的进行,且没有统一的统计标准,因此,所有的数字都应是大概的估测。这里我们姑且依周绍泉先生依据的“以卷、册、张为单位”计。根据上述意见,《徽州文书类目》的作者推测“流传至今的”徽州文书的总数不少于20万件,缺乏根据,因为这一数字,正如上文所说,我们无法估测;周绍泉先生所估测的“不下于20余万件”的数字当是指已被组织机构收藏登记和公布的徽州文书数量,这是根据他的调查与摸底而得出的结论,其主要依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收藏有一万四千余件,黄山市博物馆收藏有三万多件,南京大学历史系收藏有近五千件,严桂夫先生主编的《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中公布的安徽省各级档案馆系统收藏有九万多件等等,据笔者掌握的材料看,这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但问题是,这个数字仅是2000年以前甚或是更早时间的数字,至少是其中没有包含一些民间个人收藏的数量,因此,还远不能反映徽州文书遗存的真实情况。
笔者认为,徽州文书遗存至今的实际数值是远超过20万件的。一方面,就已发现的徽州文书看,其数量除了我们已知的有20万件左右外,近几年来新发现的还在不断涌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是1999年底以后才建立的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其作为特藏室之一的“伯山书屋”所藏的徽州文书系笔者2001年5月19日正式捐献的,共计一万一千多件,其中明代以前的有近二百件,最晚的一份是1984年的。 它们均是笔者2000年6月份以前在黄山市工作期间历十二年时间于原徽州六邑的民间收集获得,当属新发现的徽州文书,并且这项工作还在继续,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祁门县博物馆也藏有万余件的徽州文书,据笔者的调查,绝大部分也都是在1994年以后获得,并且过去一直没有公布,亦属新发现;黄山学院图书馆过去很少有徽州文书,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加大了徽州文书的收集力度,至2004年10月,所获徽州文书原份已近四万份。黄山市档案馆系统2000年以来至2004年10月也新征集徽州文书六七千份等。民间一些个人手上收藏的文书也不少。据笔者所知,目前个人收藏徽州文书超万份的至少有两位。一个是笔者本人。2001年5月笔者捐献给安徽大学的徽州文书是2000年以前所收集到的文书,这之后,笔者仍在以个人的力量努力地抢救着徽州文书,至2004年10月,至少又收集到徽州文书三万多份。再就是上海有一位学者,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在收集徽州文书,至今已达到万份左右。收藏徽州文书在一千份至五千份之间的至少有六位,主要分布在黄山市和合肥市。收藏徽州文书在五百份至一千份之间的有十位,主要分布在黄山市、宣州市、广州市、北京市、苏州市,其中还包括一位学者日本。至于收藏徽州文书在百余份的则更多,其人数至少有三十余位。因此,初略的估测,至2004年10月至,个人收藏者手上收藏的徽州文书总量当在七万五千份左右,它们都将会暂时留在收藏者手上,保持一定的收藏稳定性,并且迟早会得到公布和开发利用,应属新发现的徽州文书。总之,依笔者的估测,到2004年10月止,新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总数当在15万份,因此,已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数量实际是达到35万份。
另一方面,就能够发现的徽州文书看,目前还散落在民间的数量还十分可观。它主要有三种分布:第一种是,由于徽州文书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大量流入黄山市的街头,而黄山市作为一个有国际性影响的重要旅游城市,每年又有大量的海内外游客,他们中有许多是出于好奇和把玩而购买徽州文书并带走,其数量多少不得知,至少的估测当在万份左右。第二种是一些社会商贩手上拥有了不少文书。它们大多是近些年在徽州乡间农村获得,最终是要进入买卖过程之中,许多人囤积,无非是要寻得一个好的买主,其数量粗略的估测也当在万份左右,不知以后花落谁家。第三种是到目前为止还藏在文书户主家里的徽州文书,其数量,据笔者积十几年收集抢救徽州文书的经验及对所获文书数量的地理区域分析情况看,目前还保存较为完好、可资研究利用的,至少的估计也还有8—13万份。它们是彻底地散落分布在民间,依然掌握在徽州人的手上,而这些徽州人,有些是知道自己拥有了自己家庭、家族的历史档案,有些人甚至还不知道。这些文书的归宿,一部分是徽州人自己要留住,至少原件永远留在民间;大部分恐怕还是要流落出来,不知飘向何方。
总之,依笔者所见,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数量当至少不下于35万份;还散落在民间、可资研究利用的徽州文书又该有10—15万份,两者相加就是45—50万份。这是不是徽州文书在今天遗存的全部,无法肯定,但至少是理论上我们可以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数量,由之,也可知徽学这门学科得以成立的基础厚实。
二、徽州文书的特点
徽州文书是一种民间档案的遗存,它是由历史上的徽州老百姓在其具体的和实实在在的生产、生活及社会交往过程中自发地、真实地形成与产生的,产生之后又是作为了一种与自己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家庭档案而保存下来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因此,真实性应是徽州文书首先具有的本质特征之一。
徽州文书是一种历史实态的直接写照,这种直接的写照甚至是不加修饰的,是作为了一种原始事件、事态以及情态、心态的直接和最初的反映。正史、野史、小说、笔记等等,往往是由某人,以自己的视角和眼光而进行有选择的记录与描写,从而还只是作为了一种客观对象二次反映的历史副本,还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实态。徽州文书则是完全地历史实态的一次反映,尽管它也是以一种文字形式的东西而存在,但这种文字所反映的内容是努力地与所要反映的对象保持一致的。如一份土地买卖契约,其卖者必须将所卖土地的来源、四至大小等交代清楚、价钱注明,并且还要明确是大卖还是小卖,这些都是不能有错的,必须十分明了、属实,并有画押,才能成约,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如果没有真实性,文书也就无法形成。所以说,徽州文书都是当时、当事和当人的,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每一份徽州文书,除去历史保存的因素外,其现在是这个样子,当年也就是这个样子。即使是有些文书是属于所谓的“抄白”,表象上看,仿佛已不是所抄内容原载文书的原件,但由于这“抄”的事件本身是历史的和真实的,抄白文书本身也是原件,所抄内容基本与原件相符,甚至在格式上都能保持一致,因此,真实性还是存在的。
徽州文书的真实性,必然决定其存在本身的唯一性。徽州文书除了一些印制的官府票证如“清丈单”等和商家印制的宣传广告单等外,绝大部分都应是各个明确的“这一个”,每一份都是唯一的。尽管有些文书,如合约、公约类的文书,往往是一式几份,多的时候达一式几十份,仿佛不是唯一的,但每份文书都有画押,而每一个的画押都是唯一的,并且如果是一式多份,其多份的具体数量都是要在文书中注明的,是多少就是多少,一点也不含糊这是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它的唯一性。存在上的唯一性或许就是文书档案区别于一般历史文献的地方。狭义的文献,如刻板印制品,往往是多存在并存的,即使是所谓的孤本,也只是因为遗存的原因而成为孤本,其最初的产生及存在还是数量大于一的。徽州文书就不一样,它的产生就是唯一的,如果有相同,则必定有假。抄白的文书是一种对原文书的复制,但这种复制是一种没有当事人画押的复制,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并且,即使是作为复制行为的抄白,由于所抄的往往只一份,每份抄白本身都是各个的具体历史行为所致,因此,仅就这份的抄白本身来说,它还是唯一的。徽州文书的唯一性是对其真实性的另一种说明,它们两者的一体,构成徽州文书在存在上的本质特征。
除此之外,就我们已发现的徽州文书看,其在整体上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1、内容极其丰富,文书形式多样。
徽州文书是徽州社会历史的综合反映,所涉及的面是非常广的,内容极其丰富。从目前已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情况看,它们所涉及的内容既有田地、山场、房屋、店面、树木、池塘、牲畜等等的大小买卖文约、招承租约;也有宗族文书、立议合同书、阄书、继书、招书、遗嘱、诉讼文书、赋税票据、赋役文书、官文、告示、会书、信函、家乘宗谱、祭文祭礼、誊契薄、收借条、记事簿、日记、账单账本、收租薄、黄册归户册、实征底册、归户清册、鱼鳞图册、礼单、货单、支用单、鸳鸯礼书、工尺谱、曲本、戏本、诗联集、乡音字类、风水图册、各种日用类书等等,所涉范围近乎包括了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间交往及习俗、信仰等各个方面;所涉文书形式,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归纳,仅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藏的一万四千余件的徽州文书就分有3种9类,117目,128子目, 而依笔者所见,其类目还应再多,其形式近乎是要包括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农村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所应形成和产生的文书形式的绝大部分。
敦煌文书是敦煌学支撑的重要基点,目前已知遗存的有六万件左右,其中佛教经典方面的文书就占有近五万件,所谓的社会文书只有万份左右。而徽州文书,其绝大部分是社会文书,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研究的空间很大,价值极高,或许这也是徽州文书的一个特点。
2,时间跨度大,持续的朝代多且系统完整。
从目前已发现和收藏的情况看,徽州文书已知最早的是北京图书馆收藏《南宋嘉定八年祁门县吴拱卖山地契》, 南宋嘉定八年即公元1215年,距今有近七百九十年。但据周绍泉先生考证,该契约是一件抄白而非原件,属于原件的徽州文书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当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收藏《淳祐二年休宁李思聪等卖田、山赤契》, 淳祐二年即公元1242年,距今有七百六十多年。较后的徽州文书,过去一般认为是到民国三十八年即1949年, 但黄山市博物馆就藏有1952年的文书,内容为休宁县漳梓乡乡长程巧云为本乡王有恒去景德镇代已故屋主收取屋租、纳税的证明;而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特藏室“伯山书屋”则藏有1984年的文书,为一份房产析分确认合约,其房产的最初析分是几十年前的事,房产的来源则更早。 因此说,目前已知的徽州文书原件,其时间跨度至少有742年,历经宋、元、明、清、民国(含洪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明代以后的文书,则是各朝各代应有尽有,极为完整。
敦煌文书目前已知最早的是东晋永和九年(353年)的,晚的为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唐朝的文书最多;而徽州文书则是从南宋直至1984年,明清的文书最著。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在年代上存在一种自然连接,总跨度有1631年,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3,连续系统,有很强的归户性。
这是徽州文书一个极其有价值的特点。徽州文书是历史上真实形成的东西,其最初的形成当有明确的归户指向,而得以妥当保存至今则完全在于其归户性。任何徽州文书除少数官方文书等外,基本上都应当有其归户的特性,甚至官方文书等也应具有归户归类指向。所属归户性,一般意义上说就是属于性,归户的文书亦即是属于谁的或由谁拥有并作为档案保存的文书。这类的文书,其每一份都应是与归属的主体之间存在某种密切联系,有着一定内在关系的,其得以保存也正是在于它于归属户来说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由之才得以构成“家庭档案”。没用的东西都扔了,留下的东西必当有些用。这一简朴的道理也就是徽州文书得以遗存的一个真理。归户性就是徽州文书本身具有的一个重要特性,我们现在之所以有许多徽州文书的收藏单位,其收藏的文书难以确定其为归户,问题不是出于文书的历史产生和历史遗存本身,而是出在其收集、整理和保存管理环节上。原本是归户的文书,收集的时候没有合户收集,而是逐件挑选,导致归户性缺失;整理的时候又不是一户一户的整理,而是人为打乱,导致归户性丧失;保存管理上又不注意一户户的分开保存管理,而是笼统置放,导致归户性流失。这些遗憾都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教训。
归户的文书其份数一般是大于1的,年代上总是存在一定的跨度,种类也比较繁多,各文书之间基于归户主体来说,还都应该是存在某种的联系,历时性上,它们存在一定的连续;共时性上,它们存在一定的关联,从而构成了一个整体,并且正是这种整体性的存在才更为体现了其真实性,反映的是多维空间的历史实态。一户的文书往往就是这一户家族变迁发展历史的真实记录与写照。实际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从目前我们已发现的徽州文书情况看,归户的文书往往是几十份、一百多份、几百份甚至一千多份为一体的,时间跨度上一般是历一百多年或几百年而连续,有很强的系统性,个案研究价值极高。
如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伯山书屋”《黟县五都四图榆村邱氏文书》共有300多份,系笔者1998年—2000年在黄山市分三次从不同的人手上获得的,其最早的一份是明天启四年,迟的是民国后期,内容极其丰富,举凡买卖租典契约、合同公约、收借条、分书遗嘱、账单账册等等皆有,种类繁多。三百多份的文书,内容上许多是连续有关联的,举其一份土地买卖文书看。道光二十二年六月,黟县五都四图榆村的邱三赐曾买了一个叫胡履丰的人所卖的一块风水地,形成了一份赤契。这份赤契是包在一张包契纸里的,在同一包里还有另外三份契约,分别是:明天启四年三月初十日胡奎卖风水地与程氏赤契,在这份契纸的对折另一面还写有一份立推单;道光十一年十二月程百达等卖风水地与叶名下赤契;道光十五年十月叶赏龄卖风水地与胡名下赤契。包这四份赤契的包契纸正面注有:“天启四年六都胡姓卖与程姓名下契一纸已印无尾 道光十一年五都程姓卖与叶姓名下契一纸已印粘尾 十五年五都叶姓卖与胡姓名下契一纸已印粘尾 二十二年六都西递胡姓卖与邱姓名下契一纸但印粘尾 共计老新契四张土名马驼山风水地计契价银四拾两整 老推单新推单收税单均在内昆字号计三千七百五十八号”。原来是同一块地,曾转买转卖了四次,前后时间历二百多年,先是胡姓卖给程姓,后是程姓卖给叶姓,再后是叶姓卖给胡姓,最后是胡姓卖给邱姓,最终归邱姓所有,各次买卖的文书具在,并归户为邱氏文书,十分连续和系统。
又如《祁门十七都环砂程氏文书》是祁门县博物馆2002年1月从环砂程氏一位后裔手上一次性获得的,其数量竟达到1380多份(部),最早的一份是明代宣德四年(1429年 )的,最迟的一份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总跨度为502年。2004年7月,经过笔者和所带领4个研究生对其进行的整理,发现这应是一户与祁门十七都环砂程氏宗族本身有密切关系的家族文书,尽管我们目前还不能确认它就是宗族祠堂文书,但至少是可以知道这户文书的拥有主人,历史上一定有几位与宗族祠堂有密切关系,可能是族长一类的人物,其文书反映的 也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的兴衰发展史。
正因为徽州文书有上述特点,因此,它不仅在徽学研究的领域意义重大,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献学等领域也都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美国学者约瑟夫·麦克德谟特在《徽州原始资料——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史的关键》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徽州文书是研究中国封建后期社会史和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料。” 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则更明确提出:“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庞大的资料的存在,使得对以往分别研究的各种课题做综合性研究成为可能,这些课题如土地所有关系、商工业、宗族和家族、地域社会、国家权力和地方行政系统、社会地位和阶级以及思想、文化等。这些资料是延至民国时期的连续不断的资料,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前近代社会和近代社会连续不断的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变化的重要线索”。“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经济、文化和探讨其发展规律方面,徽州文书具有很大价值,起着任何东西无法替代的作用。” 国内则有学者认为徽州文书的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笔者认为,对徽州文书进行研究至少是进行着一种中国后期传统社会的农村实态研究,籍以可了解与弄清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其后期传统农村社会变化发展的多维真实情况,具有不可替代的 研究价值和深刻的意义。
三、徽州文书的整理
1925年,王国维在总结概括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这四大发现时,曾经说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 在《故史新证》里,他又说“我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既然徽州文书在多学科领域都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我们除一方面要要进一步地做好徽州文书的抢救收集外,另一方面就是要对已发现的徽州文书进行很好地整理与公布,充分的开发、利用好这一宝贵资源。
应该说,过去我们在徽州文书的整理与公布问题上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傅衣凌先生就注意发现并整理公布了徽州文书资料,1960年,曾发表了《明清徽州庄仆文约辑存》一文。 从1983年开始,安徽省博物馆就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经济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共同协作,对安徽省博物馆和原徽州地区博物馆所藏的徽州文书进行编校整理, 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徽州文书资料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集,收编文书950件;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校出版的资料集的第二集,收编文书697件。
但真正在学术界造成极大影响的还是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整理,花山文艺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它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徽州文书,宋、元、明代的,挑选散件1800余件,簿册43册,鱼鳞图册13部,编成宋元明编20卷;清代和民国的,挑选散件1400余件,簿册79册,鱼鳞图册3部,编成清民国编20卷。两编共达40卷。这也是徽州文书第一次大规模地、系统地向学界和社会影印公布,其造成的影响,正如编者所相信的那样:“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推动徽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之后,徽州文书的原始资料的整理公布工作相对停滞,整理与出版的主要是文书类目。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张传玺主编的《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收入了一些徽州文书;1996年,黄山书社出版了严桂夫先生主编的《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共收入安徽省档案馆系统等收藏的徽州文书类目9600条;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了由王钰欣、罗仲辉、袁立泽、梁勇编的《徽州文书类目》,其条目所收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收藏的徽州文书,总计14137件(册)。直到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陈智超先生在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三卷,才既研究又影印公布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归户的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余封,堪称幸事。而恰恰是在这一段时间内
目前已经整理公布的徽州文书只占已发现的徽州文书中的极小一部分,还有大量的文书特别是大量属新发现的文书还不为人知晓。“学术乃天下共器。”徽州文书既作为珍贵的、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其就应当得到尽快、尽好地整理与公布,以使它充分体现价值,发挥应有的作用。本于此,我们依托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借助该中心的重大课题《新发现的徽州文书整理》项目,首先重点对新发现的徽州文书进行整理,并努力地在此整理的基础之上,将它影印出版,以让更多的徽州文书天下共器,为徽学事业同时也是包括了整个的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作贡献。
十分幸运的是,我们这项工作得到了许多徽州文书收藏单位及个人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全力配合和共同协作。从2004年6月份开始,这项工作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由于徽州文书在整理上工作十分艰巨,每一份文书的整理都存在着识读、定名、归类等诸多难点,加上它的收藏量大,收藏单位多,因此,其整理和影印出版工作我们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而只能是分期、分步进行。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和祁门县博物馆所藏徽州文书的整理及影印出版是我们的第一期工程。它又将分为若干辑。第一辑收入的是归户的文书,共计十卷。其中“伯山书屋”所藏徽州文书编成五卷,祁门县博物馆所藏的徽州文书编成五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安徽大学特聘教授栾成显、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程自信、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利、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陈联、胡中生和笔者及笔者所带的研究生等曾参加了“伯山书屋”所藏徽州文书的前期登记整理工作;后期成书的整理和拍照则是由笔者与笔者所带的四个硕士研究生完成,他们分别是安徽大学哲学系的2002级研究生吴丽丽和2003级研究生赵懿梅、王玮、李少华。祁门县博物馆所藏徽州文书的整理和拍照工作,是由笔者与祁门县文化局局长陈琪先生具体负责,参加人员有吴丽丽、赵懿梅、王玮、李少华和祁门县博物馆的章望南、陈国顺、裘霞飞、陈接农等。
本书的编纂是在安徽大学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祁门县政府暨祁门县文化局等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才得以完成的。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副校长韦穗等一直关心着徽州文书的新发现及其整理,并且本书编排了文书寻获记的创意就是在黄德宽教授的直接指导下才产生的;安徽大学特聘教授栾成显一直在指导着新发现徽州文书的整理,在文书的定名、分类等基本问题上曾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主任朱万曙、副主任卞利和张启斌及中心其他同志为本书的整理和编纂提供了全力的支持;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胡益民教授、安徽大学中文系的吴春华女士、黄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翟屯建副研究馆员、黄山市李俊工作室的李俊先生、黄山市人民银行的蒋毅华先生及中国科技大学的吴耀华教授、詹月红工程师夫妇等等都为本书的编纂给予了大量的帮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何林夏总编、宾长初博士和责任编辑朱荣所、蒋辉等曾直接参与了该书的策划,为本书的编纂和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等等。这些都是要感谢的。
由于我们学识水平和摄影技术水平有限,加上时间仓促及工作设备和条件的限制,在文书的识读和拟题上难免有错,在所摄文书的图片上难免不尽人意,还恳请大家不吝批评指教,以帮助我们改进。
作者简介
目录信息
一、黟县一都榆村邱氏文书附黟县一都汪氏文书,黟县十都卢氏文书
二、黟县二都四图胡氏文书
第二册
一、黟县二都查村江氏文书附黟县二都六图郑查邵户文书
二、黟县四都汪氏文书
第三册
一、黟县五都四图程氏文书
二、黟县八都三图查氏文书附黟县八都查氏等文书
第四册
一、黟县八都四图金氏文书
二、黟县八都燕川吴氏文书
第五册
一、黟县八都燕川吴氏文书续
二、黟县十都丰登江氏文书
三、黟县十都三图余氏文书
第六册
一、祁门八都邱氏文书
二、祁门十二都一图胡氏文书
三、祁门十七都环砂程氏文书
第七册
祁门十七都环砂程氏文书续
第八册
祁门十七都环砂程式文书续
第九册
一、祁门十七都环砂程式文书续
二、祁门二十一都一图陈氏文书
第十册
一、祁门二十二都红紫金氏文书一
二、祁门二十二都红紫金氏文书二
· · · · · · (收起)
读后感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用户评价
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该死的大部头,如果丢了,我真的真的赔不起,所以,我想,如果丢了,我就不回学校了
评分刘伯山老师已成为大神
评分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该死的大部头,如果丢了,我真的真的赔不起,所以,我想,如果丢了,我就不回学校了
评分清史土地问题的重要材料
评分刘伯山老师已成为大神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wenda123.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目录大全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