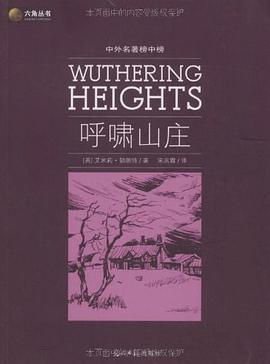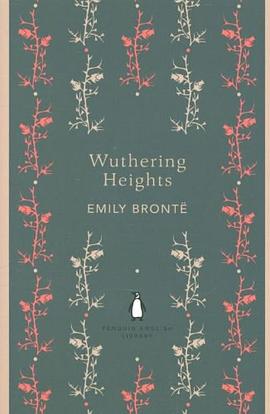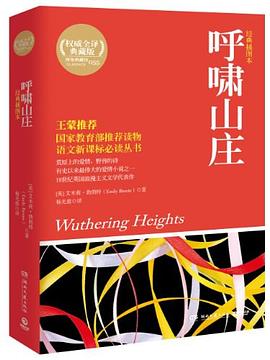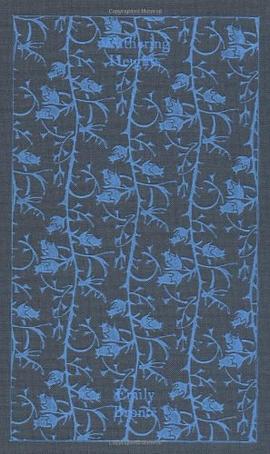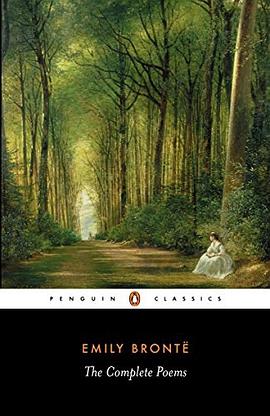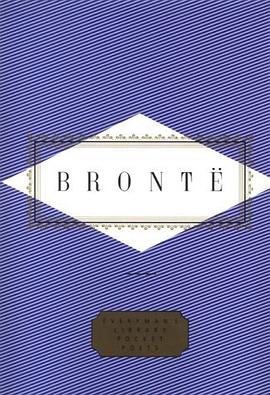呼啸山庄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之妹,安妮•勃朗特之姐。她出生于贫苦的牧师之家,曾在生活条件恶劣的寄宿学校求学。艾米莉性格内向,娴静文雅,从童年时代起就酷爱写诗。1846年,她们三姐妹曾自费出过一本诗集。《呼啸山庄》是她唯一的一部小说,发表于1847年12月。她们三姐妹的三部小说——夏洛蒂的《简•爱》、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和小妹妹安妮的《艾格尼斯•格雷》是同一年问世的。除《呼啸山庄》外,艾米莉还创作了193首诗歌,被认为是英国一位天才的女作家,三人并称勃朗特三姐妹。
- 艾米莉·勃朗特
- 英国
- 小说
- 外国文学
- 英国文学
- 经典
- 爱情
- 呼啸山庄

★献给每个人的永恒真爱纪念经典读物
★“暮光之城”灵感来源,作者梅尔读过不下百遍,汲取无数灵感,暮粉发帖热议的名著经典。
★ 风靡世界、长销不衰,中国最畅销的三本文学名著!
★ 暮光之城主人公贝拉和爱德华爱不释手的爱情小说!
★“暮光版世界名著”2010年出版后,在英美带动全年名著市场份额直翻3倍,成为当今欧美最流行最畅销名著版本!
★ 最永恒的爱情经典:“如果你不在了,无论这个世界多美好,它在我眼里也只是一片荒漠,而我就象一个孤魂野鬼。”
★ 毫不掩饰的浪漫:“我对林顿的爱情就像是树林里生长着的叶子。我明白,冬天来临的时候,叶子会随着时光而发生改变。我对希斯克利夫的爱情却是深埋地下的永恒不变的岩石,那是不可或缺的、弥足珍贵的快乐源泉。奈莉,我就是希斯克利夫!他永永远远在我心里。”
三、内容简介:
谁不曾年少?谁不曾憧憬?谁不曾真爱?
真爱是“意气的争执”(劳伦斯),也是“高尚的热情”(乔治•桑),是“丰富的资产”(泰戈尔),也是“道德中最大的秘密”(雪莱)……真爱埋藏在我们心里,刻印在我们记忆里,伴随我们长大,变老,直至永恒!
“真爱经典”第一辑精选了3部世界经典名著,这些伟大的爱情作品均为著名作家斯蒂芬妮梅尔心中永恒经典,珍爱无比。它们不仅给“暮光之城”的创作带来无数灵感,提供巨大影响,同时,也让更多读者重新发现经典作品的当下意义。就现代人的心灵世界而言,最远的有时就是最近的。
《呼啸山庄》是《暮光之城》系列主人公爱德华和贝拉最爱读的爱情小说,《呼啸山庄》里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之间强烈炙热的情感深深地吸引了贝拉,也恰好映照了她与爱德华爱恨交织的深刻感情。爱情时而缠绵悱恻,时而冷酷无情,永恒的爱恋超越了生死与世俗的偏见,谱写了天地间最动人的乐章。
当凯瑟琳和希斯克里夫随着一起成长,从童年的友谊变成了深刻的爱情,进而扭曲为对爱的复仇,最终生不能相守得以死后相拥,《呼啸山庄》便成为了世界上永远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即使命运与她们俩作对,双方爱的极致激情却反复地伤害着对方,都始终没有让他们真正分开,甚至死亡……他们的爱不可阻挡,无论世界如何改变,他们灵魂的材质独一无二,永远相同。
具体描述
读后感
很多次想起关于爱情,都是因为凯瑟琳她说,我就是希刺克利夫,他永远永远在我心里。想到,就会动容,就会黯然。 爱情的定义,是心动么,是温柔么,是无奈么。呼啸山庄里,爱就是天雷地火,生死相许,在凯瑟琳和希刺克利夫面前,许多的所谓爱情都黯然失色。动心,失望,...
评分从前,以为读《呼啸山庄》最好的氛围,是狂风闪电的暴雨之夜;现在忽然觉得,要在故事表层的狂野不羁中,品出最深处的宁静如水的悲凉,还是要在雪落无声的冬夜读。 呼啸山庄,其实是一个成长与背叛的故事。 成长本身,就意味着对纯美童年的背叛,和对丑陋成人世界的妥协。凯...
评分 评分 评分并不觉得男女主角之爱令人震撼 还什么爱情的绝唱之类的 似乎这爱多可歌可泣 不过是一个偏激的男人偏激的爱 并没显得这爱多伟大 吸引我的不是上一代的故事 虽然他们两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但那所谓"狂风暴雨"的爱并没那么高尚动人或者荡气回肠 这也叫荡气回肠啊 是他之...
用户评价
前期看着觉得有点神经病,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感情有点过于强烈了。最后希斯克利夫的复仇也有点让我觉得可以理解但也有点不带人性。然而但小凯瑟琳和亨德尔在一起,而且一切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时,我突然很感动,因为我感觉看到了曾经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可能,本来应该如此……最后希斯克利夫说是含恨而死,但我觉得他应该也想通了,释怀了。在雨夜中,三座坟墓下曾经一切那么强烈的感情,也归于平静。
评分用暮光之城宣传。。。 第一次读呼啸山庄比读百遍暮光之城感觉都深刻啊
评分借着暮光之城的宣传真让人无语。。。。。。
评分我爱你,因为你比我更像我自己。
评分If all else perished, and he remained, I should still continue to be; and if all else remained, and he were annihilated, the universe would turn to a mighty stranger: I should not seem a part of it.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wenda123.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目录大全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