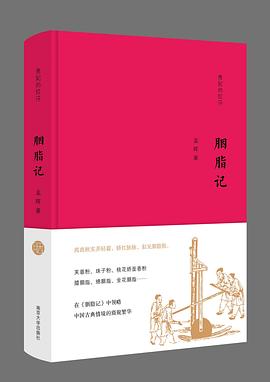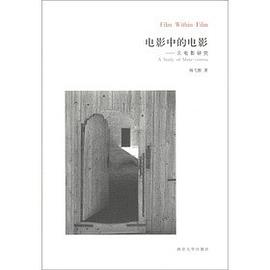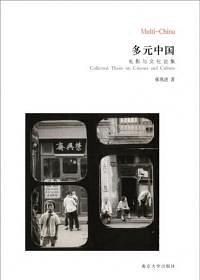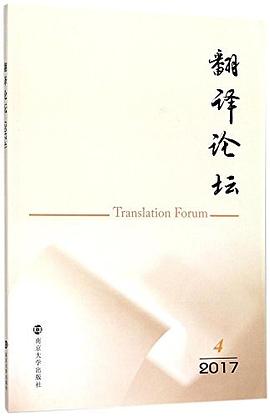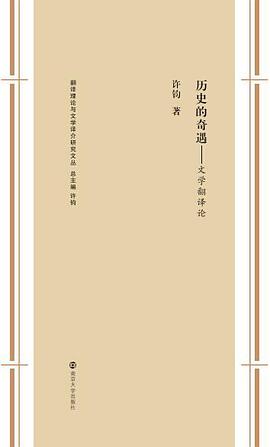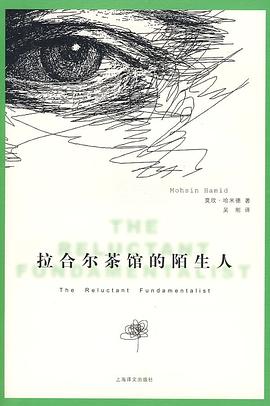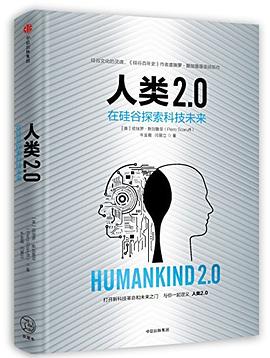具体描述
《东京记》分杂人和杂事两部分,收“安藤先生”、“田中老头”、“老朱同志”、“搭快车”、“看广告”、“上茅房”、“打领带”、“泡酒吧”、“图书馆”、“旧书店”等30多篇文章。
《东京记》由田川编写。
作者简介
田川,北京人,成长于宣武门。纪录片工作者,曾制作《回望梁启超》、《将军一去》、《满江红——抗战珍稀影像全纪录》等纪录片。香港《明报周刊》专栏作者,曾出版《四季日光》(港版)、《寻找英雄》、《草莽艺人》、《东京记》等。
目录信息
东京的表情(代序)
杂人
安藤先生
林义明
“发盘手”宫寺
田中老头
吉池老师
秋鸣
谷冢和玖
赵凡
佐藤邦彦
萧海
小萍姐
香蕉与大井
小栗
银座东急饭店人物志
新木场的人们
房东与邻居
一之濑教授
老朱同志
杂事
搭快车
吃寿司
贩卖机
看广告
搬家记
剪猫记
养乌鸦
逮蟑螂
上茅房
会错意
过马路
自恋狂
老地震
泡酒吧
看民主
常问路
图书馆
打领带
光膀子
李香兰
旧书店
后记
商品描述
编辑推荐
田川,北京人,成长于宣武门。纪录片工作者,曾制作《回望梁启超》、《将军一去》、《满江红——抗战珍稀影像全记录》等纪录片。香港《明报周刊》专栏作者,曾出版《四季日煳(港版)、《寻找英雄》、《草莽艺人》等书。《东京记》也是其随笔作品集,收录作品30多篇。
目录
再版序
东京的表情(代序)
杂人
安藤先生
林义明
“发盘手”宫寺
田中老头
吉池老师
秋鸣
谷冢和玖
赵凡
佐藤邦彦
萧海
小萍姐
香蕉与大井
小栗
银座东急饭店人物志
新木场的人们
房东与邻居
一之濑教授
老朱同志
杂事
搭快车
吃寿司
贩卖机
看广告
搬家记
剪猫记
养乌鸦
逮蟑螂
上茅房
会错意
过马路
自恋狂
老地震
泡酒吧
看民主
常问路
图书馆
打领带
光膀子
李香兰
旧书店
后记
序言
东京的表情
昭和老作家永井荷风在《江户艺术论》里说:“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消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木,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
我听了这样的话来了东京,总在有意无意间寻找这样的世界。在街巷里、人群中,这种江户的风韵若隐若现,又不太确实。永井荷风曾预言:“日本之都市外观和社会的风俗人情,或者不远将全部改变了吧。可伤痛的,将美国化了,可鄙夷的,将德国化了吧。”表面上确实如此:具体的利害。个人狭小的生活圈子。没有幻想,只有欲望。
一旦适应了工业社会的生活,好像所谓自由的、随心所欲的生活和空泛的情感没有了落脚处;所谓大气的、方方面面的、感性的,不过是走马观花,现代日本人像瞎子摸象一样,每人只满足于摸好大象的一部分。
可是,日本人又还是那些江户的日本人:吃鱼过多,敏感的心隐藏在冷漠的面孔下,成群结伙又保持距离。幕布换成了工业化,演员还是他们。在银座街头的Office Lady脸上,仍然可以辨认出永井荷风笔下的表情。街上,电车里,他们点滴地流露。那种哀伤,那种无助,那种毫无归属的感觉,那种日本私小说的氛围。我曾经是这个城市的一员,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观察他们。眼前的浮光掠影也折射出我自己的表情。看到这些照片,我常常想起那里我认识的每一个中国人,虽然我拍他们很少。
我知道,东京的表情其实就是我的表情。
后记
在东京一家书店看见过一本旅日朝鲜人出版的摄影集,名字叫《祖国》。当时看了这个名字非常激动,好像平生第一次明白了这个词这么好。2000年在日本过了新世纪,回国没想到又碰到了2001年新世纪,结果过了两遍才进了新世纪,很不容易。刚回到北京,觉得满街的人和车都是雾气腾腾的,好像随时要蒸发而去似的。有人指着一片光鲜的建筑说“这是西单”,我觉得他是在开玩笑:我在这儿长大的,对每条胡同、墙上的每个瓦片都是熟悉的,现在他却让我管这条陌生的街叫西单?
半年以后,我自己也成了街上那些待蒸发的一员,尽管我脑子里的西单还是原来那样儿。这时又想起了“祖国”这个词,已经没有当时那么强烈的感情了;再想想日本,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感情了。这让我有点心慌。看来感情是不跟着人走的,它会永远长在某个地方或某个人、某个东西身上。我对自己的记忆总是不能完全确信。现在想想,像睡了一觉似的,而且梦太多,影响了睡眠的质量。幸亏身边有两本日记和一些照片,为了留下一点坚定的印象,我觉得有必要在照片后面写一些提示性的文字。正好南京的杨全强先生来了电话。这些文字最后能发展成一本小书,归功于杨先生始终的鼓励。
我们的出版物历来有重文轻图的倾向,最近又反了过来,到了“读图时代”。这让很多人不知所措,包括我。我害怕它哪天又回到“读字儿时代”,想趁机赶快出点照片;可好心的朋友说,现在的摄影书只会出现在外文书店无入问津的玻璃柜里,或和几本陈旧的画册在美术类书架上挺尸。这和我对“读图时代”的理解大相径庭。不得已,又在书里添了更多的字。这种两面不讨好的做法肯定不利于顺应“时代”的大潮。其实,文字和照片都有各自的擅长和不擅长。照片有其他语言无法替代的社会批判功效,只是这种功效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尽管我从心底里,还更看重照片一点,但我根本就不敢说,怕人挤兑我借着“读图时代”的光儿兜售自己的小情感。
母亲、二哥、女朋友是我这本书最早的读者,每有几个小节完成就拿给他们看,他们说“这儿好,那儿不好”,通过他们的眼睛我能对过去的生活有个检讨和认知。摄影家罗伯特·弗兰克曾写到:“我母亲把我有时忘在一旁的照片整理并保存起来。我要感谢她在我还是起步时就对我满怀信心。”我也把同样的话送给我的家人和朋友。
过了半年再看这些文字和照片,虽然觉得有很多不足,但其中对日本社会的描写还是真实的,决定也不再改动了。书里涉及了很多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身上的缺点多于优点,但我们每个人不都是有自己的限制和顾忌吗?我回来了,很多人还留在那边,我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他们好好保重自己。不管怎么说,“祖国”这个词,是与众不同的。
2001年11月于北京莲花池
文摘
“发盘手”宫寺
听不懂日语的时候,我就发现,交流是不需要语言的。我看着别人的脸、表情、眼神,就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是夸我、挖苦我、或是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说话只占交流的一小部分。
一直到离开饭店,我和宫寺说过的话统共超不过三句。宫寺对我是平等的,因为他也很少理他的同伙们。官寺一米七二左右的个子,很瘦,大脑袋,颧骨很高,白眼珠多黑眼珠少,跟人说话时直瞪着无神的大白眼珠。
我开始并没有注意过宫寺,那时正忙着应付饭店里周围那些蹦蹦跳跳想欺负我的日本学生。“长辈”欺负“晚辈”、旧人欺负新人似乎已经成了日本社会的普遍现象。学校里,老师默许的欺生行为每年都导致数十起自杀。我那时是一个听得见的聋哑人。休息的时候,当我走到他们中间,一个自告奋勇的家伙就会从后面突然拍我一下,我一回头,他一本正经地冲我说了一句什么,我一脸困惑时,周围的人哄堂大笑。对这类恶作剧我当然不好急,因为弄不清楚是善意还是恶意。他们对我的心理是一清二楚,所有的“初心者”(日语初学者、初来乍到的人)都有过类似的犹豫。
有一个叫松井的学生一天上工见了我,主动打招呼并洋溢着友好的笑容,让我很不解。当时我已经调整了认为他们是人的看法,因为他们平时对我的招呼,总是不理不睬假装没看见,我省去了这些繁文缛节后倒落得自在。这次松井的主动表示让我以为自己在自作多情,但当他走到我身前的时候,使用了一个更友好、更亲昵的动作:用手摸我的下面,并问:“还好吗?”我立刻还以颜色,以一个不正规的动作使他倒地。本来以为这会引起一场战争,没想到松井站起来,拍拍屁股,走了。日后,松井虽然仍竭力显示出对我的优越感,但这种优越感已经不能再感染我了。我烦的时候,就用眼睛盯着他看。
通过和这些人接触,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对大多数日本人,如果你不及时地欺负他,他就会看不起你。日本人的血气全是装出来的。
宫寺不太一样,他只有周末来打两天工,很少说话,休息时也和林义明一样,在外面一个人抽烟。真正的休息。如果他说话,只是与唯一的女性、食品专门学校身高一米四的香芝笑谈两句;如果他动作,只是为了从办公室里随便抽出一本杂志或漫画闲翻。我真正注意到周围有这样一个人,是有一次在市谷的车站下车,他正走在我前面,穿着一件格外扎眼的背上印着下山虎的黄皮夹克,背着军绿书包,手里拿着一本包着三省堂皮的16开本厚书,根本不像我在饭店认识的他,那副吊儿郎当、卓而不群的样子,完全是上野市场卖鱼的下町人。
于是,我就对他有些留意。我向林义明问起宫寺,林说他可不简单,是东京艺术大学学版画的。刚来不久的吉野也特别提到官寺是东京艺术大学的这件事。我才知道东艺大是比东京大学还难考的国立大学。一位朋友对我说,他在上野公园隔墙看见这所绿树环抱的前帝国艺术大学后,只有一个念头:自己这辈子完了。
官寺是“发盘手”,在这里已经是老同志了,从上大学时起在这儿打工,今年是第五个年头。发盘是一个对左右脑都要求极高的工作,周末又是最忙。林义明说,宫寺发的盘子、器皿不仅丝丝入扣极富美感,而且极有条理,最紧张的时候也毫发不乱,自己甘败下风。我说,宫寺干得时间长了,熟能生巧。林说不是,他刚来时一上手就很漂亮。我说,也许他家里就是干这个的。林说,关键是他干活动脑子,看他漫不经心的,其实很认真,学生里没有这样的人。
后来,林去刷锅的时候,我成了替补“接盘手”。我接过很多人的盘子,接宫寺的盘子是一种享受,该收则收该放则放,调度自如,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紧张有序。宫寺不在的时候,是一个叫山本的学电影的人当发盘手,宫寺来了,山本就自动让开。有一次,周六,宫寺因考试没来,山本代做,大家都经历了一场噩梦,在后面不停地为山本擦屁股。那时我才知道“能力”一词的意思。宫寺是“刷碗大师”。
官寺好像游离在生物圈之外。他会听着别人聊天突然自己笑起来,有时又对别人话里的某个词极感兴趣,他请求别人再说一遍,那种口气介乎于认真和无所事事之间,你好像不能不再说一遍;碰到自己喜欢的话题,他有时也插进意见,不过三言两语,都是补充细节,却总能使谈资丰富不少。工作中他是一言不发的,我见过唯一一次他说话是因为一个新人问了他三次同一个东西应该放哪儿的问题,前两次他都默默地用鼻子指给他,第三次,他不客气地说:“长脑子为什么不用呢?”
日本的高效率其实就是这样:聪明人带着一群傻子干出来的。脑子只需要一个,其他人甘于当零件。而在中国,所有的人都想当脑子。
在林义明当“接盘手”时,我挤掉了山本,成了平时“发盘手”。平日的工作碎碎叨叨,我渴望一次机会体验一下周末真正意义上的“发盘”。这个机会到来的时候,我已经陕离开这个饭店了。周日那天我是早晨十点到晚上十一点的班,宫寺一般下午一点来。他来的时候正是我在岗位上最忙的当儿,我假装没看见他,安藤在一边吆喝,让我让位,却被宫寺制止住,说,让他干干试试吧,林义明在另一边看着我笑。那天干了一下午,五点吃饭回来,安藤笑着问我:“还想发吗?”我客气道:“无所谓。”事后我为这句话后悔了好几天,那次机会错过后,我仍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周末,不停地卸车回库、把盘子器具举上举下、混着众人像抢夺一样劳苦,有时看着滚烫的脏水里自己的倒影,池子里泡着上百个口小肚大的蛋羹杯等着我,再次懊恼那次客气。干“发盘手”到底只有我一个人,而在外围,在混成“先辈”以前,所有人都可以使唤我。每个周末下午五六点的时候,我的眼前就开始出现双影,有时真觉得“今天可能累得回不去了”。
不久,正赶上98年法国世界杯亚洲区总决赛,电视里,日本队所有的队员都哭着抱成一团,他们在加时赛战胜了伊朗队,第一次冲进世界杯决赛圈。功臣中田默默地走回休息室,没有参加赛后的合影,当记者找到他,激动地问他的感想时,他只是很技术性地说:“我传了那么多好球,前锋终于踢进了一个。”对于他,这好像只是一场比赛,与其他比赛没什么不同。他让我想到了官寺。
宫寺大学毕业后准备找工作,但日本经济滑到了谷底,就业很困难,他就决定先上三年研究生再找机会,市谷饭店的“发盘手”现在还应该是他。
P23-28
· · · · · · (收起)
读后感
东京,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和欲望。你可能会喜欢它,却永远都看不真切,好像易逝的三月樱花,无法让时间为之驻足。对于旅行者来说,只是萍水相逢就够了,不需要每天清醒地面对它的节奏与压力,只需在那片迷人的樱色中醉一次,期待与它下一次的久别重逢。 生活在那样的城市,...
评分东京,一直想去的一个城市。 读完了这本,对东京有新的认识。不知道为何,读杂人的时候,总是心痛,太真实了,太直白了,我不懂,无法体会一个人在外的苦,从小就是在襁褓中长大,没有长时间离开过亲人,时间一长吗,就会觉得是种束缚,抑制。到最后,反而没有力量挣脱。...
评分 评分在看东京记的时候,时常会觉得未免太小家子气了,不仅作者,故事里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没有度量,不够淡定,不上进。 但是看完以后却学会了换位思考,如果是我一个人留学在东京,不依靠父母去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要应付课程和考试,是否还有那份淡定的气质?淡定的气质永远...
评分用户评价
这本书给我带来的阅读体验,可以用“沉浸式”来形容,但这种沉浸并非来自廉价的感官刺激,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共鸣。角色的困境和选择,尽管背景设定可能与我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但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人性挣扎、对身份的追寻以及面对命运时的无力感,却是如此的普适和真实。我发现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常常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经验投射到人物身上,思考“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这种互动性极强,它强迫你从一个旁观者转变为一个参与者。作品中探讨的主题宏大而又贴近个体经验,例如关于“记忆的可靠性”和“个体在庞大体系中的位置”,这些议题的探讨是深刻且不带说教意味的,更多的是通过故事的肌理自然流淌出来。读完之后,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挥之不去,仿佛刚从一场重要的交谈中抽离,留下的只有回味无穷的思考痕迹。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简直是一场文字的盛宴,细腻到近乎苛刻的打磨痕迹清晰可见,但绝非故作姿态的矫饰,而是服务于表达本身的力量。作者对于词汇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同样的意象,在不同的语境下能焕发出截然不同的光彩。我注意到,在描写人物情感冲突时,作者经常采用一种克制而又极富张力的笔法,没有使用任何煽情的词汇,但那份压抑着的汹涌情感却透过字缝直击人心,读起来需要屏住呼吸。这种“少即是多”的叙事哲学贯穿始终,使得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段落,回味起来却韵味无穷。对于一些哲思性的探讨,作者的处理也显得非常高明,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巧妙地将思考的权利交还给了读者,引发了我不禁停下来,反复咀嚼那些句子,试图捕捉其中更深层次的含义。这是一本需要慢读,甚至值得反复翻阅的书,因为它在文字的表层之下,蕴藏着更丰富的矿藏。
评分我必须强调这部作品在营造“氛围”上的独特成就。它不是那种情节驱动力极强的作品,但它的“在场感”却极其强烈。作者似乎有一种魔力,能将读者完全拉入到故事所构建的特定时空里,那种环境的压迫感或者说疏离感,比任何直接的描述都要来得更有效。光影、气味、声音,这些本应是辅助的元素,在这里被提升到了近乎主角的地位,它们共同编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故事的核心秘密牢牢锁住。这种叙事手法使得揭示真相的过程充满了悬念,因为你清晰地感受到了“某种东西”正潜伏在每一个角落,等待被发现。这种由环境烘托出来的紧张感,比直接的动作场面更让人心惊肉跳。对我而言,这是一次成功的、对叙事边界的探索,它证明了优秀的故事不需要依赖于频繁的事件爆发,真正的力量在于对情绪和环境的精微操控。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相当到位,开篇铺陈的细节并不冗长,反而像是一张精心绘制的地图,将读者逐步引入一个充满未知与魅力的世界。作者在环境描写上展现了非凡的功力,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特有的、难以言喻的氛围感,让人仿佛能亲身感受到故事发生地的温度和湿度。尤其是一些关键场景的转换处理得非常自然流畅,从喧嚣的市井到幽静的角落,情绪的过渡处理得干净利落,没有丝毫的拖沓感。情节的推进并非一味地追求刺激,而是注重内在逻辑的严密性,每一个转折点似乎都是水到渠成的必然,这使得整个故事的骨架异常坚实。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人物内心活动的细致刻画,那些微妙的挣扎、不为人知的渴望,都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对话和场景暗示了出来,使得人物形象立体而饱满,不再是扁平的符号。读到一半时,那种被故事完全吞没的感觉非常强烈,让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探究下一页隐藏的秘密。
评分从整体结构来看,这部作品展现了作者高超的掌控力,尤其体现在对多线叙事的驾驭上。好几条看似毫无关联的线索,在故事的后半段如同精密齿轮般咬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宏大而又逻辑严密的整体。这种复杂性并没有让读者感到迷失,反而因为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叙事感而感到一种智力上的愉悦。作者对于时间维度的处理也值得称赞,在过去、现在与可能性的未来之间穿梭自如,每一次跳跃都精准地服务于当前的情感焦点或情节推进,没有丝毫的跳跃感或突兀感。此外,书中对于一些象征性元素的植入处理得非常自然,它们既可以作为独立的画面存在,又在更宏大的主题下发挥着强烈的暗示作用,让整个故事的厚度大大增加。我甚至开始怀疑,作者是不是事先在脑海中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三维世界,再将它精确地投射到了纸面上。
评分旅行时在各种交通工具上读完的,一个中国人在东京打工留学的切实感受。这是任何游记攻略都读不到的,旅行也不行。身边的事情和身边的人交织描绘,真实深入。
评分生活在肥皂泡里的人,永远听不见一些声音,看不见一些颜色,闻不到一些气息。作者一边踏实地生活,一边以旁观者的心情,把东京的世间冷暖、人生百态娓娓道来,让我们这些肥皂泡里的人有了互相瞥见的可能。PS:永井荷风真是个好名字。
评分认识真实的日本
评分1对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描述和反思真实、细腻。2并且介绍了很多“怎么搞定讨厌的日本人”的小窍门,可作为留日工具书。3作为一个留学生在日本的所遭遇的各种艰难困苦,作者都从中得到个人的磨练,好励志。
评分难得好文笔。减法做的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wenda123.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目录大全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