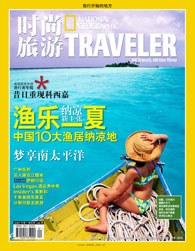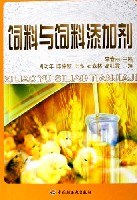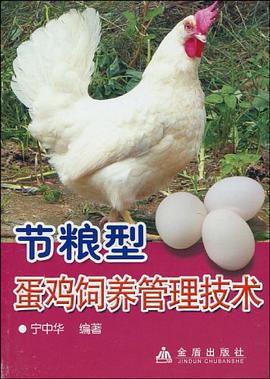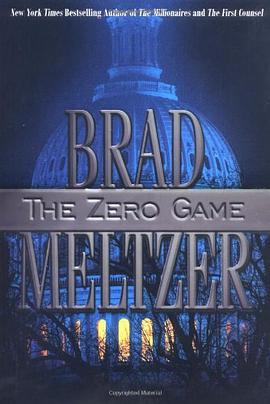具體描述
讀後感
后现代,就是现代主义的市场化。现代主义还有批判精神的个性,后现代就只剩下了嘲笑。意义不再存在。嘲笑成为社会风尚,痞子就成为了社会明星。——《读书》10年1期刘再复李泽厚对谈 于是乎,和胡颖造句—— 文学就只剩下了广告。 美术就剩下了广告设计。 奶粉就只剩下了三聚氰胺。 房地产就只剩下了央企。 真理就只剩下了任志强。 真实就只剩下了宋祖德。 历史就只剩下了明朝那些事儿。 孔子就只剩下于丹。 博客只剩下了微博。 季羡林只剩下了书画。 煤老板只剩下了房产。 矿工只剩下了半条腿。 人民就只剩下了被。 传说就只剩下了哥。 兄...
評分《读书》(三联书店·1997年第2期) 这期《读书》,有一个主题话题“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发言者有韩少功、戴锦华、旷新年、李陀四人,谈的还算扎实。不过现在读当年的观点,不免有些陈旧过时,毕竟1997年才是大众文化刚刚风行的时候,而在2010年的当下,又是一番风景。另外马文通谈海德格尔与纳粹、刘小枫谈基斯洛夫斯基、杨念群谈礼物交换的本土精神、单纯谈冯友兰等文章皆可读。刘小枫关注波兰导演,看重的是基斯洛夫斯基在《蓝》《白》《红》里所传达的“爱”,也就是刘小枫标题里写的那样:“爱的碎片中的惊鸿一瞥”。海德格尔是大哲学家,但他跟...
評分对于与我本人同一年诞生的《读书》杂志,我是怀着一份特殊感情的,自初中时在老哥影响下开始《读书》的启蒙阅读算起(其实那会真正是瞎读,连“一知半解”都算不上),对这本杂志的阅读时间跨度居然已有14,5年,真是弹指一挥间。 彼时还是沈昌文先生担任杂志主编,金克木、冯亦代等当时的作者如今都已作古,陈平原、葛兆光、朱学勤、凯蒂、李零……以及对我的文体审美趣味产生过极大影响的乐评人李皖,《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汉奸发生学》、《最是文人不自由》、《民谣三题》等(以现在眼光观之)堪称经典的文章,乃至现如今在学界影响很大的《天涯》...
評分我一直都把《读书》当做是一本半学术的读物,它并不休闲,也不是完全的无趣味的纯学术杂志。杂志里面的很多文章都让人读后有一种思维上的冲撞,我只买过几本《读书》杂志,可以这样说,《读书》实在是一本很小众化的杂志。这也是它的成功之处。《读书》永远不缺少固定的读者群,而且这样的读者群将是非常精英类的读者群。《读书》杂志很便宜,所谓物超所值。但是似乎杂志内的新鲜东西越来越少了,好像是一个正在被逐渐消耗的蛋糕,表面的奶油越来越淡,它偏向学术的倾向可能会丧失一些读者,而这也是无法避免的。 end
評分2012年10月刊 回首二十世纪 P26 托尼 贾特 怀着道义理想的知识人。 《记忆小屋》《沉珂遍地》《思考二十世纪》社会民主制 "世界上的正义原则、价值或者真理是多元的,它们不能被还原到一种简单的真理,无论那种真理多么诱人,前景多么美好。" "一元论往往走向文化偏狭;而多元论的知识人为了超越狭隘的地方性偏向,不仅关注并通晓本地的事务,而且以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关注世界各地的事务。" “由于美国人生活在一种托克维尔所说的从众主义的公共空间,知识人也更容易陷入主导舆论的操控,因为多数人的意见似乎牢牢的披上了合法性外衣,多数...
用戶評價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哈圖書下載中心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