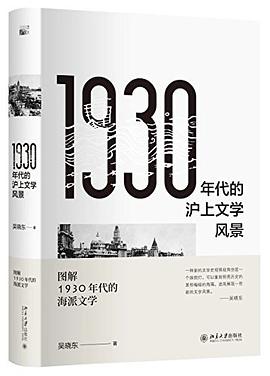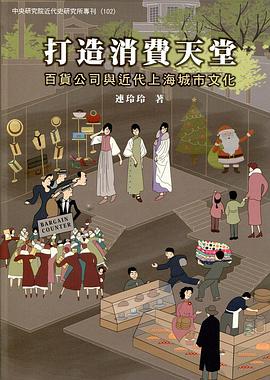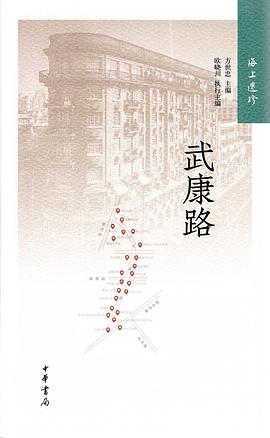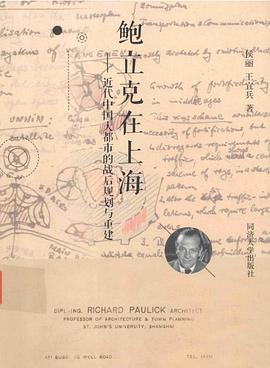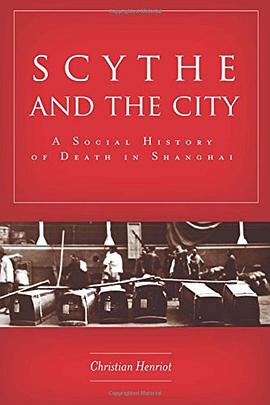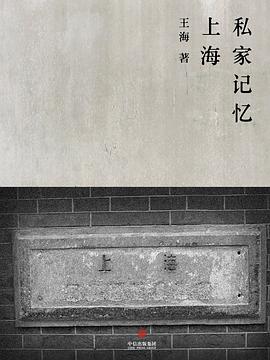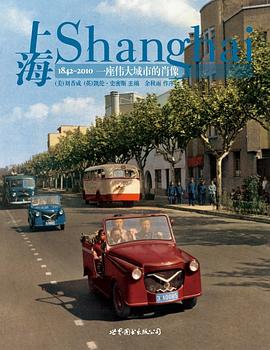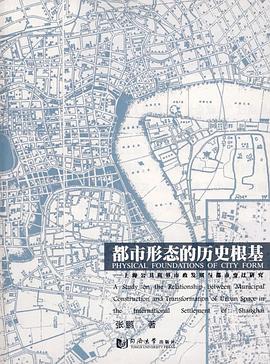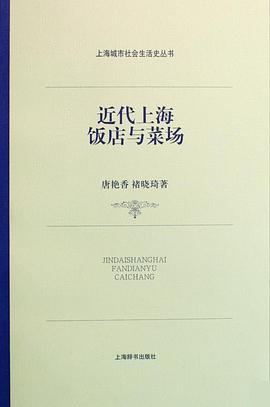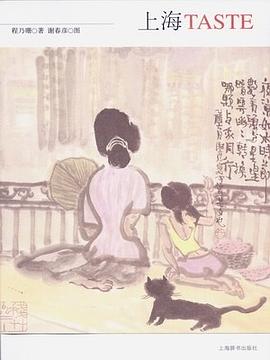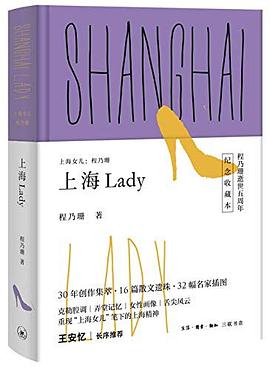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她爱吃,闻到糖炒栗子的香味就迈不开腿;赶时髦,动乱年代也要用废电线圈烫头发;追爱豆,追到比弗利山庄与格里高利•派克拥抱合影……她生于1946年,是名副其实的名门之后,却比谁都贴近今天的年轻人。她是上海的女儿,或者说她就是上海,在时代的新旧交替间看似驯顺,又有固执的坚守,外圆内方,自得其乐。于是,笔下流出的文字……,寻常巷弄蛰伏着传奇,别具强盛的生趣。尽管离去已5年,她关于生活的那股子热腾劲,依然在纸面上兴致勃勃,感染着做书和读书的人。
名人推荐
将程乃珊和其他都市描摹比较,我的意见是,程乃珊不可替代。不只材料拥有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文学营养的品质差异。
——作家 王安忆
程乃珊是上海的女儿,上海哺育了程乃珊,她也以自己的充满感情的个性文字,回报了这座城市。
——作家 赵丽宏
对乃珊而言,书房乃是战场,是其生命的维系。她每日躲进狭小的书房,奋笔疾书,拼尽剩余一点气力,说尽留存于大脑中有关老上海的悲欢离合。
——主持人 曹可凡
20世纪80年代,程乃珊、王安忆和王小鹰是上海青年女作家的三鼎甲……我与不少北方的作家朋友谈起上海文学创作时,他们都把读程乃珊作为了解他们心目中的上海影像的途径。
——学者 陈思和
强烈的自觉,使她成为新世纪以来,发掘、传播老上海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很重要也很有影响的作家……她翻箱倒柜地在上海历史旧箱子的角角落落里,发掘着具有文脉意味的各种器物、习俗、细节。
——文艺评论家 毛时安
作者简介
程乃珊(1946—2013),上海女作家代表人物。创作多根植上海本土,取材于独特的时代背景、家族故事与人生境遇,以细腻的文笔勾勒出上海文化中很生动的两种质素——老克勒文化与小市民生活。代表作有《上海Lady》《上海Taste》《远去的声音》等。
翻译过美籍华人作家谭恩美代表作《喜福会》
目录信息
总序/王安忆
四季歌
就这样慢慢敦化成上海女人
我的妈妈
荣贞阿婆
上海街情话
镜花缘
做头发
髻
女人和帽子
花边
旗袍吟
高跟鞋
女儿经
小姊妹
绢头
结绒线
女红和铁蝴蝶
女人和床
红豆曲
她喜欢吃甜的
老公如老酒
太太万岁
上海女人的“作”
介绍朋友
由上至下和由下至上
仕女图
上海女人
上海小姐
一枝花
小家碧玉
亭子间的女人们
申家姆妈
交际花
女裁缝
保姆
上海煞女
代跋/毛时安
文摘
《就这样慢慢敦化成上海女人》
浙江桐乡梧桐镇的女人们
我们程家的故乡浙江桐乡梧桐镇——好美丽的名字——在祖辈父辈的回忆中,是一派飘逸清幽的水乡,但见水道纵横,白墙黑瓦的民居倚河而立。家乡是著名的蚕乡,正如茅盾的《春蚕》所描述的。
水乡可以讲是中国特有的景致。外国的水乡不多,恕我不见世面,似只有威尼斯,那窄窄的河道和古朴的布满青苔的墙壁还蕴含着水乡之气。然与中国的水乡相比,还是十分不同的。我们的水乡是一幅写意的水墨画,黑白之间,自有一份天长地久的空灵。
遗憾的是,2006年我与叔婶重返梧桐镇之时,那百年水乡古风已无从寻觅——程家的老宅已拆除,河道也填没,还残存的几幢半塌的老民居十室九空,墙上一个个画上粗影的红色“拆”字,像煞古装电影里拍出来的处决犯人的“批”,看着触目惊心!
梧桐镇已改名为“梧桐街道”,父辈记忆中大片的桑园消失了,一片车水马龙,这就叫现代化吗?纵使风景再好,已非江南水乡的景色了!
程氏祠堂当然也拆了,唯有一棵柏树,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叔叔依稀记得还是原先的那棵。一句“家族之树常绿”,此时悄然潜上我的心头,并萌发了尽我所能写部五代家族史的念头。
去年5月,我的微博里有一封私信,打开一看,信发自广州,发信人开口称我“乃珊姑姑”,自报家门,她的曾祖父程慕廉与我祖父程慕灏是同父异母兄弟,这支程家支脉一直在杭州山子巷24号开枝散叶,如今,山子巷24号已被杭州市政府保留为民国时期的优秀建筑。
从梧桐镇到杭州,到上海,乃至今日的香港、北美……我们这棵家族之树可谓根深叶茂,支脉繁衍,其中不乏祖辈的辛勤栽培,包括那几位连名字都没留下的我们宗族的母亲们。
那位微博上留下私信的我的堂侄女,虽然我与她从未谋面,她所属的那个慕廉祖父的支脉成员我一个也未见过,但这位堂侄女很让我感到亲切: 她自小学钢琴,现为广州专职钢琴老师,且文笔优美,已出几册与音乐有关的散文集和钢琴教育书,还擅长绘画——这完全是我们程家女性的特征。我家女性专业从事绘画、钢琴、写作、外语的颇多……所谓血浓于水。然而在我的百年家族故事中,第一位载入我们家史的女主角却是一位没有留下任何照片、目不识丁、缠着一对小脚的农村妇女。她连名字都没留下,她就是我的曾祖父震权公的原配程黄氏。
我们程家祖籍安徽省休宁县,祖先原任当地盐公道,想来是一个管盐的公务员。太平天国时期,迁至浙江桐乡落籍,租居了梧桐镇东门外的一幢前后两进的旧平房,前进有高祖父久安公,开设店铺,名“程久盛”,专业经营蚕种、桑叶之类,后进为居家之用。但终因书生经商业务不佳,以致家道清贫。曾祖父震权公不得不早早辍学,赴杭州当账房打工。曾祖父娶妻黄氏,缠了一对小脚,却桑田蚕房店务几头一手抓,并育有两子,大子慕廉,也早早辍学去乌镇某酱园学生意,幼子连名字也没留下就夭折了!
不记得哪年,曾祖父突然大病,危在旦夕。那个时代,男人是家中的顶梁柱,一个家若没有男人,真的如天塌下来一样!此时长子慕廉虽已辍学去学生意,然尚无能力独立挑起养家之职。曾祖母走投无路,心一横,带着幼子跪在菩萨前发了毒誓: 愿以母子两人之命来换取丈夫的命。当时小儿虽尚年幼,却已懂得在菩萨前发誓的分量,因此咬紧双唇任凭母亲打骂威逼就是死不开口。怨恨之下,母亲擅自代幼子发了誓,并强按着他的头在菩萨前磕了三个头,然后拉着他去屋后直奔井台。毕竟是做娘的,她心软了,忍不下心亲手将儿子扔下井里,只是婉转对儿子说:“姆妈先下去,在下面等你,你不要怕……”便纵身跃下。儿子没有跟下去。乡里闻讯赶来,从井里捞出,已回魂乏术!
井那么深,那么凉,那么黑,根本就是一条通往另一个不可知世界的隧道,别具一种令人发指的恐惧。纵身一跃时,需多大的勇气和决心!而我这位曾祖母,纵身一跃,捣碎了一镜潋滟的月光,成就了我们家族史一则湮远的凄厉典故。从此,我害怕走近任何井台,包括上海弄堂里常有的那种用粗铁链封锁住井盖的井。
信不信由你,自曾祖母黄氏投井自尽后,曾祖父的病竟不治而愈,遗憾的是,那个幼子虽然没有在菩萨前发誓,也没往井里跳,第二年也夭折了!
曾祖父再娶续弦邵氏,就是我祖父的亲生母亲,共育有子女十个,但由于家贫,最后成活的只有三个: 祖父程慕灏、伯祖程慕颐(后成为有“中国细菌学之父”之称的著名微生物学家)、姑婆程慕英。续弦的曾祖母也是一对小脚,却是挑担采桑、缫丝孵蚕,田里屋里样样一把抓。据讲,她孵的蚕子质量上乘,以至乡里人都传颂:“久盛号”蚕种是最好的。
说来真奇,曾祖父一病愈,程家家道也似走上重生之道,虽然仍是清贫,却似有了一线新机。当时乡间的“久盛号”已由曾祖母打理,曾祖父也就放心去杭州张公馆继续履职。由于处理账务钱财进出有条不紊,深得东家器重,东家再将曾祖父推荐给自己的姻亲孙家兼职。说起孙家,来头不小,主人就是曾得清庆亲王赏识而未被慈禧重用的孙宝琦。辛亥革命后,他为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显赫一时。孙宝琦有一个孙女就是张爱玲的继母。只是好不过三代,到抗战开始不久,张、孙两大家都已败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说起张家的发迹,也是一则传奇。传说张家的发家人原是一守城小卒,那天正在城头上边抽旱烟边大解,突然发现海面有倭寇(也有讲是海盗)之船来偷袭,他不慌不忙将旱烟枪往近处的炮台一点,“轰”一声,贼船以为城门哨兵已有觉察,连忙掉头就逃。这位小卒就这样一不小心立了大功。朝廷在其老家浙江同里广赐良田,每年来交租的船络绎不绝,并在杭州大兴土木,造了赫赫有名的张公馆。据祖父回忆,张公馆内犹如大观园,奇石名花,楼台亭阁,真是说不尽的奢华。张公馆的几位少爷成天吟诗作画,进出名驹,风流倜傥。
从小祖父就对我们说,张家对我们程家是有恩的。祖父清晰记得,幼时随曾祖父到张公馆度假,一天祖父与伯祖兄弟俩正在园内嬉戏,忽闻一阵清晰的马蹄声,有人高呼“三少爷到”,两小兄弟自知回避不及,便连忙打千请安。三少爷见两个孩子聪明可爱,问起谁家的孩子,两小兄弟忙自报家门,是账房程震权的儿子。三少爷当即让人把曾祖父找来问:“两个那么聪明的孩子为什么不进学校念书?”曾祖父回答:“我们小户人家,能够识几个字、记几笔账糊口就可以了,没有能力全力栽培。”三少爷极力劝道:“你的想法已经落伍了,现在西学奋进,国家需要大力栽培年轻人。你应该将孩子送到新学校栽培,两个孩子这么聪明,将来前途无量。你没有能力我来帮你。”就这样,我的祖父、伯祖两兄弟在张家的资助下,转学至桐乡县立小学,他们学业优秀,祖父续赴杭州省立簿记学校(相当于今天的会计学校),在校学习期间,由于成绩优良,得该校高才生之誉,伯祖慕颐杭州官立中学毕业后,公费保送杭州医专深造。家业似有转机了。
而在浙江梧桐镇乡间,小脚曾祖母为了增添家庭劳动力,让在酱园店已满师的祖父同父异母的长兄慕廉早早娶了一门媳妇吴氏来操持家务,种桑养蚕。为了方便劳作,这位淳朴的乡间妇女已是一对大足。中国古语“长嫂如母”,对这位长嫂,祖父和伯祖一世尊重。两兄弟后来发达后,在杭州山子巷造了三层大洋房,拱手让给这位大嫂和后代居住。当然,这已是后话了。但是,此时两个乡间女人养不起两个洋学生,只好让仍在医专求学的伯祖慕颐娶了目不识丁的伯祖母王氏,只为了家里可以多一个劳动力,不意间,却种下了一个长达一辈子的爱情苦果。就这样,前方加紧苦读,后方三个乡间女人克勤克俭,为了程家的未来辛勤奋斗。
上海新闸路斯文里的女人
慕颐伯祖在杭州医专成绩拔萃,很快得到政府公费资助,往东京帝国大学微生物专业深造。消息传来,令曾祖父悲喜交集。喜的是,家里竟然可以出一个洋学生,这是十几代都做不到的;悲的是,虽然学费由政府资助,还有东家张家的鼎力相助,但以他个人的财力,尚不能同时栽培两个儿子。
这时,祖父毅然决定放弃在省立簿记学校的求学,打工养家。恰巧此时,张家的女婿、当时的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回杭州拜访岳丈,曾祖父登门,于孩子辍学就业养家的问题请求帮助。孙宝琦念及多年主佣之情,一口答应,当即亲笔写信,将祖父介绍给当时的上海中国银行行长丁道津。就因为这样一封信,祖父终其一生服务于中国银行。
1913年2月12日,曾祖父陪同二十四岁的祖父来到汉口路3号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今汉口路50号,此大厦现还在),拜见丁道津行长。祖父清楚记得,丁行长为贵州人,身材魁梧,性情豪爽,他对祖父说的第一句话祖父记了一辈子:“想发财的不要进中国银行,但只要你勤勤恳恳,认认真真,信义为本,学好本领,必有前途。”这句话从此成了祖父的座右铭,直到他后来进入中国银行管理层,每次向新员工训话,必以此句为开场白。
只半天工夫,一应入行手续和宿舍已办理完毕,父子依依惜别之前,曾祖父给祖父四十块带着体温的银圆,以备不时之需。祖父在中国银行由练习生升到助理员,再升到办事员,先后任文书、会计、营业、译电等多项职务,逐渐成为银行业务的多面手,工资待遇也相应不断提高。他还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去青年会补习英文。三年后,回桐乡老家时,不仅把四十块银圆完璧归赵,另外掏出省吃俭用存下的四十块银圆,给曾祖母作为家用,这已成为我们程家五代的教育经典。遗憾的是,我们的后辈还不大明白其中的含义。这时家中经济逐渐好转,祖父还能资助在日深造的伯祖,并与曾祖父一起,在老家新建两进共九间青砖新房,曾祖父特取名“读月庐”,内设书房,并镶有彩色玻璃,在当地也算十分讲究。
1917年,新房造好,祖父迎娶当地农家女馥笙,那就是我的祖母。祖母也是一双天足。1918年,祖父的长子——我的父亲程学樵出世。按当时习俗,男人大都外出打工,女人留在乡间侍奉长辈,照顾孩子。祖父也是如此,吃住在银行宿舍,家眷留在乡间,既节约开支,也省心省事。
1921年,中国银行拟在日本筹设第一个海外经理处,要求派专人带一百万日元作为开办资金,并派专业会计随行。此时已入行八年的祖父因办事认真、业务熟练而被行长宋汉章赋以此任。后此事因故没有谈成,祖父离日回国时,带去的一百万日元不仅分文不少,还将此笔巨款存入当地银行所获的利息四万日元,除去日常开支外一并交存,账目清晰,单据齐全,这种负责精神更加深了银行对他日后的器重。
此时祖父的事业可谓风顺水顺,但他不满足于当时大多数人所采取的自己留在上海、将家眷留在乡间的做法,他觉得时代在变化,不愿让他的孩子像他一样在闭塞的乡间度过最好的启蒙教育时期。于是,祖父坚决将祖母和我的父亲从桐乡接到上海。上海的“住”之昂贵,自开埠以来就存在了,尽管祖父当时已是银行有稳定收入的员工,仍是不胜负荷。好不容易租赁到今新闸路东斯文里一单开间石库门二楼前楼一间房间。说起来,上海石库门其实种类很多,等级分明,东斯文里这种石库门是最蹩脚的,人称“江北石库门”,就是没有厢房也没有亭子间,上下两层就靠一层薄薄的木板隔开,而且紧靠着粪码头,到夏天简直不能开窗,臭气熏人。晚年的祖父犹记得,当年我的大姑妈尿床,尿水顺着席子流到地板上,又顺着地板的缝隙滴到楼下正在品酒的邻居的胡子上,成为笑谈。
就这样,我的祖母馥笙无怨无悔,跟着自己的男人,离开蚕乡桐乡梧桐镇,来到一无所知的大上海,从而成为我们程家第一个踏入大上海的女人,含辛茹苦与祖父养育了四女二男。
1923年,由中国银行总行拨三千二百两白银在西区极斯菲尔路(今万航渡路)买了十七亩地,建造了包括礼堂、小学校、各种文康俱乐部在内的银行职工宿舍区,取名“中行别业”。宿舍建有各种规格,以适应各级职员居住。此时祖父已升为中国银行国库股主任,也获得了两开间三层楼的主任级住房一栋,居住条件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祖母虽然没有文化,不识字,但她努力脱尽自身的乡土气,从言谈和行为上令自己做一位称职的银行先生的太太。桐乡人在上海统称为“湖州人”,被公认为翻丝绵的老手,祖母就热心帮教邻里撕翻丝绵,从小孩衣裤到大幅的丝绵被,来者不拒,还将我们桐乡的美食——鸳鸯蛋分送给邻里享用。所谓鸳鸯蛋,其实很简单,就是将煮熟的鸡蛋一剖为二,上面覆上用金针菜调配好的碎猪肉,像煮红烧肉那样煮。我们的家乡菜偏甜重油,很受邻里欢迎。还有每逢过年,祖母就会精心制作甜点心——枣饼,就是将枣子煮熟,拆出枣肉,与糯米粉拌在一起,另外再用核桃肉拌上黄糖、芝麻做馅,然后嵌入特制的印有福禄寿吉祥图案的模子里,垫上粽箬壳上笼格蒸,香气四溢。每逢过年过节,祖母都要蒸上好几蒸架,分送给左邻右舍。更收了大批的徒弟,过年之前就跟着祖母学做枣饼。祖母也跟他们学做黄蛋糕(一种中国式蛋糕)、裹宁波汤团、打年糕等,完全脱胎换骨成为一位能干的银行先生的贤内助。
讲起来,从前银行的工作是银饭碗,但过的也是这样平实、简朴的小日子,并不是现今影视剧中描写的那样整天雪茄红酒嘭嚓嚓(交谊舞)。因为桐乡方言称“我们”为“哦拉”,所以大家都戏称她为“哦拉嫂嫂”。我从来没见过这位祖母,但都说我忠厚随和的脾气,还有一对天不亮水泡眼是来自她的基因。
1926年,北伐开始,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北洋军政权摇摇欲坠。基于大势已定,上海工商界、金融界纷纷与北伐军取得联系,并表示如有军需需要,一定给予协助。因此,军长白崇禧的军需官曾到上海中国银行借过军需款项。自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并联系上海金融界人士,成立替蒋政权筹募经费的机构,由陈光甫为主任委员。他把祖父借调到委员会担任金库员,以便审批签章。祖父在此机构任职一年多,有机会结识了不少上海各界的知名人士。全靠有一个贤内助,祖父的事业才能如此一帆风顺。人说夫荣妻贵,但我的祖母依然是一位在邻里间生活俭朴的“哦拉嫂嫂”。
就这样慢慢敦化成上海女人
祖母馥笙可以讲是梧桐镇程家第一个步入大上海的女人。其更大的意义是程家一支新嫩的支脉将在大上海破土而出,同时为梧桐镇的女人们开了一个闯荡大上海的先例。
吴毓英,一个如同茅盾的《林家铺子》里林家姑娘一样朴实的水乡姑娘,眉清目秀,在县城女中初中毕业,在当时也算是一个女知识分子,安分守己的小家碧玉。经人说媒,许给我祖母的弟弟,据说也因为祖父在上海做银行先生,女方家长才同意了这门亲事。因为新娘子长得娇小玲珑,我父辈亲热地称她为“矮子舅妈”。小夫妻刚完婚就双双到大上海寻找梦想。祖父帮小舅子在钱庄找了个职位,工资不高,却也稳定。矮子舅妈打理家务,闲时常来中行别业帮助我祖母照料几个孩子和做家务,小日子过得蛮舒服。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大上海虽说处处有机会,却也是步步有陷阱,矮子舅妈的老公不知如何交上几个损友染上了毒瘾。据父辈回忆,未染上毒瘾前,这个舅舅和蔼可亲,对几个外甥是疼爱有加,常常带他们去看戏吃点心;自从染上毒瘾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先是贪污钱庄里的钞票,将好端端的一份工作也丢了,再到处借债,自己彻夜不归,债主连夜上门逼债,逼得矮子舅妈走投无路,到后来吓得家里也无法住,就一直躲在中行别业我家。初时祖父还帮着苦劝这位舅子,送他去戒毒所戒毒,帮他还债,再替他另谋新的工作,但都无济于事,过不多久,他便旧病复犯,夜不归宿。
终于,一天祖父对矮子舅妈说:“你只好心硬一点,譬如当他已经死了,你要重新开始你的生活。”
那个时代,一个弱女子要重新开始生活,自力更生,谈何容易?祖父考虑到自己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可资助她,但毕竟非长远之计,仅有的出路就是鼓励她做一个自食其力的职业妇女。好在矮子舅妈尚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祖父先为她在一家助产士学校报了名。两年后,伯祖程慕颐被上海医学院聘为教授专授细菌学,并为他特别设立一个化验专科班,祖父便鼓励矮子舅妈再去深造。此时的吴毓英一直住在中行别业我们家,一心苦读,成绩斐然,毕业后适逢伯祖程慕颐化验所业务如火如荼,她就很顺当地成为一位称职的化验员。有了固定的收入,她便搬出中行别业,自己在外面租了房子,过着滋润淡定、自力更生的职业妇女生活,并以此为据点,将梧桐镇的娘家弟兄侄子一个个接到上海来闯荡天下。说起来,吴家还真出了几个人才: 吴毓英的侄女吴曼华早年参加革命,后任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吴毓英的侄子吴建华的女儿,现为加拿大某市华人总商会的会长……
吴毓英一生以化验专业为职业,直到八十八岁去世,学生已桃李满天下。曾见过她年轻时的照片,一头垂肩烫发,配浅色宽身呢大衣,平跟的缚带皮鞋,这是当时上海最典型的职业妇女打扮。一个蚕乡的小家碧玉就这样慢慢敦化成上海典型职业女性。
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完全沦落成上海街头的叫花子,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拖着鞋皮与一群瘾君子为伍,露宿街头,并常常会守候在我父亲和姑叔放学的路上,向他们乞讨:“想想娘舅从前也很宝贝你们的,你们就可怜可怜娘舅,给我点钱买只大饼吃吃……”祖父常会警告他们,一个铜板也不许给他。每逢此时,父亲他们又惊又怕,总是落荒而逃。
毕竟是亲娘舅,虽然他沦为瘾君子,却总会在他们背后叮嘱:“不要奔,不要奔,小心跌跤,娘舅不跟你们缠了……”听来令人唏嘘。
1927年,作为国家银行的中央银行正式成立,宋子文任总裁,央行虚设两个副局长职位。有人在宋的面前极力推荐祖父,其实宋子文对祖父也早有所闻,知道他在财务委员会负责金库管理、筹募款项均尽心尽力,办事干练,正是年轻有为的人才,并想当然地认为,将祖父调到中央银行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未征得祖父本人意见时,就在内部公布“程慕灏为业务局副局长”的任命。
这时,贝祖诒(贝聿铭之父)从香港中国银行调到上海中国银行任经理,得知祖父得到宋子文的赏识要调往中央银行,不愿放人。同时提出,既然中央银行聘他为副局长,我们中国银行就升他为副经理。再讲,祖父本身也不愿去中央银行,感到中央银行是纯官僚机构,自己勤恳工作,不过求个丰衣足食,既不善钻营,也不会钻营,根本无意涉足仕途,而且官场多变屡见不鲜,远不如中国银行稳定,便委婉谢绝了宋子文的邀请。此时祖父仅二十九岁,无意中创造了中国银行有史以来的三个“第一”: 第一个由主任跳过襄理直接晋升为副经理的人员;第一个年仅二十九岁的经理;第一个没有大学文凭也没有留洋经历的经理。
然而,正所谓赌场得意,情场失意,甘蔗没有两头甜。正当祖父事业春风得意之时,个人生活却遭到重大的打击——祖母突发心脏病猝然去世,丢下二子四女,最小的姑姑只有两个月。祖父一个男人家如何应付得了这个场面!这时矮子舅妈毅然搬入家里帮助祖父,料理家务,抚慰失去母亲的孩子们……
祖父晚年时曾向我透露,在那最悲伤的时候,吴毓英给他很大的宽慰。或许对吴毓英来说,这段感情应注入得更早,早在祖父为她不成器的丈夫奔走,鼓励她、帮助她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女性时,一个英俊能干的男人已深深走入她的心灵……或许有许多理由可以令吴毓英由孩子们的舅妈转换为母亲……但是吴毓英毕竟是有丈夫的,尽管丈夫不成器,下落不明,但在法律上,她是有丈夫的,还是祖父的内弟媳。祖父作为一位金融人士,一举一动更需要行得正、立得直,不能有一点让人诟病之处。对这一点,两人都深知其中轻重,终于快刀斩乱麻了结了这段情愫。
若干年后一个北风凛冽的冬夜,一个叫花子找到我家报信,矮子舅妈的丈夫倒毙在街头。祖父连忙陪着矮子舅妈去收尸,矮子舅妈以未亡人身份一样为他戴孝守灵。此时祖父已迎娶了无锡鼋头渚杨家的二小姐为续弦,女儿都已三岁了。矮子舅妈终身未再嫁。人前人后,矮子舅妈都被尊称为“吴先生”。中国的女人向来有很多称呼: 小姐、夫人、贵妇、师母、太夫人……但总觉得,一个女人被称为“先生”,是一种最大的荣誉。能够被称为“先生”的女性,必须受过良好教育,德望俱重,懿范双具,她们一定经历过时代的风云,阅尽世情的沧桑,处世低调又恬淡,犹如一杯清澈的香茗。
据我的四姑妈回忆,祖父九十岁时,她去香港探亲,祖父嘱咐她带一封信给矮子舅妈。信中写什么当然不得而知,但矮子舅妈当着姑妈的面读完此信后泣不成声。关于矮子舅妈与祖父的这段故事,我已写入我的长篇小说《金融家》之中。
· · · · · · (收起)
读后感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用户评价
上海女人的日常?
评分上海的味道,尤其是那时的女人,裁缝,阿姆,小玩伴....都是过去一幕幕旧式生活的参与者。也可以窥见海派文化的一点点渗入,婉约又不失风情。
评分上海女人的日常?
评分哎,冤枉钱。
评分如果循着文字去搜索体会,真的感觉不一样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wenda123.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目录大全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