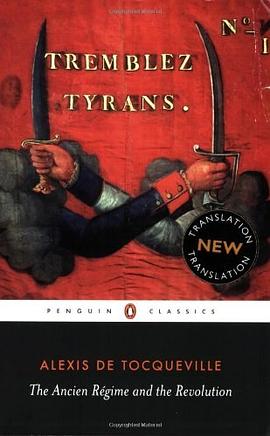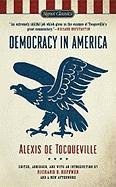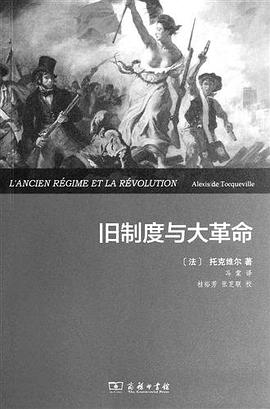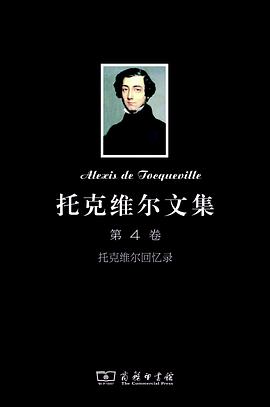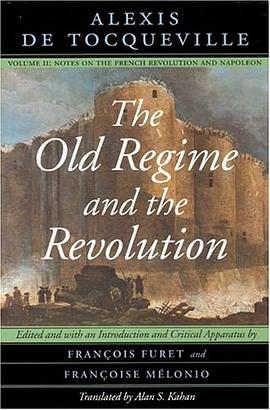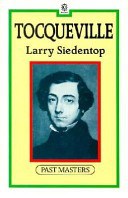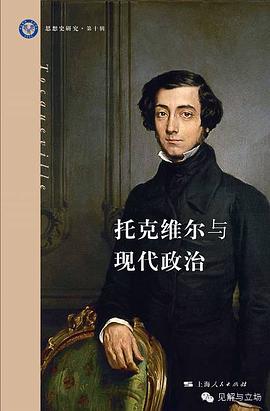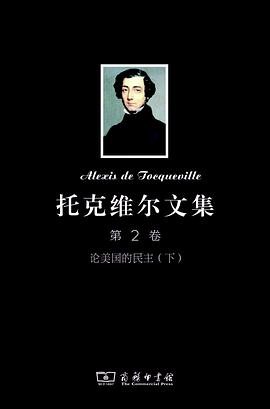Selected Letter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 政治哲学
- 托克维尔
- 社会理论
- 法国史
- Tocqueville
- 英文原版
- 知识分子
- 法国

虽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以其对美国政治出色的洞察力和对1789年革命之前法国社会的分析而广受赞誉,但对大多数读者而言,他仍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他之所以为人所知,主要因为他的巨著《论美国的民主》,这部对美国社会的分析著作是他在1831-1832年与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一起巡游美国之后写成的,而那次出游的表面目的是要去考察美国的监狱制度。事情有时就是这样。《旧制度与大革命》和他关于1848年革命及其后果的《回忆录》后来出现在大学的阅读书目名单上。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与任何现代分类范畴都不是很契合。作为一位写下了一部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分析美国政治的著作的政治学家、一位十九世纪法国最富鉴别力的历史学家,一位现代社会学家的先驱、一位曾当选众议员并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政治实践者,托克维尔给每个人都留下了遗产。然而,要想把所有这些构成部分都融为一体却并非易事。
与以前的读物相比,这部书信选集提供了一个有关托克维尔的更为全面的画卷。他的第一部内容广泛的书信选集的英译本之所以能在本世纪问世,是因为以下两件事使其成为可能:一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在J. P. 迈耶的主持下,托克维尔全集的权威法文版陆续出版,另一方面,1972年出版了他给其选区代理人的信件的德文版。为补充这些材料,我们也查阅了耶鲁大学的托克维尔文献收藏,以及19世纪出版的一些托克维尔的书信[1]。
在这卷选集中,我们试图提供一个有关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生涯的概览。我们将从青年时代的托克维尔开始追述,那时他是个迷恋英国的律师,然后是他在北美的旅行、他创作《论美国的民主》、他作为反对派众议员的令人沮丧的政治生涯、他对1848年革命的直接反应,最后是他被迫从路易·拿破仑的第二帝国隐退后重新开始的政治著述。虽然他在北美写的信件十分重要、他给夏布罗尔和凯戈莱的长信显露出了他关于美国民主制度的第一印象和随之而来的反应之中的敏锐之处,但我们不能高估他人生这一阶段的意义。因此我们选择的信件涵盖了他的整个一生,并且必然要更多地关注他所置身于其中的法国政治和思想界。“尽管我在那本书(《论美国的民主》)中很少谈到法国,但我在写下每一页文字时都在思考法国”(第53封信)。托克维尔一直认为自己既是政治行动者,又是学者,但在这两个角色中,他首先关心的都是如何使民主制度适应于法国的政治文化。
这些信件当然以托克维尔一生的政治活动为中心,但它们也势必会显示他的个人性格。虽然有一些托克维尔的生平传略以及关于他北美之行的详细研究,但迄今并没有关于他的完整而详尽的传记[2],考虑到这一点的话,这些信件就显得格外重要了。通过这些通信,我们可以看到,托克维尔是如何从其个人气质和理想——至少部分来说是这样——来进行政治和社会分析的。这些信件中交织着四种情感:首先是他个人生活中的焦虑及他对亲密友情的信赖;第二,与当时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一样,托克维尔对这场运动也很关注;第三是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的逐步冷却;最后是宗教在他个人生活和政治信念中的重要意义[3]。
个人生活:焦虑、不快、友谊
托克维尔信件中表露出来的一个特点可能会让某些读者感到诧异。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阿尔及利亚、在众议院还是在1848年的街垒后面,托克维尔看起来镇静而自信,但是当他在本书的第一封信中说自己有“绝望感”时,我们发现,托克维尔并不快乐,正如他自己曾说过的,这种想法经常折磨着他[4]。在给他哥哥的一封信中,他再次表达了同样的焦虑和不安,这种焦虑和不安驱使他去从事有意义的事业,但也“无端地”折磨着他,给他带来“很大的伤害”(第39封信)。后来他还对博蒙说,他从未发现通往快乐的道路:“年轻的时候,我那相当健康的躯体上经常是颗混乱的头脑。现在,我的头脑接近康复,但它的外壳丝毫也不更加适应它的要求。所以患病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快乐,而且现在也不知道”(第86封信)。有时候,托克维尔甚至显得很绝望,他曾对其终生的好友凯戈莱透露说,“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理智正在丧失”,对博蒙他也曾说,“有的时候我十分痛苦,以致难以控制自己。”[5]他在追求快乐方面的挫折也许大大强化了他政治上的悲观主义和幻灭感。
表面看来,这些情感使得托克维尔对人生的看法很像个深知可以期待者唯有失望的斯多噶主义者。他曾说,生活既不是件高兴事,也不是件悲伤的事,它仅仅是个严肃的任务,我们的职责就是体面而有尊严地履行之。“所以,生活既不是非常美好,也不是很坏,而是某种由好坏两方面所混合的中等事物。不应对它有过多的期待,亦不应对它有过多的恐惧,而应努力把它看作既不令人厌恶也不让人狂热的东西……重要的是使之变得能为人承受。”(第10封信)。
在一段广为人知的文字中,托克维尔曾说,他一直依照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信条而生活[6]。对于19世纪法国任何一位政治思想家来说,选择后两位作家道理很明显,但是,阅读托克维尔公开发表的著作的读者,可能对有关帕斯卡尔的深层意义感到困惑。不过,如果注意到托克维尔的焦虑及他对获得思想宁静的无能为力,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他对帕斯卡尔的偏爱了。但另一方面,帕斯卡尔曾指出,大部分人是靠消遣来逃避焦虑和怀疑,然而托克维尔的信中却很少提到我们可以称之为消遣的东西。在阅读任何一位作家的信件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去发现哪些话题是作者忽略或很少提及的;托克维尔几乎完全忽略了任何可能使他的头脑摆脱焦虑的或娱乐性的话题——与朋友一起进餐、聚会、看戏、娱乐活动、度假、财务问题、业余爱好、投机、看闲书,以及体育活动。即使他一定程度上介入过其中的某些活动,但他的主要“消遣”看来只有三种:思想创造、政治活动以及朋友之间的愉快之事。
虽然托克维尔可能认为,他的声望并不在于终归失败的政治活动,但就创作来说,创作本身也没有减轻焦虑并给他带来快乐。他告诉博蒙,在严冬般的六个月中,他头脑中所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学术著作,这也是他唯一的消遣,但是,即便是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前后两卷都受到称赞之后,他在给兄弟的信中仍然说道,未曾料想到的成就并不能给他“完全的快乐”,因为“我的生活阅历足以让自己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美好的事物,它带来的享受能完全吸引我,让我满足。” [7]相对而言,政治活动更能让他激动。“没有什么快乐可与政治上的成功相比,尤其是当你为那些重大问题而兴奋、而你的支持者给予的同情又一再使这种兴奋之情升温时。”[8]然而,他的政治活动徒劳无功,对那个时代法国所有可能的政治替代方案他都感到厌恶,这些都让他深受挫折。
吸引托克维尔投身政治的,不仅有政治问题的严肃性,而且还有能与朋友们亲密合作的前景。总的来说,友谊看来给托克维尔带来了他能够拥有的大部分快乐。确实,从政治上说,友谊对托克维尔很重要,因为与朋友采取共同行动——以联合或团体的方式——可以削弱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威胁。不过这些信件自始至终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友谊内在的重大意义的故事,友谊本身就是目的。他曾说,“只有在父亲和妻子那里,才有真正的和永远的深情”,因为“与这种情感比起来,所有其他的友谊都只是不完整、难以真正起到作用的感情”(第94封信),但这番话只是他关于友谊对个人和政治事务之意义的终生信念的一次偏离。诚然,友谊给托克维尔带来过痛苦。当路易·德·凯戈莱退出实际政治活动、以保持他君主主义原则的纯洁性,当他拒绝或无力从事托克维尔认为他能够从事的思想创造、并最终转向了被托克维尔目为令人憎恶的商界时,托克维尔与他的深厚友谊逐渐淡薄了。在1844年的那场争吵中,托克维尔和博蒙都深深伤害了对方,这场起因于政治分歧和误解的争吵过后[9],两人的友谊看来已不够密切,直到1848年革命使他们再次走到一起。
尽管如此,友谊对托克维尔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22岁的时候,他在给凯戈莱的信中说,我如何深刻地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友谊的价值。让我们全力维护这份情感吧,亲爱的路易,只有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可靠、最持久的”(第4封信)。而对于博蒙,这个曾与他一起到美国和阿尔及利亚旅行、两次旅途中都曾在他重病时照料他的人,这种感情只会更加亲密。1855年,托克维尔曾回忆起此前的25年,虽然有些感伤和怀旧,但最后还是下了一个愉快的结论。“为进一步让自己振作起来,我想起了那个与我一起在孟菲斯捕猎鹦鹉的朋友,直到今天他依然是我的知己,我想起了时间只是使我们之间当时的信任和友谊更加紧密”(第82封信)。在本书的最后一封十分悲伤的信中,病中的托克维尔绝望地请求博蒙前来帮助他,这再次证明了他们友谊的力量。在读过他们长期往来的书信之后,任何读者都会认为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结尾。
托克维尔和法国浪漫主义
托克维尔不能被称作浪漫主义者,因为他更容易让人想起巴尔扎克和斯汤达尔等现实主义者,而非茹勒·米什莱和阿尔方斯·德·拉马丁等浪漫主义者(见第三章关于拉马丁的注释)。不过,他的焦虑不安会让任何法国思想史的研究者想起许多他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者的幻灭感,拉马丁《沉思集》(1820年)中的忧郁,弗朗索瓦·夏多布里昂笔下的著名人物勒内表现出的空虚,都是这种幻灭感的典型体现。所以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根据这些信件,可以认为托克维尔——他曾嘲笑过那些触目伤怀的浪漫主义者,而且更喜欢博叙埃主教,而不是阿尔弗雷德·德·缪塞——是属于自己所处的浪漫主义时代中的一员。他不仅在给未婚妻的信中玛丽·莫特莱的信中复活了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第16封信),而且法国浪漫主义的一些特征贯穿在他的信件中。
首先,虽然托克维尔在其出版的著作中经常表现得十分冷静,分析问题十分明晰,但我们也发现,他渴望冒险,热衷于政治运动,甚至渴望成就伟大的业绩。当他19岁的时候,他在给凯戈莱的信中谈到要溜出去看看英国,谈到他们“剩余的时间去漫游”的梦想(第2封信)。三年之后他又哀叹说,研究法律正使他变成一台机器,变成一个专业狭隘、无法具备高度的思维能力、无力从事重大事业的人(第3封信)。如果读者认为托克维尔是一个沉迷于书卷的人,认为他在引经据典的研究之外就无所适从,那么他的书信中如此频繁地表露出的对重大政治作为的渴望则会让读者吃惊。1835年,他曾袒露了这样一种愿望:希望上苍赐予他成就某种伟大事业的机会,让他能扑灭驱使他展开行动的“地狱之火”(第23封信)。1848年革命期间,他带着显而易见的满足感对博蒙说:“也许一个我们可以采取光荣行动的时刻即将到来”(第56封信)。他拥护1789年的原则,憎恶拿破仑的独裁倾向,但又认为这个人是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出现的最卓越的人物,他甚至以为,鸦片战争中英国在南中国的征服是有益于进步的伟大举措,即便这必然意味着“世界的第五个部分对其他四个部分的奴役”(第36封信;另见第43和51封信)。
托克维尔的贵族背景和他与当时的浪漫主义一代人的某种亲和关系,使他难以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相调和,无法享受一种投身商业和聚集财富的相对平静的生活。1853年,博蒙遭遇经济困难,托克维尔很不请愿地提示说,博蒙几年前就应该从事商业活动以增加收入,但他随即又补充说:“当然,我并不希望看到你的整个生活都是为了增加收入,就像可怜的路易(·德·凯戈莱)正在做的那样,即便你是出于为孩子打算的良好意愿”(第73封信)。虽然托克维尔偶尔也表现出对宁静而不为钱财所苦的中产阶级生活的向往,但他还是觉得,这样的生活对他个人而言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从精神上也感到厌恶。他在一封信中宣称,他宁愿作为一个士兵远渡中国、或者赌上自己的命,也不愿过“马铃薯”一般的生活——这就是他对普通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描绘(第18封信)。托克维尔还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面前夸口说,法国应在与英国的争端中持强硬立场,以维护其军事和民族荣誉,而不应该怯懦地退缩,以修建铁路来自我安慰(第40封信)。毫无疑问,他觉得与自己所处的商业世界格格不入,而他对冒险和光荣的渴求,无论对于前几个世纪被理想化的贵族风尚还是某些浪漫主义者的不满心态而言,都更为相称。“有时我担心自己会变成像唐吉诃德似的疯子。一种我们现代少有的英雄主义充塞了我的头脑,当我从这梦幻中走出以面对现实时,我有一种陡然跌落的感觉”(第31封信)。
托克维尔还具有他那一代浪漫主义者的另一个特点:他欣赏强烈的激情,虽说他深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但有时他并不信任过分的推理。他曾说,“对我来说,理智就像一个阻止我采取行动、但又不能阻止我在铁窗后咬牙切齿的囚笼”(第42封信)。相反,他赞赏那些会驱使人们去强烈关注几乎任何事物的激情:
随着自己日益远离年轻时代,我对情感有了更多的关注,几乎可以说是尊重了。当这些情感是良好的时,我会喜爱它们,当它们是不好的时候,我甚至无法确定是否该讨厌它们……我们今天最少见的东西就是激情,真正可靠的、调节并引导生活的激情。我们不再知道愿望、热爱、仇恨。怀疑和博爱使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无能为力——无论是最邪恶的还是最高尚的……
在他去世前不到一年的时候,他又提到了这种情感,哀叹说人们已经没有强烈的感情,既没有强烈的爱也没有强烈的恨,唯一指望的就是尽快在交易所赚钱(第103封信)。
托克维尔之所以感到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部分原因是,他强烈地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历史转折期。这同样是法国浪漫主义的一个特征。缪塞曾说:“一切存在过的东西都已消失,一切将会出现的东西还没有到来。我们的苦恼都是因为无法看得更远。”[10]同样,圣西门也说“摇摆在两种秩序之间,一种已经被摧毁且不可能恢复,另一种正在到来但尚未固定。”[11]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荣光早已远去,而某些人憧憬的黄金时代又为时尚早,所以那一代的许多浪漫主义者觉得他们注定要生活在一个过渡时期,一个政治堕落、文化粗糙的时期。虽然托克维尔也表达出这种情感,但他认为生活在过渡时代是件好事。他觉得,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便于他分析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优点和缺陷。在一封写给亨利·里夫的著名信件中,托克维尔最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论点:“我出生之时,贵族制度已然死亡,但民主制还根本不存在;因此我的本能不能驱使我盲目地转向这一方或那一方……总之,我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保持着很好的平衡,以致从天性和本能上说,我觉得自己不会更偏向哪一方,而且我无需作出巨大的努力便可平静地看待这两个方面”(第28封信)。后来托克维尔把这一转折描述成“资产阶级和工业因素对于贵族阶级和地产的胜利”,但他不知道未来对这一转变的判断是好是坏(第72封信)。不管未来如何,虽然他仍期望自由,但他很担心新的专制主义出现;像他同时代的很多浪漫主义者一样,托克维尔也强烈地感受到,在这个政治和文化都很苍白的过渡时代,他应该争取最好的结果。
对时代的失望
托克维尔很长时间内都是个活跃的政治人物,但政治生涯总是带给他恼怒和苦涩。1839-1848年,托克维尔曾是七月王朝的众议员,但在当时的议会政治中,人们要么与基佐、要么与梯也尔站在一起,否则在政治上注定无能为力,但基佐(参见第二章注释)主张维持现状,而梯也尔(参见第二章注释)靠的是野心计划、而非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来领导反对派。正像托克维尔对皮埃尔-保罗·卢瓦耶-科拉尔所说的,无论是基佐和还是梯也尔,“我从思考方式和情感方式上就反感这两个人。我蔑视他们”(第42封信)。梯也尔特别让他感到气愤:“我所热爱的,他则仇恨或嘲笑;他所热爱的,我则恐惧或蔑视”(第50封信)。在另一封信中,他哀叹说,“如果是在别的时候、同别的人在一起,我或许能做得更好。但时间会带来转机吗?我所看到的这些人会被更好的、或至少是不那么‘坏’的人取代么?我对国家最近的变化、而不是对我自己感到失望。我们时代真正的噩梦是,在自我面前看不到爱与恨,而只有蔑视”(第42封信)。
托克维尔试图在众议院保持独立,他与针对基佐的左翼反对派联合,企图组建一个自己的反对派,并努力分化巴罗(见第三章注释)和梯也尔,希望巴罗能够提供另一条可行的道路。但他的努力总是归于徒劳。虽然他很担心1848年的革命,但当时他对博蒙说出了一个秘密,并为此长长地松了口气——基佐、梯也尔和七月王朝那些无聊的争论终于结束了:“我们肯定还会看到更坏的政府,但现在的这个毕竟不会再看到了,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事”(第56封信)。然而,当1848年革命终于结束、当路易·拿破仑当选为总统并以武力称帝之后,托克维尔更加沮丧了。托克维尔一度把路易·拿破仑说成“一个伟大的民族面前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最拙劣的篡权者”(第64封信),但正是这个人给法国带来了秩序,并推动了工业发展——但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公民已经养成了“奴役的爱好”(第87封信)。最后,托克维尔通过学术研究和阅读过去的著作来逃避这个时代。“我们四周是以欧洲各种主要语言出版的最好的书。只有卓越的书才可以进入我的图书馆;它的藏书不算多,特别是19世纪的书不占多大地位,告诉您这一点就足够了”(第91封信)。
对于托克维尔的失望感,我们可以找到两个基本原因。首先,法国已经丧失了信心,它不再尝试在政治和思想方面从事伟大的事业,只忙于那些被托克维尔称为几乎“无处不在的卑劣行径”(第29封信)。虽然法国在上个世纪表现得极其骄傲和崇高,但他那个时代的法国则显得很卑微,甚至无法进行细微的改进。“以前我们觉得可以改变自己,现在我们认为无力进行改革……以前我们认为无所不能,今天我们觉得一无所能”(第78封信)。法国已经变成一个疲惫的国家,它没有了追求成就的动力,托克维尔很喜欢说它“令人厌倦”(第91封信)。更糟糕的是,托克维尔认为法国正在丧失其作为世界思想中心的地位,并说,如果博叙埃和帕斯卡尔造访19世纪,他们会认为法国正在“向半野蛮状态倒退。”[12]
如果[17和18世纪]杰出的论者和作家得以复生,我认为,他们对现代社会的单调乏味,比对煤气、汽船、氯仿、电报等东西更感到吃惊。[13]
他在给博蒙的信中说,法国正变得“贪婪而轻浮”,人人都在忙着挣钱,要么就是惦记着如何“疯狂”花钱。[14]
托克维尔感到失望的第二个原因更具政治色彩。在早年的一封信中,他抱怨广泛存在的对“所有能扰动社会的观念”的“漠不关心”,因为“每个人都越来越关心个人利益”(第14封信)。法国人对于政治日益冷漠,因为他们把政治仅仅看作“一场人人都在追逐胜利的游戏,”看作一场戏剧,剧中的角色并不关心戏剧的结果,而只在乎个人角色的成功和掌声(第50封信)。托克维尔开始怀疑,政治世界中“是否真的存在原则”,人们是否只是为了一己私利才宣扬原则(第29封信)。简言之,他之所以感到绝望,是因为法国人已经远离政治、陷入冷漠,因为法国的政治领导人并不是在运用政治原则,而是把政治看作增强人事或物质私利的一种投资。
不过,托克维尔并没有责怪法国人民。他抱怨的是随掌权的中产阶级而来的贪婪习气和自私德行。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没有远大抱负,它只想以“物质享乐和卑微的满足感”来娱乐人民(第40封信)。托克维尔把七月王朝的资产阶级描绘成“最自私最贪婪的财阀集团”,它“把政府看作一桩生意”,而且他认为中产阶级无非是个新兴的、腐败而庸俗的贵族阶层。[15]在他晚年的一封信中,托克维尔甚至梦想着一场由“开明”阶级领导的、法国人民全力投入的新革命(第100封信)。
虽然托克维尔深感失望,但他很少失去对未来的希望,而且每当别人批评法国的时候,他会很愤怒。他的信件对某个作者的排斥,这种情况通常就像提到某个作者一样重要,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发现,托克维尔确实是个法国人,因为他很少提到外国作者。虽然他偶尔也讨论一下普鲁塔克和马基雅维里等经典作家,但是,对于那些可以被现代读者看作伟大的英国或德国政治思想家的人,如洛克、休谟、斯密、柏克、边沁、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人们要想在托克维尔的信件中发现他们不止一次被提及,那纯属徒劳。众所周知,他声称英国是他的第二祖国,他也访问过英国和德国,但是,像很多法国思想家一样,托克维尔以为巴黎才是世界的精神首都。在他自己的精神宇宙观中,法国作家位于宇宙的中心,英国和德国的作者只是遥远的卫星。
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使得托克维尔对英国抱有终生的矛盾心态。对于英国,他偶尔有赞赏,但经常批评它。19岁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了那种法国人的偏见,当时他对凯戈莱夸口说,他们要去看看“那些英国猪,在我们这里,他们总是被描绘得很强壮很富足”(第2封信)。他认为美国和法国是引领世界走向民主的伙伴,虽然这个说法有点自欺欺人。相反,英国则陷入了贵族制的泥沼中。在一封写自英国的信中,托克维尔说,“在我看来,贵族精神已经深入到所有阶层……总之,我在这里看不到任何我们在美国看到的东西”(第15封信)。几乎1/4个世纪之后,虽然他赞赏英国的阶级合作、悲叹法国的阶级冲突,他仍然断定“贵族的地位看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稳固”,在英国,“政府由极少数家族掌握”(第97封信)。作为1844-1845年间《商界报》的支配性角色,托克维尔更为直接地表露了他的立场(以及希望):
没有哪个地方的贵族制像英国那样根深蒂固。没有哪个地方像法国这样彻底地接受平等的原则……因此法国的关键所在是要以自由制度普遍取代专制制度……但这对英国来说无所其谓。[16]
当托克维尔因声称英国富人对穷人不公正而惹恼拿骚·威廉·西尼奥尔时,托克维尔为自己辩护说:“在我得到相反的证据之前,我仍将认为,在英国,富人一点一滴地把社会条件给与人们的几乎所有利益都据为己有”(第20封信)。在1855年的一封信中,托克维尔似乎很高兴看到英国正任由“一个平庸而软弱的政府”折腾(第83封信)。
有意思的是,由于托克维尔深信法国精神上的衰落,在面对那些抨击法国没有创造出伟大的精神成就的言论时,托克维尔似乎不可能为法国辩护,即便他希望这样做。当阿图尔·德·戈比诺发起攻击时,托克维尔只能援引拉马丁和平庸的斯克里布来捍卫法国人的文学才能(第103封信)。这并不是因为托克维尔不熟悉法国的文坛人物。除了福楼拜和波德莱尔两个显著的例外,他在不同的背景下提到了法国当时几乎全部的重要作家:巴尔扎克、贝朗瑞、夏多布里昂、大仲马、戈蒂埃、雨果、拉马丁、缪塞、圣伯夫、乔治·桑、斯克里布、欧仁·苏——他几乎肯定知道斯汤达尔。[17]托克维尔为何不能捍卫19世纪法国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成就呢?也许是因为他对所有关于文学的重要辩论都不了解,这个十分政治化的人物当然没有什么真正的愿望,要去深入研究当代文学。也许对自己时代的失望使他不能承认当时法国文学的高度成就。
宗教的重要意义
虽然托克维尔偶尔表达过对有组织的宗教的敌意,但他的信件明白无误地表明,他是个非常注重宗教的人,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在思想活动中,他都很看重宗教的价值。例如,在早年的一封信中,他承认对这个世界是否有确定的真理深感焦虑和困惑:“那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时候;我只能把自己同一个头晕目眩的人相比——仿佛他脚下的地板在发抖,他周围的墙壁在晃动。甚至今天,我想起那个时期仍带有一种恐惧的感觉。可以说,当时我同这种疑惑进行了直接交锋,而且这样做时我很少会感到更多的失望”(第10封信)。在另一封信中,他似乎要将自己的疑虑投射到别人那里。他给凯戈莱写道,美国的新教徒可以选择的信仰很宽泛,但是“这样的画面肯定会把新教徒的精神投入某种必然的怀疑论中”,所以托克维尔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会投入天主教那富有权威的怀抱中(第8封信)。人们肯定会好奇,他自己在宗教上的困境是否影响到他对美国宗教的分析,另一方面,虽然托克维尔对天主教会心存疑虑,但人们肯定会怀疑,托克维尔是否真的不喜欢天主教提供的使人宽慰的确定性。
如果要在托克维尔发表的著作中寻找有关他个人道德立场之哲学基础的系统讨论,那纯属徒劳。不过,从他的信件来看,他认为基督教是其最重要的道德前提。托克维尔的朋友戈比诺是19世纪最重要的种族主义理论家之一,但托克维尔激烈地反对他朋友的观点,其中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戈比诺的理论违反全部的基督教信仰:“显然,基督教倾向于让所有人都成为兄弟和平等者。您的理论至多是把他们看作堂兄弟,而他们共有的父只是在天上;在尘世,从出生时的权利上说,他们只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主人和奴隶;这种观点是如此正确,以致您的理论得到——哪些人呢?——黑奴的所有主们的赞同、引用和评论……”(第92封信)。托克维尔一度考虑写一部论述前几个世纪的道德哲学的著作——但他从未对此进行过透彻的研究——也许是因为他仍然深信,虽然现代哲学家们有那么多的哲学论述,但没有一个人对基督教教义作过有意义的补充。正如他在1843年给戈比诺的一封信中说的:
现代道德哲学家的著作或创见中,有哪些是真正新颖的呢?……难道他们真的为人类的义务奠定过什么新的根基、乃至提出过什么新的解释吗?……透过我思维中的全部黑暗领域,我只能认识到一点:对我而言,完成这场有关义务和权利的全部观念之革命——您似乎更愿意称之为转变——的似乎是基督教;观念毕竟是全部道德认识的基础……因此基督教极大地彰显了所有人之间的平等、一致和博爱。[18]
托克维尔很少进行哲学思辨;实际上,他把这种思辨称作“一种人们愿意承受的自我折磨”(第10封信)。他的信件一再表明他所忽视的东西是什么。读者找不到关于自然权利学说、康德的绝对律令和英国功利主义的评论,因为托克维尔在伦理上的前提预设明显植根于他所受的天主教教育,以及某种政治责任观念。尽管他对天主教会和他所出身的贵族阶级多有顾虑,但在他的道德信念中可以发现这两种传统的痕迹,而且他的信念仍然非常坚定,不过有关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如果说宗教在他的私人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么宗教在他的思想活动中同样很重要。托克维尔从未提出过全面的历史理论,而且他肯定没有概括出历史发展规律的抱负。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未来具有令人不安的不可确定性,它可能走向伟大的民主自由,也可能导向新型的民主专制。不过,借助于基佐的学说,他认为欧洲历史发展中有个隐约可见的趋势,这就是不断增长的平等的趋势。虽然他偶尔也对这一历史进程作一些经济的、政治的或阶级的分析,但在公开论证中他则以神的意图为依据。《论美国的民主》的读者都知道,托克维尔以为“天意”正推动欧洲走向不可抗拒的平等。之所以这样表述他的论点,也许是为了让读者更易于接受之,[19]因为这比基佐的阶级分析要简单得多,但我认为他这样做也是出于自己的信念,他好像从来没有从博叙埃的神引导历史的观点中解脱出来。在给凯戈莱的一封信中,他说:“我不能相信,神几个世纪来一直把两三百万人推向状态平等,以让他们最后终结于提比略和克劳狄的专制主义”(第19封信)。他曾对戈比诺恼火,质疑后者的学说的价值及其实际影响,并提出,神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要我们最后归结于戈比诺所描绘的消极奴役状态:“我对您的信心要少于对神的善良和正义的信心”(第92封信)。
不过,托克维尔的基督教信仰带有难以磨灭的政治色彩。很多时候,他总想将政治自由和基督教教义调和起来,而在英国的一次旅行看来让他发现了这种美妙的结合:“它让我看到了宗教道德和政治道德之间、私人品德和公共品德之间、基督教和自由之间的完美的和谐”(第96封信)。托克维尔争辩说,有太多的基督徒认为,当他们坚持自己的个人信仰、甚或进行私人慈善活动的时候,他们的义务就完成了。但是托克维尔来自一个具有政治传统的家族,他的父亲担任过公职,他的外曾祖父拉穆瓦尼翁·德·马勒泽尔布是旧制度时代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一位允许出版《百科全书》、并在路易十六因叛国罪而接受审判时替国王出庭的王家官员。因此,托克维尔的教养使他以为,宗教不仅支持个人美德,同样还应支持政治义务和政治参与。他还在一封信中回忆起他祖母对她儿子的教导:宗教要求人们履行个人道德和公共责任,它既要求人们对其邻人宽厚仁慈,也要求他参与国家事务(第90封信)。
托克维尔的信件表明,他是一个热情地献身于把自己最高的个人信仰运用于公共领域之事业的人。它们还表明,托克维尔最个人化的关怀——他的焦虑、他的失望、他对冒险和政治荣誉的渴望、他的宗教信念——影响了他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运动。我们对这个人了解的越多,就会觉得他并不那么政治化。
罗杰·博谢
于洛杉矶西方学院
[1] 目前,托克维尔著作的权威法文版《全集》(, Paris : Gallimard, 1951—)正在J. P. 迈耶主持下出版,本书后文将标为 (M)。另见Alexis de Tocqueville, (《作为众议员的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给选举代理人保罗·克拉默冈的信件,1837-1851年》) (Hamburg: Ernst Hauswedell &Co., 1972); 以及(《托克维尔全集》)(Paris : Michel Lévy Frères, 1860-1866),这部全集是在托克维尔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的主持下出版的,本书后文以 (B)指称。
[2] 最近的一些传记写得不错,但太短,而19-20世纪之交的传记则显得冗长乏味,且急于表明托克维尔是站在天主教会一边的。前一类传记如J. P. Mayer, e(《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政治生平研究》)(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1966),以及Edward Gargan, (《德·托克维尔》)( New York: Hillary House Publishers, 1965);后一类传记如Antoine Redier, (《德·托克维尔先生如是说》)(Paris: Librairie Académique Perrin, 1925)。
有两部关于托克维尔的北美之行及《论美国的民主》的创作的出色而详尽的著作,即George Wilson Pierson, (《托克维尔和博蒙在美国》)(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以及James T. Schleifer,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形成》)(Chapel Hill :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3] 希望全面研究托克维尔思想的读者可以参阅下列著作中的任意一部或多部:Jack Lively,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社会和政治思想》)(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62);Marvin Zetterbaum, (《托克维尔和民主问题》)(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Raymond Aron, , I, (《社会学主要思潮,I:孟德斯鸠、孔德、马克思、托克维尔》),Richard Howard和Helen Weaver译 (Garden City, N.Y. : Doubleday, 1968);R. Pierre Marcel,(《关于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政治评论》)(Paris : Librairie Félix Alcan, 1910);Maxime Leroy, , II, (《法国社会思想史,II:从巴贝夫到托克维尔》)(Paris : Gallimard, 1950);Hugh Brogan, (《托克维尔》)(London : Fontana, 1973);Seymour Drescher, Tocqueville and England(《托克维尔和英国》)(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Jean-Claude Lamberti, (《托克维尔和两种民主制》)(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3) ;Xavier de la Fournière,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一位独立君主派〉)(Paris : Librairie Académique Perrin, 1981);Roger Boesche, « The Prison : Tocqueville’s Model for Despotism ,»(“监狱:托克维尔眼中的专制主义典范”)(《西部政治学季刊》)XXXIII (December 1980) : 550-563;Roger Boesche, « The Strange Liberalism of Alexis de Tocqeville,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奇特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史》)II (Winter 1981) : 495-524;Roger Boesche, «Why Could Tocqueville Predict So Well ? »(“托克维尔的预见力为何如此之好?”)(《政治理论》)XI (February 1983) : 79-103;Georges Lefèbvre, « A propos de Tocqueville, »(“关于托克维尔”)(《法国革命史年鉴》)XXVII (October-December 1955) : 313-323;Harold Laski, « Alexis de Tocqueville and Democracy,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和民主制”)in (《维多利亚时代几位代表性思想家的社会和政治思想》), ed. F. J. C. Hearnshaw, pp. 100-115 (London : George Harrap & Co., 1933)。
[4] 见后文第一封信;Alexis de Tocqueville and Nassau William Senior,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和拿骚·威廉·西尼奥尔通信及谈话录》), 2 vols. in 1, ed. M. C. M. Simpson, M. C. M.. Simpson夫人译 (New York : Augustus M. Kelley, 1968),1 : 125 ; 后文称作。
[5] 见后文第23封信;以及Tocqueville, (M), VIII, pt. 1,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和古斯塔夫·德·博蒙通信集》), p. 499 ; 后文标为。
[6] Tocqueville, (M), XIII, pt 1, , p. 418(《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和路易·德·凯戈莱通信集》),后文标作。
[7] Tocqueville, Oeuvres (M), VIII, pt. 3, , pp. 153-154 ; 及后文第39封信。
[8] Tocqueville, , 2 :206-207.
[9] 第47封信及第48封信(博蒙的回复)。
[10] Harry Levin, (《魔法之门:五位法国现实主义者研究》)(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79-80.
[11] Henri de Saint-Simon, (社会组织:关于人的科学及其他》), Felix Markham编译(New York : Harper & Row, 1964), p. 60.
[12] Tocqueville, , 1 :140-141.
[13] Ibid., 2:85.
[14] Tocqueville, (M), VIII, pt. 3, , p. 469.
[15] Tocqueville, Correspondance…Senior, 1 :134 ; Tocqueville,(《回忆录》),George Lawrence译(Garden City, New York. : Doubleday, 1971), p. 6 ; 见后文第52封信。
[16] (《商界报》), September 6, 1844, and January 21, 1845. 关于托克维尔在《商界报》的观点的详细讨论,见Roger Boesche, « Tocqueville and : A Newspaper Expressing His Unusual Liberalism », XLIV (April-June 1983) : 277-292.
[17] 1844-1845年,当托克维尔控制着《商界报》的时候,他对大部分上述作家都作过评论。另见Oeuvres (M), VI, pt. 1,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和亨利·里夫及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通信》), p. 320, 在一篇为密尔写的评论中,托克维尔展现了他对法国文学的熟悉;见R. Virtanen, « Tocqueville and the Romantics », XIII (Spring 1959) : 167-185。最后,由于托克维尔和斯汤达尔都是文学批评家让-雅克·安培的亲密朋友,所以托克维尔很可能熟悉斯汤达尔的作品。
[18] Alexis de Tocqueville, (《欧洲革命和与戈比诺的通信》),John Lukacs译(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1968),pp. 190f.
[19] 见Zetterbaum, , ch. 1.
具体描述
读后感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用户评价
法国大革命是旧制度的延续,而不是断裂。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社会制度已经在发生重大变化了。大革命延续的最重要的事物,是中央集权制。法国最重要的中间权力是贵族的独立和社会领导地位已经崩溃了。旧制度(绝对君主制)的最大影响是破坏了法国传统社会的这种政治-社会结构,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机构取代了过去的中间权力和自治机构。
评分法国大革命是旧制度的延续,而不是断裂。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社会制度已经在发生重大变化了。大革命延续的最重要的事物,是中央集权制。法国最重要的中间权力是贵族的独立和社会领导地位已经崩溃了。旧制度(绝对君主制)的最大影响是破坏了法国传统社会的这种政治-社会结构,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机构取代了过去的中间权力和自治机构。
评分法国大革命是旧制度的延续,而不是断裂。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社会制度已经在发生重大变化了。大革命延续的最重要的事物,是中央集权制。法国最重要的中间权力是贵族的独立和社会领导地位已经崩溃了。旧制度(绝对君主制)的最大影响是破坏了法国传统社会的这种政治-社会结构,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机构取代了过去的中间权力和自治机构。
评分法国大革命是旧制度的延续,而不是断裂。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社会制度已经在发生重大变化了。大革命延续的最重要的事物,是中央集权制。法国最重要的中间权力是贵族的独立和社会领导地位已经崩溃了。旧制度(绝对君主制)的最大影响是破坏了法国传统社会的这种政治-社会结构,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机构取代了过去的中间权力和自治机构。
评分法国大革命是旧制度的延续,而不是断裂。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社会制度已经在发生重大变化了。大革命延续的最重要的事物,是中央集权制。法国最重要的中间权力是贵族的独立和社会领导地位已经崩溃了。旧制度(绝对君主制)的最大影响是破坏了法国传统社会的这种政治-社会结构,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机构取代了过去的中间权力和自治机构。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wenda123.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目录大全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