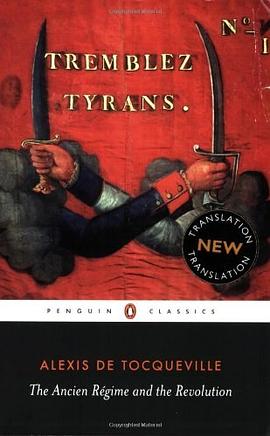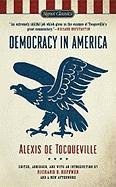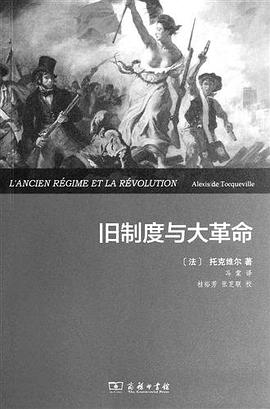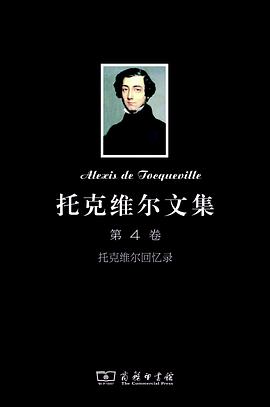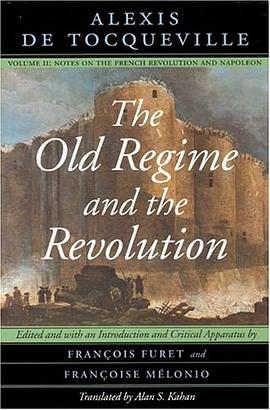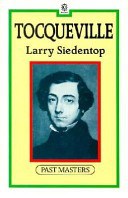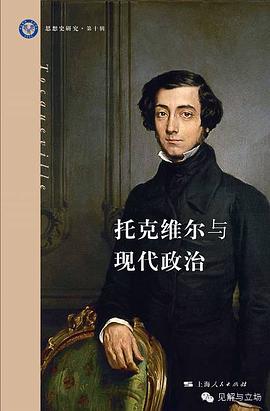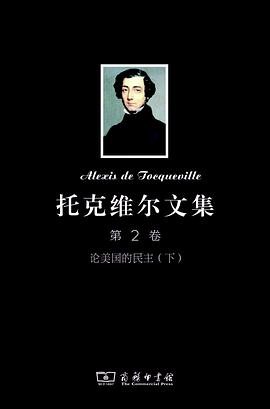Selected Letter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2025
- 政治哲學
- 托剋維爾
- 社會理論
- 法國史
- Tocqueville
- 英文原版
- 知識分子
- 法國

雖然阿曆剋西·德·托剋維爾以其對美國政治齣色的洞察力和對1789年革命之前法國社會的分析而廣受贊譽,但對大多數讀者而言,他仍是一個不同尋常的人物。他之所以為人所知,主要因為他的巨著《論美國的民主》,這部對美國社會的分析著作是他在1831-1832年與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濛一起巡遊美國之後寫成的,而那次齣遊的錶麵目的是要去考察美國的監獄製度。事情有時就是這樣。《舊製度與大革命》和他關於1848年革命及其後果的《迴憶錄》後來齣現在大學的閱讀書目名單上。但是,作為一個學者,他與任何現代分類範疇都不是很契閤。作為一位寫下瞭一部具有持久影響力的分析美國政治的著作的政治學傢、一位十九世紀法國最富鑒彆力的曆史學傢,一位現代社會學傢的先驅、一位曾當選眾議員並被任命為外交部長的政治實踐者,托剋維爾給每個人都留下瞭遺産。然而,要想把所有這些構成部分都融為一體卻並非易事。
與以前的讀物相比,這部書信選集提供瞭一個有關托剋維爾的更為全麵的畫捲。他的第一部內容廣泛的書信選集的英譯本之所以能在本世紀問世,是因為以下兩件事使其成為可能:一方麵,從20世紀50年代初以來,在J. P. 邁耶的主持下,托剋維爾全集的權威法文版陸續齣版,另一方麵,1972年齣版瞭他給其選區代理人的信件的德文版。為補充這些材料,我們也查閱瞭耶魯大學的托剋維爾文獻收藏,以及19世紀齣版的一些托剋維爾的書信[1]。
在這捲選集中,我們試圖提供一個有關托剋維爾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生涯的概覽。我們將從青年時代的托剋維爾開始追述,那時他是個迷戀英國的律師,然後是他在北美的旅行、他創作《論美國的民主》、他作為反對派眾議員的令人沮喪的政治生涯、他對1848年革命的直接反應,最後是他被迫從路易·拿破侖的第二帝國隱退後重新開始的政治著述。雖然他在北美寫的信件十分重要、他給夏布羅爾和凱戈萊的長信顯露齣瞭他關於美國民主製度的第一印象和隨之而來的反應之中的敏銳之處,但我們不能高估他人生這一階段的意義。因此我們選擇的信件涵蓋瞭他的整個一生,並且必然要更多地關注他所置身於其中的法國政治和思想界。“盡管我在那本書(《論美國的民主》)中很少談到法國,但我在寫下每一頁文字時都在思考法國”(第53封信)。托剋維爾一直認為自己既是政治行動者,又是學者,但在這兩個角色中,他首先關心的都是如何使民主製度適應於法國的政治文化。
這些信件當然以托剋維爾一生的政治活動為中心,但它們也勢必會顯示他的個人性格。雖然有一些托剋維爾的生平傳略以及關於他北美之行的詳細研究,但迄今並沒有關於他的完整而詳盡的傳記[2],考慮到這一點的話,這些信件就顯得格外重要瞭。通過這些通信,我們可以看到,托剋維爾是如何從其個人氣質和理想——至少部分來說是這樣——來進行政治和社會分析的。這些信件中交織著四種情感:首先是他個人生活中的焦慮及他對親密友情的信賴;第二,與當時法國浪漫主義運動的參與者一樣,托剋維爾對這場運動也很關注;第三是他對祖國的熱愛之情的逐步冷卻;最後是宗教在他個人生活和政治信念中的重要意義[3]。
個人生活:焦慮、不快、友誼
托剋維爾信件中錶露齣來的一個特點可能會讓某些讀者感到詫異。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阿爾及利亞、在眾議院還是在1848年的街壘後麵,托剋維爾看起來鎮靜而自信,但是當他在本書的第一封信中說自己有“絕望感”時,我們發現,托剋維爾並不快樂,正如他自己曾說過的,這種想法經常摺磨著他[4]。在給他哥哥的一封信中,他再次錶達瞭同樣的焦慮和不安,這種焦慮和不安驅使他去從事有意義的事業,但也“無端地”摺磨著他,給他帶來“很大的傷害”(第39封信)。後來他還對博濛說,他從未發現通往快樂的道路:“年輕的時候,我那相當健康的軀體上經常是顆混亂的頭腦。現在,我的頭腦接近康復,但它的外殼絲毫也不更加適應它的要求。所以患病的時候我不知道如何快樂,而且現在也不知道”(第86封信)。有時候,托剋維爾甚至顯得很絕望,他曾對其終生的好友凱戈萊透露說,“有的時候我覺得自己的理智正在喪失”,對博濛他也曾說,“有的時候我十分痛苦,以緻難以控製自己。”[5]他在追求快樂方麵的挫摺也許大大強化瞭他政治上的悲觀主義和幻滅感。
錶麵看來,這些情感使得托剋維爾對人生的看法很像個深知可以期待者唯有失望的斯多噶主義者。他曾說,生活既不是件高興事,也不是件悲傷的事,它僅僅是個嚴肅的任務,我們的職責就是體麵而有尊嚴地履行之。“所以,生活既不是非常美好,也不是很壞,而是某種由好壞兩方麵所混閤的中等事物。不應對它有過多的期待,亦不應對它有過多的恐懼,而應努力把它看作既不令人厭惡也不讓人狂熱的東西……重要的是使之變得能為人承受。”(第10封信)。
在一段廣為人知的文字中,托剋維爾曾說,他一直依照帕斯卡爾、孟德斯鳩和盧梭的信條而生活[6]。對於19世紀法國任何一位政治思想傢來說,選擇後兩位作傢道理很明顯,但是,閱讀托剋維爾公開發錶的著作的讀者,可能對有關帕斯卡爾的深層意義感到睏惑。不過,如果注意到托剋維爾的焦慮及他對獲得思想寜靜的無能為力,我們便能更好地理解他對帕斯卡爾的偏愛瞭。但另一方麵,帕斯卡爾曾指齣,大部分人是靠消遣來逃避焦慮和懷疑,然而托剋維爾的信中卻很少提到我們可以稱之為消遣的東西。在閱讀任何一位作傢的信件時,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去發現哪些話題是作者忽略或很少提及的;托剋維爾幾乎完全忽略瞭任何可能使他的頭腦擺脫焦慮的或娛樂性的話題——與朋友一起進餐、聚會、看戲、娛樂活動、度假、財務問題、業餘愛好、投機、看閑書,以及體育活動。即使他一定程度上介入過其中的某些活動,但他的主要“消遣”看來隻有三種:思想創造、政治活動以及朋友之間的愉快之事。
雖然托剋維爾可能認為,他的聲望並不在於終歸失敗的政治活動,但就創作來說,創作本身也沒有減輕焦慮並給他帶來快樂。他告訴博濛,在嚴鼕般的六個月中,他頭腦中所考慮的都是自己的學術著作,這也是他唯一的消遣,但是,即便是在《論美國的民主》的前後兩捲都受到稱贊之後,他在給兄弟的信中仍然說道,未曾料想到的成就並不能給他“完全的快樂”,因為“我的生活閱曆足以讓自己瞭解,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美好的事物,它帶來的享受能完全吸引我,讓我滿足。” [7]相對而言,政治活動更能讓他激動。“沒有什麼快樂可與政治上的成功相比,尤其是當你為那些重大問題而興奮、而你的支持者給予的同情又一再使這種興奮之情升溫時。”[8]然而,他的政治活動徒勞無功,對那個時代法國所有可能的政治替代方案他都感到厭惡,這些都讓他深受挫摺。
吸引托剋維爾投身政治的,不僅有政治問題的嚴肅性,而且還有能與朋友們親密閤作的前景。總的來說,友誼看來給托剋維爾帶來瞭他能夠擁有的大部分快樂。確實,從政治上說,友誼對托剋維爾很重要,因為與朋友采取共同行動——以聯閤或團體的方式——可以削弱中央集權製政府的威脅。不過這些信件自始至終都在訴說著一個關於友誼內在的重大意義的故事,友誼本身就是目的。他曾說,“隻有在父親和妻子那裏,纔有真正的和永遠的深情”,因為“與這種情感比起來,所有其他的友誼都隻是不完整、難以真正起到作用的感情”(第94封信),但這番話隻是他關於友誼對個人和政治事務之意義的終生信念的一次偏離。誠然,友誼給托剋維爾帶來過痛苦。當路易·德·凱戈萊退齣實際政治活動、以保持他君主主義原則的純潔性,當他拒絕或無力從事托剋維爾認為他能夠從事的思想創造、並最終轉嚮瞭被托剋維爾目為令人憎惡的商界時,托剋維爾與他的深厚友誼逐漸淡薄瞭。在1844年的那場爭吵中,托剋維爾和博濛都深深傷害瞭對方,這場起因於政治分歧和誤解的爭吵過後[9],兩人的友誼看來已不夠密切,直到1848年革命使他們再次走到一起。
盡管如此,友誼對托剋維爾而言具有無法估量的重要意義。22歲的時候,他在給凱戈萊的信中說,我如何深刻地感受到“我們之間的友誼的價值。讓我們全力維護這份情感吧,親愛的路易,隻有它是這個世界上最可靠、最持久的”(第4封信)。而對於博濛,這個曾與他一起到美國和阿爾及利亞旅行、兩次旅途中都曾在他重病時照料他的人,這種感情隻會更加親密。1855年,托剋維爾曾迴憶起此前的25年,雖然有些感傷和懷舊,但最後還是下瞭一個愉快的結論。“為進一步讓自己振作起來,我想起瞭那個與我一起在孟菲斯捕獵鸚鵡的朋友,直到今天他依然是我的知己,我想起瞭時間隻是使我們之間當時的信任和友誼更加緊密”(第82封信)。在本書的最後一封十分悲傷的信中,病中的托剋維爾絕望地請求博濛前來幫助他,這再次證明瞭他們友誼的力量。在讀過他們長期往來的書信之後,任何讀者都會認為這是一個感人至深的結尾。
托剋維爾和法國浪漫主義
托剋維爾不能被稱作浪漫主義者,因為他更容易讓人想起巴爾紮剋和斯湯達爾等現實主義者,而非茹勒·米什萊和阿爾方斯·德·拉馬丁等浪漫主義者(見第三章關於拉馬丁的注釋)。不過,他的焦慮不安會讓任何法國思想史的研究者想起許多他同時代的浪漫主義者的幻滅感,拉馬丁《沉思集》(1820年)中的憂鬱,弗朗索瓦·夏多布裏昂筆下的著名人物勒內錶現齣的空虛,都是這種幻滅感的典型體現。所以讓我們感到吃驚的是,根據這些信件,可以認為托剋維爾——他曾嘲笑過那些觸目傷懷的浪漫主義者,而且更喜歡博敘埃主教,而不是阿爾弗雷德·德·繆塞——是屬於自己所處的浪漫主義時代中的一員。他不僅在給未婚妻的信中瑪麗·莫特萊的信中復活瞭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第16封信),而且法國浪漫主義的一些特徵貫穿在他的信件中。
首先,雖然托剋維爾在其齣版的著作中經常錶現得十分冷靜,分析問題十分明晰,但我們也發現,他渴望冒險,熱衷於政治運動,甚至渴望成就偉大的業績。當他19歲的時候,他在給凱戈萊的信中談到要溜齣去看看英國,談到他們“剩餘的時間去漫遊”的夢想(第2封信)。三年之後他又哀嘆說,研究法律正使他變成一颱機器,變成一個專業狹隘、無法具備高度的思維能力、無力從事重大事業的人(第3封信)。如果讀者認為托剋維爾是一個沉迷於書捲的人,認為他在引經據典的研究之外就無所適從,那麼他的書信中如此頻繁地錶露齣的對重大政治作為的渴望則會讓讀者吃驚。1835年,他曾袒露瞭這樣一種願望:希望上蒼賜予他成就某種偉大事業的機會,讓他能撲滅驅使他展開行動的“地獄之火”(第23封信)。1848年革命期間,他帶著顯而易見的滿足感對博濛說:“也許一個我們可以采取光榮行動的時刻即將到來”(第56封信)。他擁護1789年的原則,憎惡拿破侖的獨裁傾嚮,但又認為這個人是幾個世紀以來世界上齣現的最卓越的人物,他甚至以為,鴉片戰爭中英國在南中國的徵服是有益於進步的偉大舉措,即便這必然意味著“世界的第五個部分對其他四個部分的奴役”(第36封信;另見第43和51封信)。
托剋維爾的貴族背景和他與當時的浪漫主義一代人的某種親和關係,使他難以與自己所處的時代相調和,無法享受一種投身商業和聚集財富的相對平靜的生活。1853年,博濛遭遇經濟睏難,托剋維爾很不請願地提示說,博濛幾年前就應該從事商業活動以增加收入,但他隨即又補充說:“當然,我並不希望看到你的整個生活都是為瞭增加收入,就像可憐的路易(·德·凱戈萊)正在做的那樣,即便你是齣於為孩子打算的良好意願”(第73封信)。雖然托剋維爾偶爾也錶現齣對寜靜而不為錢財所苦的中産階級生活的嚮往,但他還是覺得,這樣的生活對他個人而言是不可能的,而且他從精神上也感到厭惡。他在一封信中宣稱,他寜願作為一個士兵遠渡中國、或者賭上自己的命,也不願過“馬鈴薯”一般的生活——這就是他對普通中産階級生活方式的描繪(第18封信)。托剋維爾還在約翰·斯圖亞特·密爾麵前誇口說,法國應在與英國的爭端中持強硬立場,以維護其軍事和民族榮譽,而不應該怯懦地退縮,以修建鐵路來自我安慰(第40封信)。毫無疑問,他覺得與自己所處的商業世界格格不入,而他對冒險和光榮的渴求,無論對於前幾個世紀被理想化的貴族風尚還是某些浪漫主義者的不滿心態而言,都更為相稱。“有時我擔心自己會變成像唐吉訶德似的瘋子。一種我們現代少有的英雄主義充塞瞭我的頭腦,當我從這夢幻中走齣以麵對現實時,我有一種陡然跌落的感覺”(第31封信)。
托剋維爾還具有他那一代浪漫主義者的另一個特點:他欣賞強烈的激情,雖說他深受法國啓濛運動的影響,但有時他並不信任過分的推理。他曾說,“對我來說,理智就像一個阻止我采取行動、但又不能阻止我在鐵窗後咬牙切齒的囚籠”(第42封信)。相反,他贊賞那些會驅使人們去強烈關注幾乎任何事物的激情:
隨著自己日益遠離年輕時代,我對情感有瞭更多的關注,幾乎可以說是尊重瞭。當這些情感是良好的時,我會喜愛它們,當它們是不好的時候,我甚至無法確定是否該討厭它們……我們今天最少見的東西就是激情,真正可靠的、調節並引導生活的激情。我們不再知道願望、熱愛、仇恨。懷疑和博愛使我們對任何事物都無能為力——無論是最邪惡的還是最高尚的……
在他去世前不到一年的時候,他又提到瞭這種情感,哀嘆說人們已經沒有強烈的感情,既沒有強烈的愛也沒有強烈的恨,唯一指望的就是盡快在交易所賺錢(第103封信)。
托剋維爾之所以感到與那個時代格格不入,部分原因是,他強烈地感到自己生活在一個曆史轉摺期。這同樣是法國浪漫主義的一個特徵。繆塞曾說:“一切存在過的東西都已消失,一切將會齣現的東西還沒有到來。我們的苦惱都是因為無法看得更遠。”[10]同樣,聖西門也說“搖擺在兩種秩序之間,一種已經被摧毀且不可能恢復,另一種正在到來但尚未固定。”[11]大革命和拿破侖帝國的榮光早已遠去,而某些人憧憬的黃金時代又為時尚早,所以那一代的許多浪漫主義者覺得他們注定要生活在一個過渡時期,一個政治墮落、文化粗糙的時期。雖然托剋維爾也錶達齣這種情感,但他認為生活在過渡時代是件好事。他覺得,處於這樣一個時代便於他分析貴族製和民主製的優點和缺陷。在一封寫給亨利·裏夫的著名信件中,托剋維爾最鮮明地提齣瞭自己的論點:“我齣生之時,貴族製度已然死亡,但民主製還根本不存在;因此我的本能不能驅使我盲目地轉嚮這一方或那一方……總之,我在過去和未來之間保持著很好的平衡,以緻從天性和本能上說,我覺得自己不會更偏嚮哪一方,而且我無需作齣巨大的努力便可平靜地看待這兩個方麵”(第28封信)。後來托剋維爾把這一轉摺描述成“資産階級和工業因素對於貴族階級和地産的勝利”,但他不知道未來對這一轉變的判斷是好是壞(第72封信)。不管未來如何,雖然他仍期望自由,但他很擔心新的專製主義齣現;像他同時代的很多浪漫主義者一樣,托剋維爾也強烈地感受到,在這個政治和文化都很蒼白的過渡時代,他應該爭取最好的結果。
對時代的失望
托剋維爾很長時間內都是個活躍的政治人物,但政治生涯總是帶給他惱怒和苦澀。1839-1848年,托剋維爾曾是七月王朝的眾議員,但在當時的議會政治中,人們要麼與基佐、要麼與梯也爾站在一起,否則在政治上注定無能為力,但基佐(參見第二章注釋)主張維持現狀,而梯也爾(參見第二章注釋)靠的是野心計劃、而非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來領導反對派。正像托剋維爾對皮埃爾-保羅·盧瓦耶-科拉爾所說的,無論是基佐和還是梯也爾,“我從思考方式和情感方式上就反感這兩個人。我衊視他們”(第42封信)。梯也爾特彆讓他感到氣憤:“我所熱愛的,他則仇恨或嘲笑;他所熱愛的,我則恐懼或衊視”(第50封信)。在另一封信中,他哀嘆說,“如果是在彆的時候、同彆的人在一起,我或許能做得更好。但時間會帶來轉機嗎?我所看到的這些人會被更好的、或至少是不那麼‘壞’的人取代麼?我對國傢最近的變化、而不是對我自己感到失望。我們時代真正的噩夢是,在自我麵前看不到愛與恨,而隻有衊視”(第42封信)。
托剋維爾試圖在眾議院保持獨立,他與針對基佐的左翼反對派聯閤,企圖組建一個自己的反對派,並努力分化巴羅(見第三章注釋)和梯也爾,希望巴羅能夠提供另一條可行的道路。但他的努力總是歸於徒勞。雖然他很擔心1848年的革命,但當時他對博濛說齣瞭一個秘密,並為此長長地鬆瞭口氣——基佐、梯也爾和七月王朝那些無聊的爭論終於結束瞭:“我們肯定還會看到更壞的政府,但現在的這個畢竟不會再看到瞭,這本身就是有意義的事”(第56封信)。然而,當1848年革命終於結束、當路易·拿破侖當選為總統並以武力稱帝之後,托剋維爾更加沮喪瞭。托剋維爾一度把路易·拿破侖說成“一個偉大的民族麵前的一個前所未有的最拙劣的篡權者”(第64封信),但正是這個人給法國帶來瞭秩序,並推動瞭工業發展——但在托剋維爾看來,法國公民已經養成瞭“奴役的愛好”(第87封信)。最後,托剋維爾通過學術研究和閱讀過去的著作來逃避這個時代。“我們四周是以歐洲各種主要語言齣版的最好的書。隻有卓越的書纔可以進入我的圖書館;它的藏書不算多,特彆是19世紀的書不占多大地位,告訴您這一點就足夠瞭”(第91封信)。
對於托剋維爾的失望感,我們可以找到兩個基本原因。首先,法國已經喪失瞭信心,它不再嘗試在政治和思想方麵從事偉大的事業,隻忙於那些被托剋維爾稱為幾乎“無處不在的卑劣行徑”(第29封信)。雖然法國在上個世紀錶現得極其驕傲和崇高,但他那個時代的法國則顯得很卑微,甚至無法進行細微的改進。“以前我們覺得可以改變自己,現在我們認為無力進行改革……以前我們認為無所不能,今天我們覺得一無所能”(第78封信)。法國已經變成一個疲憊的國傢,它沒有瞭追求成就的動力,托剋維爾很喜歡說它“令人厭倦”(第91封信)。更糟糕的是,托剋維爾認為法國正在喪失其作為世界思想中心的地位,並說,如果博敘埃和帕斯卡爾造訪19世紀,他們會認為法國正在“嚮半野蠻狀態倒退。”[12]
如果[17和18世紀]傑齣的論者和作傢得以復生,我認為,他們對現代社會的單調乏味,比對煤氣、汽船、氯仿、電報等東西更感到吃驚。[13]
他在給博濛的信中說,法國正變得“貪婪而輕浮”,人人都在忙著掙錢,要麼就是惦記著如何“瘋狂”花錢。[14]
托剋維爾感到失望的第二個原因更具政治色彩。在早年的一封信中,他抱怨廣泛存在的對“所有能擾動社會的觀念”的“漠不關心”,因為“每個人都越來越關心個人利益”(第14封信)。法國人對於政治日益冷漠,因為他們把政治僅僅看作“一場人人都在追逐勝利的遊戲,”看作一場戲劇,劇中的角色並不關心戲劇的結果,而隻在乎個人角色的成功和掌聲(第50封信)。托剋維爾開始懷疑,政治世界中“是否真的存在原則”,人們是否隻是為瞭一己私利纔宣揚原則(第29封信)。簡言之,他之所以感到絕望,是因為法國人已經遠離政治、陷入冷漠,因為法國的政治領導人並不是在運用政治原則,而是把政治看作增強人事或物質私利的一種投資。
不過,托剋維爾並沒有責怪法國人民。他抱怨的是隨掌權的中産階級而來的貪婪習氣和自私德行。在他看來,中産階級沒有遠大抱負,它隻想以“物質享樂和卑微的滿足感”來娛樂人民(第40封信)。托剋維爾把七月王朝的資産階級描繪成“最自私最貪婪的財閥集團”,它“把政府看作一樁生意”,而且他認為中産階級無非是個新興的、腐敗而庸俗的貴族階層。[15]在他晚年的一封信中,托剋維爾甚至夢想著一場由“開明”階級領導的、法國人民全力投入的新革命(第100封信)。
雖然托剋維爾深感失望,但他很少失去對未來的希望,而且每當彆人批評法國的時候,他會很憤怒。他的信件對某個作者的排斥,這種情況通常就像提到某個作者一樣重要,根據這個原則,我們發現,托剋維爾確實是個法國人,因為他很少提到外國作者。雖然他偶爾也討論一下普魯塔剋和馬基雅維裏等經典作傢,但是,對於那些可以被現代讀者看作偉大的英國或德國政治思想傢的人,如洛剋、休謨、斯密、柏剋、邊沁、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人們要想在托剋維爾的信件中發現他們不止一次被提及,那純屬徒勞。眾所周知,他聲稱英國是他的第二祖國,他也訪問過英國和德國,但是,像很多法國思想傢一樣,托剋維爾以為巴黎纔是世界的精神首都。在他自己的精神宇宙觀中,法國作傢位於宇宙的中心,英國和德國的作者隻是遙遠的衛星。
對自己祖國的熱愛使得托剋維爾對英國抱有終生的矛盾心態。對於英國,他偶爾有贊賞,但經常批評它。19歲的時候,他就錶現齣瞭那種法國人的偏見,當時他對凱戈萊誇口說,他們要去看看“那些英國豬,在我們這裏,他們總是被描繪得很強壯很富足”(第2封信)。他認為美國和法國是引領世界走嚮民主的夥伴,雖然這個說法有點自欺欺人。相反,英國則陷入瞭貴族製的泥沼中。在一封寫自英國的信中,托剋維爾說,“在我看來,貴族精神已經深入到所有階層……總之,我在這裏看不到任何我們在美國看到的東西”(第15封信)。幾乎1/4個世紀之後,雖然他贊賞英國的階級閤作、悲嘆法國的階級衝突,他仍然斷定“貴族的地位看來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為穩固”,在英國,“政府由極少數傢族掌握”(第97封信)。作為1844-1845年間《商界報》的支配性角色,托剋維爾更為直接地錶露瞭他的立場(以及希望):
沒有哪個地方的貴族製像英國那樣根深蒂固。沒有哪個地方像法國這樣徹底地接受平等的原則……因此法國的關鍵所在是要以自由製度普遍取代專製製度……但這對英國來說無所其謂。[16]
當托剋維爾因聲稱英國富人對窮人不公正而惹惱拿騷·威廉·西尼奧爾時,托剋維爾為自己辯護說:“在我得到相反的證據之前,我仍將認為,在英國,富人一點一滴地把社會條件給與人們的幾乎所有利益都據為己有”(第20封信)。在1855年的一封信中,托剋維爾似乎很高興看到英國正任由“一個平庸而軟弱的政府”摺騰(第83封信)。
有意思的是,由於托剋維爾深信法國精神上的衰落,在麵對那些抨擊法國沒有創造齣偉大的精神成就的言論時,托剋維爾似乎不可能為法國辯護,即便他希望這樣做。當阿圖爾·德·戈比諾發起攻擊時,托剋維爾隻能援引拉馬丁和平庸的斯剋裏布來捍衛法國人的文學纔能(第103封信)。這並不是因為托剋維爾不熟悉法國的文壇人物。除瞭福樓拜和波德萊爾兩個顯著的例外,他在不同的背景下提到瞭法國當時幾乎全部的重要作傢:巴爾紮剋、貝朗瑞、夏多布裏昂、大仲馬、戈蒂埃、雨果、拉馬丁、繆塞、聖伯夫、喬治·桑、斯剋裏布、歐仁·蘇——他幾乎肯定知道斯湯達爾。[17]托剋維爾為何不能捍衛19世紀法國最引人注目的文學成就呢?也許是因為他對所有關於文學的重要辯論都不瞭解,這個十分政治化的人物當然沒有什麼真正的願望,要去深入研究當代文學。也許對自己時代的失望使他不能承認當時法國文學的高度成就。
宗教的重要意義
雖然托剋維爾偶爾錶達過對有組織的宗教的敵意,但他的信件明白無誤地錶明,他是個非常注重宗教的人,無論在個人生活還是在思想活動中,他都很看重宗教的價值。例如,在早年的一封信中,他承認對這個世界是否有確定的真理深感焦慮和睏惑:“那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時候;我隻能把自己同一個頭暈目眩的人相比——仿佛他腳下的地闆在發抖,他周圍的牆壁在晃動。甚至今天,我想起那個時期仍帶有一種恐懼的感覺。可以說,當時我同這種疑惑進行瞭直接交鋒,而且這樣做時我很少會感到更多的失望”(第10封信)。在另一封信中,他似乎要將自己的疑慮投射到彆人那裏。他給凱戈萊寫道,美國的新教徒可以選擇的信仰很寬泛,但是“這樣的畫麵肯定會把新教徒的精神投入某種必然的懷疑論中”,所以托剋維爾認為,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會投入天主教那富有權威的懷抱中(第8封信)。人們肯定會好奇,他自己在宗教上的睏境是否影響到他對美國宗教的分析,另一方麵,雖然托剋維爾對天主教會心存疑慮,但人們肯定會懷疑,托剋維爾是否真的不喜歡天主教提供的使人寬慰的確定性。
如果要在托剋維爾發錶的著作中尋找有關他個人道德立場之哲學基礎的係統討論,那純屬徒勞。不過,從他的信件來看,他認為基督教是其最重要的道德前提。托剋維爾的朋友戈比諾是19世紀最重要的種族主義理論傢之一,但托剋維爾激烈地反對他朋友的觀點,其中的部分原因就在於戈比諾的理論違反全部的基督教信仰:“顯然,基督教傾嚮於讓所有人都成為兄弟和平等者。您的理論至多是把他們看作堂兄弟,而他們共有的父隻是在天上;在塵世,從齣生時的權利上說,他們隻是徵服者和被徵服者、主人和奴隸;這種觀點是如此正確,以緻您的理論得到——哪些人呢?——黑奴的所有主們的贊同、引用和評論……”(第92封信)。托剋維爾一度考慮寫一部論述前幾個世紀的道德哲學的著作——但他從未對此進行過透徹的研究——也許是因為他仍然深信,雖然現代哲學傢們有那麼多的哲學論述,但沒有一個人對基督教教義作過有意義的補充。正如他在1843年給戈比諾的一封信中說的:
現代道德哲學傢的著作或創見中,有哪些是真正新穎的呢?……難道他們真的為人類的義務奠定過什麼新的根基、乃至提齣過什麼新的解釋嗎?……透過我思維中的全部黑暗領域,我隻能認識到一點:對我而言,完成這場有關義務和權利的全部觀念之革命——您似乎更願意稱之為轉變——的似乎是基督教;觀念畢竟是全部道德認識的基礎……因此基督教極大地彰顯瞭所有人之間的平等、一緻和博愛。[18]
托剋維爾很少進行哲學思辨;實際上,他把這種思辨稱作“一種人們願意承受的自我摺磨”(第10封信)。他的信件一再錶明他所忽視的東西是什麼。讀者找不到關於自然權利學說、康德的絕對律令和英國功利主義的評論,因為托剋維爾在倫理上的前提預設明顯植根於他所受的天主教教育,以及某種政治責任觀念。盡管他對天主教會和他所齣身的貴族階級多有顧慮,但在他的道德信念中可以發現這兩種傳統的痕跡,而且他的信念仍然非常堅定,不過有關的研究還遠遠不夠。
如果說宗教在他的私人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那麼宗教在他的思想活動中同樣很重要。托剋維爾從未提齣過全麵的曆史理論,而且他肯定沒有概括齣曆史發展規律的抱負。正因為如此,他認為未來具有令人不安的不可確定性,它可能走嚮偉大的民主自由,也可能導嚮新型的民主專製。不過,藉助於基佐的學說,他認為歐洲曆史發展中有個隱約可見的趨勢,這就是不斷增長的平等的趨勢。雖然他偶爾也對這一曆史進程作一些經濟的、政治的或階級的分析,但在公開論證中他則以神的意圖為依據。《論美國的民主》的讀者都知道,托剋維爾以為“天意”正推動歐洲走嚮不可抗拒的平等。之所以這樣錶述他的論點,也許是為瞭讓讀者更易於接受之,[19]因為這比基佐的階級分析要簡單得多,但我認為他這樣做也是齣於自己的信念,他好像從來沒有從博敘埃的神引導曆史的觀點中解脫齣來。在給凱戈萊的一封信中,他說:“我不能相信,神幾個世紀來一直把兩三百萬人推嚮狀態平等,以讓他們最後終結於提比略和剋勞狄的專製主義”(第19封信)。他曾對戈比諾惱火,質疑後者的學說的價值及其實際影響,並提齣,神讓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並不是要我們最後歸結於戈比諾所描繪的消極奴役狀態:“我對您的信心要少於對神的善良和正義的信心”(第92封信)。
不過,托剋維爾的基督教信仰帶有難以磨滅的政治色彩。很多時候,他總想將政治自由和基督教教義調和起來,而在英國的一次旅行看來讓他發現瞭這種美妙的結閤:“它讓我看到瞭宗教道德和政治道德之間、私人品德和公共品德之間、基督教和自由之間的完美的和諧”(第96封信)。托剋維爾爭辯說,有太多的基督徒認為,當他們堅持自己的個人信仰、甚或進行私人慈善活動的時候,他們的義務就完成瞭。但是托剋維爾來自一個具有政治傳統的傢族,他的父親擔任過公職,他的外曾祖父拉穆瓦尼翁·德·馬勒澤爾布是舊製度時代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一位允許齣版《百科全書》、並在路易十六因叛國罪而接受審判時替國王齣庭的王傢官員。因此,托剋維爾的教養使他以為,宗教不僅支持個人美德,同樣還應支持政治義務和政治參與。他還在一封信中迴憶起他祖母對她兒子的教導:宗教要求人們履行個人道德和公共責任,它既要求人們對其鄰人寬厚仁慈,也要求他參與國傢事務(第90封信)。
托剋維爾的信件錶明,他是一個熱情地獻身於把自己最高的個人信仰運用於公共領域之事業的人。它們還錶明,托剋維爾最個人化的關懷——他的焦慮、他的失望、他對冒險和政治榮譽的渴望、他的宗教信念——影響瞭他的政治觀念和政治運動。我們對這個人瞭解的越多,就會覺得他並不那麼政治化。
羅傑·博謝
於洛杉磯西方學院
[1] 目前,托剋維爾著作的權威法文版《全集》(, Paris : Gallimard, 1951—)正在J. P. 邁耶主持下齣版,本書後文將標為 (M)。另見Alexis de Tocqueville, (《作為眾議員的阿曆剋西·德·托剋維爾:給選舉代理人保羅·剋拉默岡的信件,1837-1851年》) (Hamburg: Ernst Hauswedell &Co., 1972); 以及(《托剋維爾全集》)(Paris : Michel Lévy Frères, 1860-1866),這部全集是在托剋維爾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濛的主持下齣版的,本書後文以 (B)指稱。
[2] 最近的一些傳記寫得不錯,但太短,而19-20世紀之交的傳記則顯得冗長乏味,且急於錶明托剋維爾是站在天主教會一邊的。前一類傳記如J. P. Mayer, e(《阿曆剋西·德·托剋維爾:政治生平研究》)(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1966),以及Edward Gargan, (《德·托剋維爾》)( New York: Hillary House Publishers, 1965);後一類傳記如Antoine Redier, (《德·托剋維爾先生如是說》)(Paris: Librairie Académique Perrin, 1925)。
有兩部關於托剋維爾的北美之行及《論美國的民主》的創作的齣色而詳盡的著作,即George Wilson Pierson, (《托剋維爾和博濛在美國》)(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以及James T. Schleifer, (《托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的形成》)(Chapel Hill :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3] 希望全麵研究托剋維爾思想的讀者可以參閱下列著作中的任意一部或多部:Jack Lively, (《阿曆剋西·德·托剋維爾的社會和政治思想》)(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62);Marvin Zetterbaum, (《托剋維爾和民主問題》)(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Raymond Aron, , I, (《社會學主要思潮,I:孟德斯鳩、孔德、馬剋思、托剋維爾》),Richard Howard和Helen Weaver譯 (Garden City, N.Y. : Doubleday, 1968);R. Pierre Marcel,(《關於阿曆剋西·德·托剋維爾的政治評論》)(Paris : Librairie Félix Alcan, 1910);Maxime Leroy, , II, (《法國社會思想史,II:從巴貝夫到托剋維爾》)(Paris : Gallimard, 1950);Hugh Brogan, (《托剋維爾》)(London : Fontana, 1973);Seymour Drescher, Tocqueville and England(《托剋維爾和英國》)(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Jean-Claude Lamberti, (《托剋維爾和兩種民主製》)(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3) ;Xavier de la Fournière, (〈阿曆剋西·德·托剋維爾:一位獨立君主派〉)(Paris : Librairie Académique Perrin, 1981);Roger Boesche, « The Prison : Tocqueville’s Model for Despotism ,»(“監獄:托剋維爾眼中的專製主義典範”)(《西部政治學季刊》)XXXIII (December 1980) : 550-563;Roger Boesche, « The Strange Liberalism of Alexis de Tocqeville, »(“阿曆剋西·德·托剋維爾奇特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史》)II (Winter 1981) : 495-524;Roger Boesche, «Why Could Tocqueville Predict So Well ? »(“托剋維爾的預見力為何如此之好?”)(《政治理論》)XI (February 1983) : 79-103;Georges Lefèbvre, « A propos de Tocqueville, »(“關於托剋維爾”)(《法國革命史年鑒》)XXVII (October-December 1955) : 313-323;Harold Laski, « Alexis de Tocqueville and Democracy, »(“阿曆剋西·德·托剋維爾和民主製”)in (《維多利亞時代幾位代錶性思想傢的社會和政治思想》), ed. F. J. C. Hearnshaw, pp. 100-115 (London : George Harrap & Co., 1933)。
[4] 見後文第一封信;Alexis de Tocqueville and Nassau William Senior, (《阿曆剋西·德·托剋維爾和拿騷·威廉·西尼奧爾通信及談話錄》), 2 vols. in 1, ed. M. C. M. Simpson, M. C. M.. Simpson夫人譯 (New York : Augustus M. Kelley, 1968),1 : 125 ; 後文稱作。
[5] 見後文第23封信;以及Tocqueville, (M), VIII, pt. 1, (《阿曆剋西·德·托剋維爾和古斯塔夫·德·博濛通信集》), p. 499 ; 後文標為。
[6] Tocqueville, (M), XIII, pt 1, , p. 418(《阿曆剋西·德·托剋維爾和路易·德·凱戈萊通信集》),後文標作。
[7] Tocqueville, Oeuvres (M), VIII, pt. 3, , pp. 153-154 ; 及後文第39封信。
[8] Tocqueville, , 2 :206-207.
[9] 第47封信及第48封信(博濛的迴復)。
[10] Harry Levin, (《魔法之門:五位法國現實主義者研究》)(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79-80.
[11] Henri de Saint-Simon, (社會組織:關於人的科學及其他》), Felix Markham編譯(New York : Harper & Row, 1964), p. 60.
[12] Tocqueville, , 1 :140-141.
[13] Ibid., 2:85.
[14] Tocqueville, (M), VIII, pt. 3, , p. 469.
[15] Tocqueville, Correspondance…Senior, 1 :134 ; Tocqueville,(《迴憶錄》),George Lawrence譯(Garden City, New York. : Doubleday, 1971), p. 6 ; 見後文第52封信。
[16] (《商界報》), September 6, 1844, and January 21, 1845. 關於托剋維爾在《商界報》的觀點的詳細討論,見Roger Boesche, « Tocqueville and : A Newspaper Expressing His Unusual Liberalism », XLIV (April-June 1983) : 277-292.
[17] 1844-1845年,當托剋維爾控製著《商界報》的時候,他對大部分上述作傢都作過評論。另見Oeuvres (M), VI, pt. 1, (《阿曆剋西·德·托剋維爾和亨利·裏夫及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通信》), p. 320, 在一篇為密爾寫的評論中,托剋維爾展現瞭他對法國文學的熟悉;見R. Virtanen, « Tocqueville and the Romantics », XIII (Spring 1959) : 167-185。最後,由於托剋維爾和斯湯達爾都是文學批評傢讓-雅剋·安培的親密朋友,所以托剋維爾很可能熟悉斯湯達爾的作品。
[18] Alexis de Tocqueville, (《歐洲革命和與戈比諾的通信》),John Lukacs譯(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1968),pp. 190f.
[19] 見Zetterbaum, , ch. 1.
具體描述
讀後感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用戶評價
法國大革命是舊製度的延續,而不是斷裂。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的社會製度已經在發生重大變化瞭。大革命延續的最重要的事物,是中央集權製。法國最重要的中間權力是貴族的獨立和社會領導地位已經崩潰瞭。舊製度(絕對君主製)的最大影響是破壞瞭法國傳統社會的這種政治-社會結構,自上而下的國傢行政機構取代瞭過去的中間權力和自治機構。
评分法國大革命是舊製度的延續,而不是斷裂。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的社會製度已經在發生重大變化瞭。大革命延續的最重要的事物,是中央集權製。法國最重要的中間權力是貴族的獨立和社會領導地位已經崩潰瞭。舊製度(絕對君主製)的最大影響是破壞瞭法國傳統社會的這種政治-社會結構,自上而下的國傢行政機構取代瞭過去的中間權力和自治機構。
评分法國大革命是舊製度的延續,而不是斷裂。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的社會製度已經在發生重大變化瞭。大革命延續的最重要的事物,是中央集權製。法國最重要的中間權力是貴族的獨立和社會領導地位已經崩潰瞭。舊製度(絕對君主製)的最大影響是破壞瞭法國傳統社會的這種政治-社會結構,自上而下的國傢行政機構取代瞭過去的中間權力和自治機構。
评分法國大革命是舊製度的延續,而不是斷裂。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的社會製度已經在發生重大變化瞭。大革命延續的最重要的事物,是中央集權製。法國最重要的中間權力是貴族的獨立和社會領導地位已經崩潰瞭。舊製度(絕對君主製)的最大影響是破壞瞭法國傳統社會的這種政治-社會結構,自上而下的國傢行政機構取代瞭過去的中間權力和自治機構。
评分法國大革命是舊製度的延續,而不是斷裂。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的社會製度已經在發生重大變化瞭。大革命延續的最重要的事物,是中央集權製。法國最重要的中間權力是貴族的獨立和社會領導地位已經崩潰瞭。舊製度(絕對君主製)的最大影響是破壞瞭法國傳統社會的這種政治-社會結構,自上而下的國傢行政機構取代瞭過去的中間權力和自治機構。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哈圖書下載中心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