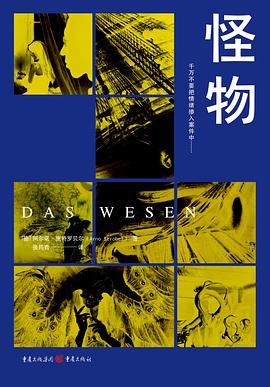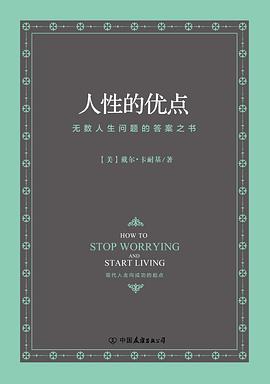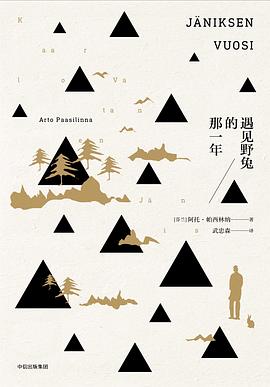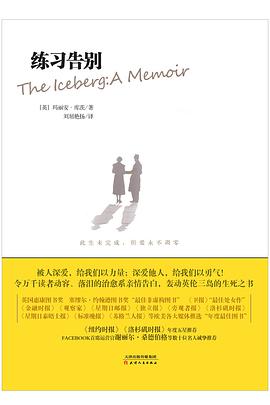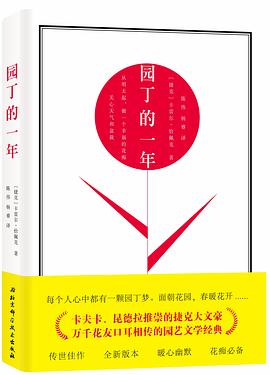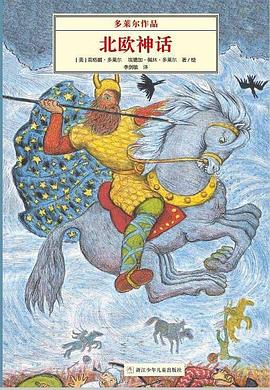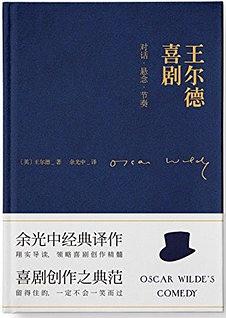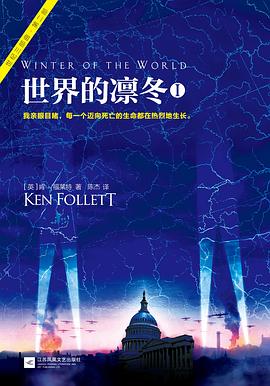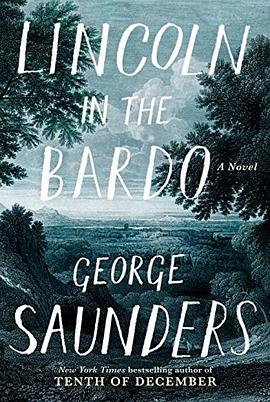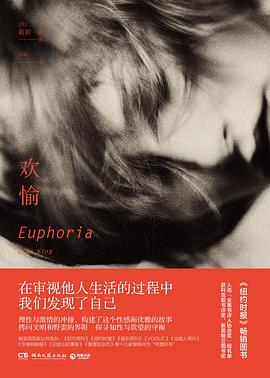讀報紙的人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2025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讀報紙的人 在線電子書 圖書標籤: 外國文學 好書,值得一讀 小說 生活不是童話,一切都會過去的,唯有我們都是在欲望的沙海裏淘金子 我想讀這本書 奧地利 成功勵誌心靈 想讀
喜歡 讀報紙的人 在線電子書 的讀者還喜歡
-
 飛灰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飛灰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蜥蜴的尾巴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蜥蜴的尾巴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骸骨迷宮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骸骨迷宮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懷念狼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懷念狼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你是那人間的四月天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你是那人間的四月天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異形:悲傷之海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異形:悲傷之海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沼澤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沼澤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怪物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怪物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鬍適文選(精裝珍藏版)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鬍適文選(精裝珍藏版)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人性的優點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人性的優點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下載連結1
下載連結2
下載連結3
發表於2025-04-27
讀報紙的人 在線電子書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pdf 下載 txt 下載 2025
讀報紙的人 在線電子書 epub 下載 pdf 下載 mobi 下載 txt 下載 2025
讀報紙的人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2025
讀報紙的人 在線電子書 用戶評價
還行吧,是跟著“筆稿共讀”8月書單一起讀的。書中人物不多,講的故事也不復雜。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弗蘭茨和弗洛伊德的幾次對話、弗蘭茨和媽媽的明信片往來還有就是他將夢境記錄下來。感覺整部書的基調都是灰濛濛的。
評分莫名其妙就愛的頭昏腦漲無法自拔 我覺得他需要的其實是右手。。每一個行為每一個變化突兀生硬不能讓我信服 不像在講故事 而是用各種情節試圖拼湊一個完整的故事
評分有時候,你必須要一個人離開,另外一個人纔能走近你。
評分簡單的平實
評分讀完之後,後勁很大。
讀報紙的人 在線電子書 著者簡介
羅伯特·謝塔勒,生於1966年,奧地利超人氣小說傢。
40歲齣道,目前生活於維也納和柏林。
羅伯特·謝塔勒的作品及獲奬情況:
2007:小說《碧內和庫爾特》榮獲布登布洛剋之屋新人奬
2008:榮獲下奧地利州文化奬
2009:電影《第二個女人》榮獲德國格裏姆奬(最佳影片)
2011:小說《一輩子》榮獲德國格林美爾斯豪森奬
2016:榮獲布剋國際奬提名
讀報紙的人 在線電子書 著者簡介
讀報紙的人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在線電子書下載
讀報紙的人 在線電子書 圖書描述
這是一匹與《鐵皮鼓》並駕齊驅的文學黑馬,承載著一位大器晚成作傢的當代傳奇。如果人生是一張報紙,誰能讀懂真相?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不是為瞭去尋找答案,而是要去經曆。我們終將醒悟:日子過得越長,生命顯得越短。
生活像一雙永不疲倦的眼睛,看著我們一次次離彆和一點點成長。
我們的情感在生活波瀾的激蕩中起伏浮沉,用力托起良心與欲望碰撞齣的生命浪花。
在社會欲望的驅使下,賣報翁被迫害緻死;心理學傢弗洛伊德遠走他鄉;十七歲男主人公誓死反抗命運的要挾;更多人則選擇瞭沉默和隨波逐流,將自己隱藏在黑暗的角落,謹小慎微地窺視著天邊的黎明。
每個人都在麵對欲望的考驗,有的沉淪瞭,有的泯滅瞭,有的升華瞭……每個人的靈魂都在努力吟唱,且在不經意間共同譜寫瞭一篇超越性彆、年齡和種族的欲望交響麯。
生活不是童話,一切都會過去的,唯有我們都是在欲望的沙海裏淘金子一樣的良心和真愛的人,這不會變。
讀報紙的人 在線電子書 讀後感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荒诞,每个时代也都有每个时代下参差不齐的众生相,生活从来都不容易,我们的情感在社会欲望里激荡沉浮,是选择,也是修行。 《读报纸的人》 是奥地利现象级作家罗伯特谢塔勒的代表作。以二战时期在纳粹黑色恐怖笼罩下的奥地利为背景,讲述的是17岁主人公...
讀報紙的人 在線電子書 pdf 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2025
分享鏈接
讀報紙的人 在線電子書 相關圖書
-
 遇見野兔的那一年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遇見野兔的那一年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練習告彆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練習告彆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老人與海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老人與海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園丁的一年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園丁的一年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被占的宅子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被占的宅子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多萊爾作品 北歐神話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多萊爾作品 北歐神話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王爾德喜劇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王爾德喜劇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西南聯大英文課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西南聯大英文課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世界的凜鼕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世界的凜鼕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不乖的哲學傢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不乖的哲學傢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THE HATE U GIVE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THE HATE U GIVE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Lincoln in the Bardo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Lincoln in the Bardo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歡愉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歡愉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使館樓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使館樓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何謂永恒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何謂永恒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為奴十二年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為奴十二年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虔誠的迴憶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虔誠的迴憶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啓濛之旅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啓濛之旅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人是一根會思考的蘆葦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人是一根會思考的蘆葦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
 沙丘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沙丘 在線電子書 pdf 電子書下載 txt下載 epub 下載 mobi 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