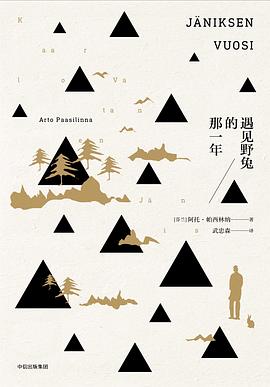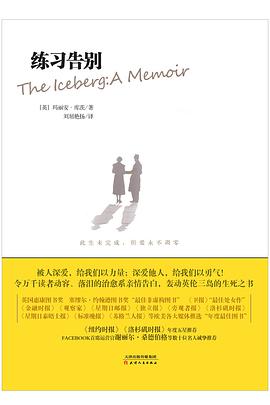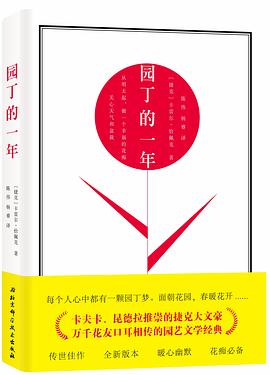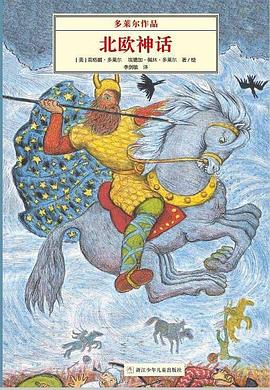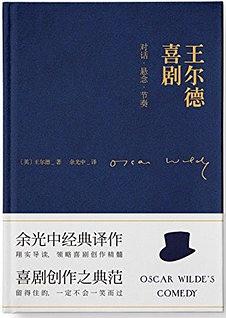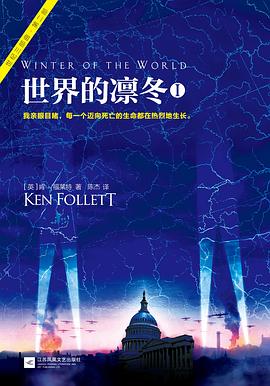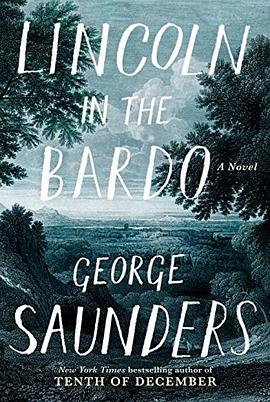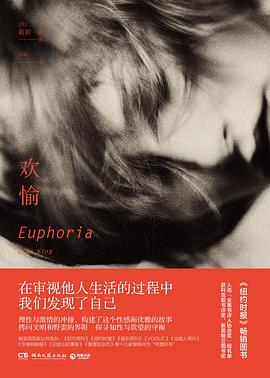具体描述
这是一匹与《铁皮鼓》并驾齐驱的文学黑马,承载着一位大器晚成作家的当代传奇。如果人生是一张报纸,谁能读懂真相?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去寻找答案,而是要去经历。我们终将醒悟:日子过得越长,生命显得越短。
生活像一双永不疲倦的眼睛,看着我们一次次离别和一点点成长。
我们的情感在生活波澜的激荡中起伏浮沉,用力托起良心与欲望碰撞出的生命浪花。
在社会欲望的驱使下,卖报翁被迫害致死;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远走他乡;十七岁男主人公誓死反抗命运的要挟;更多人则选择了沉默和随波逐流,将自己隐藏在黑暗的角落,谨小慎微地窥视着天边的黎明。
每个人都在面对欲望的考验,有的沉沦了,有的泯灭了,有的升华了……每个人的灵魂都在努力吟唱,且在不经意间共同谱写了一篇超越性别、年龄和种族的欲望交响曲。
生活不是童话,一切都会过去的,唯有我们都是在欲望的沙海里淘金子一样的良心和真爱的人,这不会变。
作者简介
罗伯特·谢塔勒,生于1966年,奥地利超人气小说家。
40岁出道,目前生活于维也纳和柏林。
罗伯特·谢塔勒的作品及获奖情况:
2007:小说《碧内和库尔特》荣获布登布洛克之屋新人奖
2008:荣获下奥地利州文化奖
2009:电影《第二个女人》荣获德国格里姆奖(最佳影片)
2011:小说《一辈子》荣获德国格林美尔斯豪森奖
2016:荣获布克国际奖提名
目录信息
1937年夏末的某个周日,一场异常猛烈的暴风雨从萨尔兹卡默古特穿梭而过。这场暴风雨,给弗兰茨·胡赫尔滴答流淌的平静生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当远处第一声雷鸣隆隆响起,弗兰茨跑进了一座小渔房,他和母亲就住在这里。
这里是阿特湖畔一个叫努斯多夫的小村庄。
他深深钻入被窝,在羽绒被温暖的庇护中听着外面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啸声。
暴风雨从四面八方摇撼着这间小屋。
房梁呻吟着,外面的百叶窗“砰砰”地被敲打着,屋顶上长满青苔的木瓦在狂风中颤动着。阵阵暴风裹着雨水噼里啪啦吹洒在窗户上,窗前几株已被折断的天竺葵淹没在花盆里。
在旧衣服箱子靠着的墙面上,挂着一尊铁制耶稣,摇摇欲坠,似乎任何一秒钟都有可能挣脱钉住它的钉子,从十字架上跳下来。
从不远处传来渔船撞击湖岸的声音。船只被汹涌波浪掀起,冲向湖边固定它们的桩子。
暴风雨终于平息下来,第一缕胆怯的阳光斑驳地洒在炭黑色的、被几辈人沉重的渔靴踏过的地板上,一直过渡到他的床上。
弗兰茨蜷缩成舒适的一团,便于脑袋从被窝里伸出来环顾四周。
小屋子还立在原地,耶稣像依旧被钉在十字架上,透过溅满水滴的窗户看去,窗外闪耀着唯一一瓣天竺葵花瓣,像一缕红色的、柔弱的希望之光。
弗兰茨慵懒地爬出被窝,走向小厨房,准备去煮一壶高脂牛奶咖啡。灶底的柴火依然是干燥的,烧起来非常快。他向明亮的火焰里凝视了一会儿。
突然一声响,门被打开了。
他的母亲站在低矮的门槛上。胡赫尔夫人在四十来岁人里算是一位苗条的女士了,看起来还是那么让人赏心悦目,尽管欠缺一些精力。她像大多数在邻近的盐场、牲口棚或者避暑客栈厨房工作的本地人一样,一生都在透支自己。
她仅仅是站在那里,一只手扶着门框柱子,微微低着头喘息。围裙紧贴在她身上,她的额头上散落着几缕凌乱的头发,鼻尖上落下几滴水珠。
在她身后的背景里,阴郁的沙夫山高高耸入灰暗的云天,天空已经在远处和近处又重新露出了些蓝色。
弗兰茨一直惦记着斜了的版刻圣母像,不知道是谁在很久以前把它钉在了努斯多夫小教堂的门框上,现在已经被岁月剥蚀得体无完肤。
“你淋湿了吗,妈妈?”他一边问着,一边用一根鲜绿的枝条来回拨弄灶火。他抬起了头,这时他才发现,她正在哭。
她的眼泪混杂着雨水一起落下,肩膀在颤抖着。
“发生了什么?”他把枝条塞进冒着浓烟的火中,吃惊地问道。
她没有回答,而是撑开了门,踉跄地走向他,然后停在了屋子的中间。有那么一瞬间,看起来她似乎在向四周寻找着什么,举起手做了一个无助的姿势,然后又滑落在膝前。
弗兰茨犹豫地往前迈了一步,把手放到她的头上,笨拙地抚摸着。
“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用沙哑的声音又问了一遍。他突然有一种不适的感觉,觉得自己有点儿傻。以前,情况刚好是相反的——他大哭大叫,母亲抚摸他。
轻抚着她的头发,他触摸到了一缕缕纤细的温柔,他能感受到她头皮下温暖的脉搏在轻微地跳动。
“他被淹死了。”她低声地说。
“谁?”
“布莱宁格。”
弗兰茨的手停了下来,静静地放了一会儿,然后收了回来。
她掠起自己额上散乱的发丝,站起身来,掀起围裙的一角擦了擦脸。
“看你把屋子弄得乌烟瘴气的!”她一边说,一边从灶台里拿出那根鲜绿的枝条拨了拨火。
阿洛伊斯·布莱宁格,总听人说他是萨尔兹卡默古特最有钱的男人。
事实上,他只排第三。
让他极度恼火的是,他总被人说成是爱慕虚荣的蠢脑瓜子,这让他声名狼藉。
他有几公顷的森林和牧场、一家锯木厂、一家造纸厂、四个水产企业、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湖域和水产养殖区、两条大型渡船、一条游船,以及据说是四千米之内的唯一一辆汽车——施泰尔-戴姆勒-普赫公司的豪华香槟红色汽车。
淫雨霏霏是萨尔兹卡默古特的特色。街道被持续的雨水冲刷,豪华香槟红色汽车只能被困在生锈的铁皮屋里无人问津。
阿洛伊斯·布莱宁格看不出已经有60岁了,他永远是一副生气勃勃的样子。他很爱自己,爱自己的故乡,爱美食,爱烈酒和漂亮女人。
不过,审美这个事是很主观的,所以是相对的。基本可以这么说,所有的女人他都爱,因为没有哪个女人他不觉得漂亮。
他和弗兰茨的母亲是在几年前一场盛大的打渔节上认识的。她站在一棵老菩提树下,穿着一身天蓝色的连衣裙。她的小腿是浅褐色的,光滑无瑕得像那辆施泰尔-戴姆勒-普赫香槟红色汽车的木质方向盘。
那天,他点了新鲜的煎鱼,一罐果汁,一瓶樱桃酒。他们在吃饭期间,还没有试图多看彼此一眼,可没过一会儿,他们就一起跳起了波尔卡舞,甚至是华尔兹,并在彼此耳边说着悄悄话。
然后,他们手挽手环绕着波光粼粼的湖散步,毫无防备地走进了铁皮屋,又去到那辆红色汽车的后座上。这辆车的后座足够宽敞,皮革柔软,减震器也上好了油……总而言之,那是一个圆满的夜晚。
从此之后,他们就一直在这个铁皮屋里见面。那是一次次短暂的火山喷发般的碰撞,不带任何的要求和期望。
对胡赫尔夫人来说,除了每次在车后座上大汗淋漓的畅快,还有另外一份愉悦:每个月底,努斯多夫的储蓄银行都会准时飘进一张金额不菲的支票。这定期的救济钱,让他们有能力从原来的旧渔房直接搬到海岸边,每天至少能吃上一顿热饭,每年还可以乘汽车去两次巴德伊舍[奥地利的一座温泉小镇,位于萨尔茨卡默古特地区中心的特劳恩河河畔。
],可以喝到海滨大道咖啡厅里的热巧克力,然后再去旁边的杂货店买几尺亚麻布做件新裙子。
阿洛伊斯·布莱宁格的慷慨之爱,也给胡赫尔夫人的儿子弗兰茨带来了好处。这让他不用像其他年轻小伙子一样,每天要在某个盐矿里或者粪堆中爬来爬去,挣点儿微薄的工资。他可以从早到晚在森林里闲逛,躺在木板小桥上晒肚皮,或者遭遇坏天气时,就待在被窝里沉溺于自己的想象和梦境。
可这些,在接下来的这件事发生之后,就都成了过去。
四十年如一日——除了极少被一些令人反感的事情打破,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锯木厂的火灾——周日上午,阿洛伊斯·布莱宁格都会坐在金色莱奥波德餐厅的固定餐桌边,为自己点一份煎鹿肉、紫甘蓝、面包丸子,以及八罐啤酒和四杯双燃烧酒,用他深沉微颤的低音穷尽词汇来表达对上奥地利发生的民族性事件的关怀。比如像星火一样在整个欧洲蔓延的布尔什维主义,变傻的犹太人,变得更傻的法国人,还有国际贸易为人们提供了最好的、无限的前途。
最后,当他伴着午餐时间的困意趔趄着从岸边小路往家走时,他的周围出奇地安静。看不见一只鸟儿,听不见一声虫鸣,连在餐馆成群绕着他汗津津的脖子飞来飞去的大苍蝇都消失了。
天空沉重地悬挂在湖上,水面如镜子一般躺在地上,船只一动不动。那一刻,就好像整个空气都凝结了,周围的世界也纹丝不动地被禁锢其中。
阿洛伊斯还在惦记着金色莱奥波德餐厅的碎猪肉冻,他本可以点这个的,而不是煎鹿肉。虽然喝下了那么多烧酒,鹿肉还是像块砖头一样堵在胃里。
他用衬衫袖子擦去了额头上的汗珠,看向铺开在他面前那丝绒般柔软而深蓝色的水面。然后,他脱掉了衣服,他想游泳了。
这个季节,湖水凉爽舒适。阿洛伊斯下水之后,平静地吸气,一头扎下,在水下神秘莫测的暗沉深处呼出。在他差不多到达湖心时,天空已经落下了第一滴雨,在他继续往前游了大约50米之后,已经是大雨倾盆。雨滴沉重地拍打着水面,打出均匀的“噼啪”声,如注的雨水好似一条条线,将黑色的天空与黑色的湖水紧紧相连,密不可分。
起风了,而且很快变成了风暴,浪尖被搅成了泡沫,一道闪电让湖水瞬间浸入虚幻的银光之中。雷声震耳欲聋,一声声巨响像是要让世界分崩离析一般。
阿洛伊斯突然大笑起来,用胳膊和腿疯狂地扑腾着水面,他快活地大喊着,他似乎从未觉得自己的生命如现在这样有活力。
水,在他周围翻滚,天空,在他头顶崩塌,他竟如此真实地活着。
· · · · · · (收起)
读后感
人言,战争,爱情,面包,理想。 日子过得越长,生命显得越短。 读这本书时,深深感受到被笼罩在阴影下的城市的感觉。 深重的雾气,笼罩在城市之间,笼罩着人们的心,双眼迷失了方向。 这时候,眼睛已经无法发挥他的能力了,唯一能辨别方向的是我们坚定跃动的心脏,是毅力与勇...
评分 评分“我们在几乎永恒的人生昏暗中四处摸索,只有足够幸运的人,才能偶尔看见一盏小灯燃起的光明。同时,只有拥有足够的勇气或毅力,或愚蠢,或最好是将这些全都混在一起之后,我们才能在某些地方留下自己的印迹。” 如果人生是一张报纸,谁能读懂真相?书封上这一句充满悬念的文案...
评分 评分用户评价
这本书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它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让我重新认识了“信息”。我们现在每天都被海量的信息所淹没,但有多少信息真正触及了我们的内心?又有多少信息能够引发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作者通过描绘那些认真阅读报纸的人,似乎在提醒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放慢脚步,去拥抱一种更具深度和韧性的阅读方式。我曾经以为,只要看得多,看得快,就能掌握这个世界,但《读报纸的人》让我意识到,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在和一群我从未谋面,却又无比熟悉的人进行心灵的对话。他们可能住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可能是任何一种职业,但他们在阅读报纸的那个瞬间,都展现出了某种共通的人性特质。我尤其欣赏作者在细节上的捕捉能力,比如,他会描述报纸的纸张质感,墨水的味道,甚至是风吹过报纸时发出的轻微沙沙声。这些细节虽然微不足道,却能够营造出一种非常真实的阅读氛围,让我仿佛身临其境,能够感受到那种纸质的温度和厚重感。
评分这本书,哦,简直是把我从日常的琐碎中彻底解放出来。我平时是个非常依赖惯性思维的人,每天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钟,准时起床,准时上班,准时吃饭,准时睡觉,好像生活的所有轨迹都已经被预设好,而我只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直到我偶然翻开《读报纸的人》,那种被卷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体验的感觉,我至今仍旧记忆犹新。它不像那些枯燥的理论书籍,也不是那种跌宕起伏、情节复杂的小说。它更像是一个温和的邀请,邀请我去观察,去思考,去重新认识那些我曾经习以为常,却又从未真正留意过的世界。 我最喜欢的是书中对“人”的描绘。作者似乎有一种神奇的笔触,能够捕捉到那些最细微、最容易被忽略的人类行为和情感。比如,他会细腻地描写一位老人在清晨的报摊前,戴着老花镜,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张报纸的每一个动作,那种专注,那种沉浸,仿佛整个世界都消失了,只剩下他和纸上的文字。又比如,他会捕捉到年轻人匆匆瞥过报纸标题时的那一丝不经意,或者是在咖啡馆里,一个人静静地读着报纸,偶尔露出的若有所思的表情。这些场景,看似平凡,却蕴含着深刻的洞察。我常常在读到这些片段时,会不自觉地停下来,回想自己读报纸的经历,那些碎片化的信息是如何在我脑海中拼凑出我对世界的认知,又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的思想。
评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它对“观察”的强调。作者就像一个孜孜不倦的观察者,他用敏锐的目光捕捉着生活中最细微的角落。他关注那些在报纸世界里穿梭的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的表情,他们的姿态,甚至他们手中的报纸被折叠的方式,都被赋予了生命和意义。我之前很少去留意身边的人,更不会去思考他们阅读报纸时的内心世界。但读完这本书,我开始尝试着去观察,去体会,发现原来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能隐藏着一个丰富而有趣的故事。 这种观察,也延伸到了我对信息本身的看法。我们习惯于接受信息,却很少去思考信息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是如何被呈现出来的。报纸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它背后有着采编、印刷、发行等一系列复杂的流程。而《读报纸的人》则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个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和劳动付出。我开始更加珍视每一份来之不易的信息,也更加懂得去辨别和分析,而不是全盘接受。
评分更让我着迷的是,这本书不仅仅是对“读报纸”这一行为的记录,它更像是一次对信息时代下个体存在的深刻反思。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被海量的信息所淹没,但有多少信息真正触及了我们的内心?又有多少信息能够引发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作者通过描绘那些认真阅读报纸的人,似乎在提醒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放慢脚步,去拥抱一种更具深度和韧性的阅读方式。我曾经以为,只要看得多,看得快,就能掌握这个世界,但《读报纸的人》让我意识到,质量比数量更重要。那些经过筛选、经过编辑的文字,以及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沉淀和思考,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我一直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信息的传递和分享来实现的。而报纸,作为一种传统的媒体形式,它承载的不仅仅是新闻,更是一种社会集体记忆的载体。书中那些关于报纸如何传递社会变迁、如何影响人们观念的描写,都让我对信息传播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我常常在想,我们现在通过各种社交媒体获取信息,虽然便捷,但也容易让我们陷入信息茧房,难以接触到多元化的观点。而报纸,尽管它有它的局限性,但它依然保持着一种相对客观和全面的视角,让读者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声音。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它让我看到了“阅读”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一直以为,阅读就是获取知识,就是增长见闻,但《读报纸的人》让我发现,阅读更是一种与自我对话,与世界连接的方式。那些读报纸的人,他们或许只是在消磨时间,或许只是在获取信息,但他们也在那个过程中,与自己的思想碰撞,与社会脉搏产生共鸣。我从中看到了阅读的温情,看到了阅读的陪伴,看到了阅读的沉淀。 我曾经有过一段时期,感觉自己被信息所淹没,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每天都是被动地接受各种碎片化的信息,感觉脑子越来越乱,思绪也越来越模糊。直到我读了《读报纸的人》,我才开始重新找回那种沉静下来的力量。作者用一种非常细腻和充满人文关怀的方式,描绘了那些认真阅读报纸的人,他们那种专注和投入,让我看到了阅读的另一种可能性。它不仅仅是获取信息,更是一种与自己内心对话,与世界建立连接的方式。
评分我必须说,这本书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动声色”。它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没有振聋发聩的论调,但它却能在不知不觉中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作者似乎对普通人的生活有着一种深切的理解和关怀,他用一种平静而温和的笔触,去描绘那些构成我们生活底色的平凡场景。我常常在阅读时,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觉得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经历,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肯定和映照。 书中对于“时间”的感知,也让我印象深刻。读报纸,本身就是一种与时间对抗的行为。在信息洪流中,报纸是少数能够保持一定“滞后性”的载体,它让人们有机会去回顾,去反思,而不是被当下瞬息万变的信息所裹挟。我曾经觉得,越快获取信息越好,但这本书让我认识到,有时候,慢下来,反而能看得更清楚。那种等待着下一期报纸出版的心情,那种在沉淀中思考的乐趣,是快餐式信息无法给予的。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动容的是,它让我看到了一种“生活态度”。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常常被各种“高效”、“便捷”所裹挟,仿佛停下脚步就意味着落后。但《读报纸的人》却展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那些在清晨的报摊前,耐心地翻阅报纸的人,他们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从容和淡定,让我觉得异常珍贵。这不仅仅是关于阅读,更是关于如何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和专注。 我曾几何时,也像书中的某些人物一样,会不经意间被报纸上的某个标题所吸引,然后会停下脚步,仔细阅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习惯似乎被各种推送和弹窗所取代。这本书的出现,让我重新审视了这种“慢阅读”的价值。它提醒我,在信息的海洋中,有时候,更需要的是一种沉淀和思考,而不是盲目的追逐和接受。我开始重新尝试着去拥抱那种需要时间和耐心的阅读方式,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收获,往往隐藏在那些不那么“快”的过程中。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释怀的是,它让我看到了“平凡”的力量。我们常常追求轰轰烈烈,追求与众不同,却忽略了那些构成我们生活底色的平凡瞬间。而《读报纸的人》则用一种充满温情和理解的笔触,描绘了那些在平凡生活中,依然保持着对世界好奇心的人们。他们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但他/她身上所展现出的那种专注、那种思考,都足以构成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一直在思考,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内心的独立和清醒。这本书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它让我看到,即使在信息被碎片化、被娱乐化的今天,依然有人愿意去认真阅读,去深入思考。这种对“深度”的坚守,让我觉得充满了希望。我开始尝试着去模仿书中的人物,放慢自己的节奏,去更深入地理解我所接触到的信息,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了解。这种转变,让我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和充实。
评分我一直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书,不是那些告诉你“应该怎么做”的书,而是那些能够引导你去“如何思考”的书。而《读报纸的人》,正是这样一本让我受益匪浅的书。它没有给我明确的答案,但它抛出了一系列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比如,在数字时代,纸质媒体的未来会怎样?我们与信息的互动方式,又将如何演变?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这本书引导我去思考这些问题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巨大的收获。 读这本书,也让我对“传统”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常常将“传统”与“落后”划等号,但《读报纸的人》却让我看到,即使是像报纸这样看似传统的载体,也依然蕴含着生命力,也依然能与现代社会产生深刻的连接。它不是在怀旧,也不是在颂扬过去,而是在探寻传统在当下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这种视角,让我对很多被我们遗忘或忽略的事物,重新燃起了好奇心。
评分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在和一群我从未谋面,却又无比熟悉的人进行心灵的对话。他们可能住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可能是任何一种职业,但他们在阅读报纸的那个瞬间,都展现出了某种共通的人性特质。我尤其欣赏作者在细节上的捕捉能力,比如,他会描述报纸的纸张质感,墨水的味道,甚至是风吹过报纸时发出的轻微沙沙声。这些细节虽然微不足道,却能够营造出一种非常真实的阅读氛围,让我仿佛身临其境,能够感受到那种纸质的温度和厚重感。 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我自己的阅读习惯。我以前习惯于碎片化地阅读,看到一个感兴趣的新闻标题,就点进去看一眼,然后就匆匆划过,很少会深入去思考。但《读报纸的人》提醒我,真正的阅读,是一种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的过程。它需要我们去理解背景,去分析观点,去形成自己的判断。我开始尝试着放慢节奏,重新拿起纸质的报纸,去感受那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我发现,当我不被各种推送信息打扰时,我的思绪会更加清晰,也更能专注于我正在阅读的内容。
评分有人为了生存,有人为了生活,都在奋力向上爬。一切都会过去的,唯有爱不变!
评分很久没有遇到情节这么紧凑的书
评分2017年9月23日读,2017-256。
评分你们怎么就那么好意思腆着脸给打五颗星啊?也就是个七八流小说的水平吧。
评分莫名其妙就爱的头昏脑涨无法自拔 我觉得他需要的其实是右手。。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变化突兀生硬不能让我信服 不像在讲故事 而是用各种情节试图拼凑一个完整的故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wenda123.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目录大全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