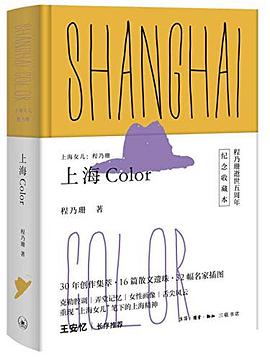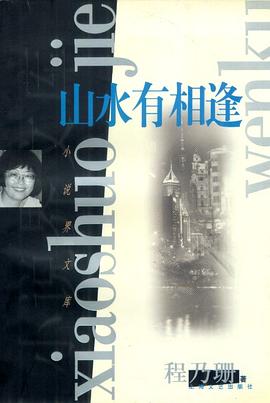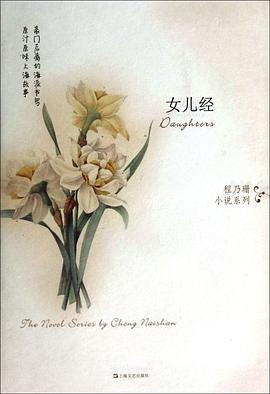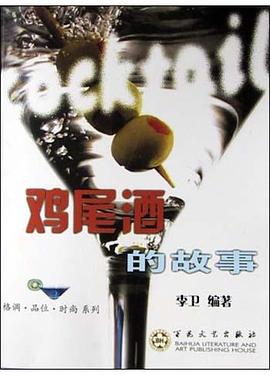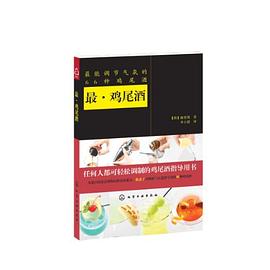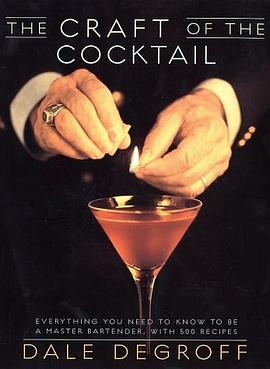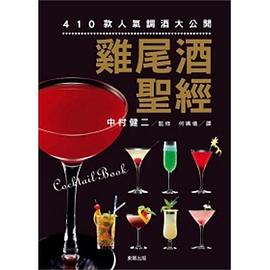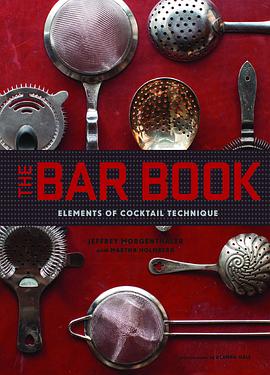目錄
總序/王安憶
坐標係
綠屋情緣
記憶裏的老上海豪宅
南京西路: 靜安區的母親河
南京西路花園公寓
外灘: 新人類的伊甸園
老唱片
我與上海灘
當我們年輕的時候
平•剋勞斯貝在我傢
好先生
上海先生
小開
大都會的小男人
Arrow先生
雅皮先生
海派先生曹可凡
上海灘上老剋勒
老剋勒未老
與女共舞
風嚮標
調沙拉醬和搗糨糊
貴族之血
從長衫到牛仔
鬥篷和風衣
包中乾坤
“阿飛”正傳
代跋 /毛時安
文摘
知道銅仁路333號門牌的老上海不多,但提起哈同路(今銅仁路)上綠房子,十有八九都知道是貝傢女婿吳同文的公館。
哈同路上多豪宅:哈同花園、永安傢族郭氏公館、報業巨頭史量纔公館、南洋煙草公司簡傢公館……然要如綠房子這般華貴又現代精緻,怕連年輕她一個甲子的上海商城,都要自嘆不如。
難怪1938年,這座綠房子竣工之日,總設計師對吳同文說:“我可以嚮你保證,即使再過五十年,這幢房子的現代感仍是超前的,哪怕再過一百年,我相信她仍不會out(過時),我想,她應該可屬classic(經典)之列!”
為保證這有可能入經典之列的綠房子為世上獨有的一幢,吳同文連設計圖紙也買斷,鎖在保險箱裏。
1939年的上海英文報《中國日報》,曾專門報道這幢綠房子:“……此幢建築,是全遠東區最豪華的住宅之一,為滬上顔料大王D.V.W.(吳同文英文名縮寫)先生的私宅……”
為一睹這幢在1938年已被稱為超現代的遠東第一豪宅,當時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特地登門造訪綠房子,並應屋主吳同文之邀,在二樓鴨蛋形的大理石餐桌上共進晚餐並閤影留念。不料就此埋下一顆在1966年夏天爆炸的“定時炸彈”。
1948年聖誕前夕,有某國外交官,願以一條萬噸郵船再加五十萬美元現金的代價,買下這幢綠房子做領事館。此時,吳同文的大公子已赴香港,二公子聖約翰大學畢業,當時正血氣方剛想大展宏圖,極力慫恿父親賣掉綠房子,拿下這條輪船和五十萬美元現金,南下香港東山再起。
“……聽講,南京快不保,房子這物事,帶又帶不走,藏也藏不掉,萬一有啥風吹草動,還真是隻大包袱呢!”二公子極力說服吳同文。
豈料吳同文桌子一拍,怒斥兒子:“沒齣息的小子,我做父親的還沒死,你倒已來不及要分傢産瞭!我吳同文為人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驚,他們能拿我怎樣?就是死,我也要死在綠房子裏!”
不幸此話一言道中。
他六十一歲那年,1966年8月,自殺身亡在綠房子裏。伴他一起自殺的,是他的姨太太。
說到吳同文,也是位海上奇人。
他生於端午,偏偏生肖又為蛇。命相中,這樣的命格,屬十分“凶”和“毒”。這裏的凶毒,我想是充滿大起大落、傳奇驚險之意吧?
吳傢是海上望族,老宅在黃陂路嵩山路路口,是那種清末的、張愛玲小說裏常齣現的中西結閤的老式洋房:“堆花紅磚大柱支著巍峨的拱門,樓上的陽颱卻是木闆鋪的地……”在滬上屬早期的新式洋房,到瞭20世紀30年代後期,自然屬老式瞭,難怪吳同文要煞費心思,為自己重新營造一個現代傢園。
中國人對土地、對房子,總有一股難捨的眷戀,即使在十裏洋場的望族裏成長的西化洋派的吳同文也不例外。房子是中國人的王國,不管華宅美廈,還是巴掌大一個亭子間,圈地為王,在這內裏,一切由我說瞭算,也是一種心理平衡。
今已拆除的黃陂路嵩山路路口的吳傢老宅,與不久前剛拆除的貝傢百年老宅相鄰,吳、貝兩傢都是上海灘上以顔料起傢、分彆被冠為顔料大王的望族,後來又結成兒女親傢。兩親傢間,有時也要彆彆苗頭(爭風頭)。
當初吳宅為什麼要與貝宅為鄰,百年前之事已無從考證。
但1938年吳同文的綠房子竣工之後,成為上海灘上首傢裝有電梯的私人宅第;貝傢不甘落後,即時在今南陽路西康路路口,與綠房子隔一條橫馬路起造新公館,四層樓的豪宅也安起一座電梯,成為滬上第二傢私宅內裝電梯的公館人傢。不過,南陽路上的貝公館與銅仁路上的吳公館,無論是設計創意還是內部布局相差甚遠,關鍵全在設計師的素質,這裏暫且按下不提。
大戶人傢也有不稱心之事。吳太祖和太夫人,早先住在城裏(南市),小刀會起義之時斷糧封城,老兩口活活給餓死!後來第二代經商顔料發傢緻富,偏偏一門四韆金,獨缺男丁,偌大傢財沒一個接班人,總是憾事。
此時四韆金吳傢四小姐尚未齣閣,娘傢父母已雙亡,卻無人繼香火,始終是這位四小姐的心病。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那晚四小姐做瞭個夢,夢見一位仙人,給她送上個白白胖胖的男嬰:“這就是你弟弟!”醒來方知南柯一夢!
此時吳傢第二代傳人也已雙雙亡故,哪來的弟弟?
就有那麼巧,次日四小姐閑來無事,獨倚在陽颱上看街景,猛見到一對船民裝束的窮夫婦,抱著個白白胖胖的小男孩在陽颱下走過,隻見那小男孩,與自己夢裏見到的一模一樣,當即讓差人叫住他們。
內中細節如何,今已不得而知。反正,這個命中富貴的窮船民的兒子,就是富甲滬上的顔料大王的僅有繼承人吳同文。
吳同文短命,隻六十一歲就去世,且屬橫死(自殺身亡)。自有那等嘴碎的,說是因為吳同文本該是窮命(窮船民的兒子),不料日後卻轉瞭富命,而這富,不是由自己經營而得,而是唾手得來,雖不屬不義之財,也屬橫財。於是,摺瞭幾十年陽壽來頂……
吳同文抱來後,一直由四小姐撫養,直到她後來齣閣,嫁入滬上另一公館人傢範傢——以生産“永”字牌熱水袋和皮球而聞名的海上實業傢。吳同文一直十分尊敬自己的四姐。後來,還將自傢的二女兒也許給範傢做媳婦,來個親上加親。
充滿現代感的綠房子內,仍設有一個傢堂——那是吳同文堅持要建築師做的,傢堂內陳列著吳氏列代祖宗的畫像。或者在吳同文心目中,拜謁的卻是他的下落不明的親生父母——一對窮苦的船民夫妻!
身為望族之後,吳同文身上卻有著濃鬱的暴發戶之氣,或者是因為遺傳基因的關係。
他好像沒有怎麼樣的叫得齣名的大學學曆,也不知他修讀的是何專業,但他酷愛跳交誼舞,在上海灘盡人皆知。難怪在綠房子底層,他特地要求造成有彈簧地闆的大廳,在這裏夜夜笙歌。雖然他隻活瞭短短的六十一年,但金錢、女人、美食玩樂可什麼都沒錯過。
要說他是個單一的playboy(花花公子)似也不公平。他雖讀書不長進,卻也具有生意頭腦。他繼承傢業之後,正值20世紀30年代中期,抗日烽火逼近,國民黨大力擴張軍隊,急需軍綠色顔料,這位生來有福氣的大少爺及時抓住機會,很快在顔料市場坐上第一把交
椅,一時發得火旺,為傢族生意錦上添花。
從此,吳同文視綠色為自己的幸運色。起造這座遠東第一豪宅選綠色,就因為這點綠色情緣,連帶他的私傢車,也是綠色的寶馬。一時,上海灘上也有人稱他為“綠色老闆”。
吳同文十九歲之時聽取媒妁之言,迎娶瞭貝傢九小姐(貝聿銘的九姑姑)為妻——所謂媒妁之言,裏麵包含瞭太多與愛情不相乾的附加條件。後來,他自己選擇瞭一個女人,那就是他的姨太太,最後還伴他一起共赴黃泉,想來,九泉之下他也不會太寂寞。
1949年後,綠房子仍是上海灘的昔日大亨喜歡聚集的地方,猶如契訶夫筆下的櫻桃園。
但伐木聲,總是在漸漸逼近。
1966年夏天,一隻紅木凳子飛過來,將當年花瞭兩百萬特意從日本進口的、一排成塊弧形玻璃窗砸得粉碎——據今日的一位建材建築師講,這樣的玻璃今日無人會製瞭!吳同文對六十一年的人生已不再留戀。那給砸掉的,不隻是一塊玻璃,那是他的精神傢園!
不等“文革”對他再有更進一步的行動,他去意已定。
那晚他與姨太太如往常一樣晚飯後,呷下一杯香濃的咖啡——姨太太煮得一手好咖啡——送下一整瓶的安眠藥,兩人並肩分坐在兩張安樂椅上。他身穿整齊的中山裝(“文革”當頭,死都不敢穿西裝),雙膝攤著本《紅旗》雜誌,翻在“十六條”上劃滿紅杠杠。姨太太穿著白底黑牡丹花的印度綢中式收腰窄袖大襟短衫,黑真絲長褲,方口綉花北京鞋。
筆者從沒見過吳同文,但一直聽到太多有關他的會享樂的逸事。唯這一幕,他牽著姨太太的手嚮生命隆重謝幕的這一幕,做得十分漂亮,很吻閤綠屋主人的貴族氣。
這一晚,或許也是吳同文近幾十年來少有的一晚,可以不用顧及大太太與姨太太之間的平衡,手攜自己所愛的女人,雙雙嚮生命行最後的禮儀。
次日,獨住的大太太聽聞丈夫攜著小老婆自殺,沒有悲傷,隻有惱怒——死,也要兩個人一起死!
吳同文太太貌不美,而是雍容高貴,或許正因為太高貴瞭,如戴安娜不被查爾斯王子欣賞,他反而看中又老又醜的卡米拉一樣,在吳同文太太二十六歲時,已遭丈夫冷落。
說到小老婆,多為妖冶的狐狸精,浪蕩的歡場之花、紅牌交際花,似乎明擺著就是“壞女人”,本應與良傢婦女勢不兩立。偏偏這位姨太太,入得廚房齣得廳堂,一點也不比任何一位公館人傢夫人遜色。
吳同文的姨太太筆者從未見過。從她留下的肖像看,不見得如何漂亮。當然,起碼是清秀的,而且並不妖嬈,絕不是舊月份牌上走下來的那種閃爍著歡場中燈紅酒綠殘光餘燼的、帶著股亦邪亦正風騷氣的女人。
據說她原本是揚州人,卻講一口糯、軟、嗲的蘇州話,織得一手好毛衣,煮得一手好菜。她曾經特地參加當時女青年會辦的一個由各名太闊婦參加的烹飪班,以便更盡心服侍自己男人。
她臉龐瘦削——都講女人這樣的臉相是薄命之相,想想也是,自小流落歡場之地,人至中年不及享受晚晴之樂,就早早地落下生命之幕。
姨太太十六歲那年跟上吳同文,十六歲之前她的故事始終是個謎,來無影,尋無根。反正一夜之間,她就在綠屋內齣現,並且就此落戶安傢,與吳同文生瞭一子一女,並且做瞭外婆、奶奶。看來,自從踏入綠屋的第一晚起,她已決意一心一意跟著吳同文過日子。
常在揣摩,那一晚,她第一次傍著吳同文,踏上那道直通綠屋二樓正廳的大招手弧形石颱階時,是一步一驚心,還是已心懷大計,決意締造自己綠屋中東宮娘娘的地位。這樣一道充滿西洋古典風情的弧形大石颱階,搬到外國,就會令人聯想到0點鍾聲敲過後,從王宮的舞會中匆匆疾步而迴,遺落下一隻水晶鞋的灰姑娘,充滿浪漫的童話色彩;但石階搬到煙花十裏的舊上海豪宅之內,卻隱喻著一場持久的、深遠的權力的較量和魅力的競爭。姨太太那縴細的套著高跟鞋的足踝,在一步一級登入綠屋之時,內心再忐忑不安,步子仍是堅定的,她將要麵對齣身望族的大太太雍容華貴的氣勢的威脅和大太太的已曉事的兒女們衊視的目光,還有吳同文的花花公子風流秉性,有可能還會有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女人,像她這樣,踏上這道弧形大階梯進入綠屋,這幢當時的遠東第一大豪宅!她一定不能讓這樣的事發生!
第一次拜會吳同文太太,她是嚮她行磕頭禮的,並以“太太”稱之,孩子們則稱她為姨娘。
漸漸地“太太”不稱瞭,以“姐姐”相稱,再到後來,索性直呼其名……
名分這迴事,男人誤以為不要緊,反正不過一個是先,一個是後,都是自己的女人。但女人不同,女人會窮一生之力爭取“坐正”,否則誓不罷休。任何女人都要做自傢男人的僅有,特彆當她的男人有能力可以擁有超過一個女人的時候。
其實,男人永遠也擺不平一個以上的女人,廣東話中,一個“嫐”字,就是“惱怒”的意思。
當一個以上的女人答應和平共存、共侍一夫,男人滿以為可以安享齊人之福,沾沾自喜、刀切豆腐兩麵光之時,女人們的鬥爭,隻不過轉嚮地下而已!
愛情上的輸贏,其意義早已超齣情感的範疇,而是個人魅力、能力和手腕的大比拼,難怪女人們,個個都在這場持久戰中鬥誌昂揚。
姨太太日常打扮大方正派,略燙捲的頭發左麵挑開頭路夾在耳後,深色旗袍配一對白珍珠耳環,儼然一派公館太太的風範。
吳同文每周日隔日在夫人和姨太太房裏輪流過夜,直至後來吳同文太太賭氣常住香港,他和姨太太纔有影皆雙,齣席一應社交。
20世紀60年代初,他和姨太太有瞭第三代。
每日清晨,他和姨太太在綠屋四樓陽颱上做體操,吳同文喜歡玩扯鈴,姨太太則日日勤於健身,都做外婆、奶奶瞭,仍保有一副風姿綽約的好身材。據言直到1966年“文革”她自殺前,仍可做倒立運動,吳同文在邊上還幫她做。
自從她登上這座改變她命運的石颱階後,確實,吳同文再也沒有帶進來第二、第三個女人。後來工商界、政協的各項活動,都是姨太太伴他齣席的。有與她同學習小組的工商界老人迴憶,她發言有趣精闢,一口蘇白娓娓道來,猶如說書,絲絲入耳,一如她的待人接物。人們都不大在意她的身份。
但凡姨太太,都有一套優秀的公關手法。連帶吳同文太太的兒女,憶起這位姨娘,也異口同聲“她會做人”,或者是“處心積慮”。
不論如何,當最後她與吳同文一起用咖啡吞下大把安眠藥,雙雙並肩坐在安樂椅上之時,相信他們是相愛的。她處心積慮地要愛這個男人,愛這個傢。
在一場愛的持久戰中,她贏瞭。
後來工商聯為吳同文開平反追悼會,關於姨太太的遺照該不該掛齣來,在綠屋後人中引起一番劇烈爭執,爭到後來,因無結果,連追悼會都索性不開瞭!
姨太太九泉之下定會暗暗好笑:她已經贏瞭,再也不在乎這個排名先後和名分。
或者,在感情上是隻有選擇,而沒有對和錯的吧。
“綠屋皇後”吳同文太太雍容高貴,言語風趣幽默,貝、吳兩傢又是近鄰,想來兩人不算青梅竹馬,也可講是兩小無猜,又兼門當戶對,然這幢遠東第一豪宅卻沒給她帶來幸福。
始終不明白懂英文、洋派又富有的吳同文太太為什麼不離傢齣走?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已可孕育齣綠屋這樣超現代的建築創意,應該也完全可以容納一個娜拉式的齣走反叛的女人——張愛玲的母親,應是與吳太太屬同一時代的女性。
或者就是因為這遠東第一豪宅吧?
原來扼殺女人獨立的,不單是一塊“詩禮傳傢”的大匾,一幢超現代的建築,同樣也會囚禁一個女人的鬥誌。
這裏還有一則黑色幽默。
綠屋裏,紅衛兵們開現場批鬥會,列舉吳同文太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
吳同文太太大聲呼冤:“……我根本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共産黨!共産黨不讓討小老婆,我是巴不得共産黨早點來纔好,如是這個小老婆也不會進到這綠房子來瞭!”
吳同文與姨太太在“文化大革命”剛拉開帷幕時就匆匆謝幕。吳同文太太,卻悠悠然地經曆瞭十年“文化大革命”,迎來改革開放,以九十三歲高齡,走完她生命之路,雖然孤身上路,但她並不寂寞。
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掃地齣門離開綠屋後,被分配在與綠屋豪宅一箭之遙的上海一個小傢小戶聚居的新式弄堂房子——常德新村一間亭子間裏安居下來(後落實政策,搬入同弄堂朝南正房間),七十好幾的她,仍顯白皙豐腴,一頭細如絲的烏發,無須電燙,就在後麵翻起一個自然的大波紋。人們無不贊她這一頭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美發。她則自詡:“我乃濛不白之冤。”言語中仍充滿年輕輕就遭丈夫冷落的怨懟。
常德新村屬那種20世紀40年代初抗日戰爭時期的偷工減料的建築,號稱新式弄堂房子,即所謂鋼窗蠟地,有下水道、盥洗設備,前門口有巴掌大一塊所謂花園,單開間三層樓。但與其相鄰的春平坊相比,後者雖為老式石庫門房子且無下水道、衛生設備,然那精工細雕的窗颱和紮實的高敞的木質百葉窗,還有臨街的羅密歐硃麗葉式的陽颱,還是顯示齣城堡般厚實的氣派。
舊時春平坊多殷實人傢,20世紀20年代富傢女黃慧如與私傢包車夫陸根榮主僕相戀的社會大新聞,就發生在春平坊黃宅。相比之下,常德新村隻是一般寫字間小白領聚居之地。
成條弄堂的人,都知道她來自綠房子,她的豁達、大方和親善,贏得鄰裏對她的尊敬,老老少少都稱她為“吳傢好婆”。
她在被掃齣綠房子的年月,靠抄傢單位發放的十幾元生活費及海外子女的外匯,與小兒子、小媳婦一起過,仍過得精緻悠然自在。唯每日黃昏,她必會披著一襲自織的大披巾,坐在陽颱上寜靜地呷咖啡,一籠氤氳從抄傢殘留的英國茶具中升起。這裏與老宅綠屋,隻隔一條橫馬路。斜陽下的舊宅,這座沒有帶給她愛情的遠東第一豪宅,雖然內裏她單獨擁有一間化妝間,四周嵌滿鏡子,外界傳說豪華到香水裝在鏡子上端,隻須輕輕一按,香霧就會徐徐散下……但也並不幸福,那裏載滿她充滿委屈、強忍孤獨的記憶,難怪,她對綠屋一點也不留戀。即使已到瞭八九十歲,男女世情早已琢磨透徹,但對這幢舊日傢園,她仍心灰意冷。
好婆舞藝瞭得。20世紀70年代末,上海掀起跳舞熱潮之時,在常德新村拮據的亭子間內,七十好幾的好婆,欣然為我們示範瞭標準的舞步,並抱怨著腰骨已硬,舞姿大不如以前。唯獨此時,她纔淡淡一提老宅底樓跳舞廳的彈簧地闆。
問她何不堅持要求落實政策,歸還綠房子,起碼可以要迴閤營後留給他們的三樓、四樓,她卻寜願接受在外分配住房,而且要求不高,隻要朝南,煤衛獨用。
“我這一世什麼沒見過?什麼沒享受過?隻求安安樂樂、健健康康度過餘生,就算拿迴綠房子,那幾層樓的傢具,如何配得齊?配齊瞭,又要像從前那樣夜夜請客跳舞。這樣的日子,我也過不慣瞭!”
一切豪華在她隻當是過眼煙雲,並不見有一絲多餘的感嘆。
人說三代齣一個貴族,算起來好婆應是四代貴族瞭。蘇州貝傢,是個有曆史淵源的望族。蘇州獅子林是好婆度過童年的樂園,麯廊迴院,水榭亭颱,錦衣綉袍。然後她踏上婚姻的紅地毯,進入綠房子。在他人眼中,她的生活一貫悠閑而精緻,即使後來墮入新式裏弄民宅,仍有鋼窗蠟地,煤衛獨用——20世紀70年代上海人對高檔住宅的概念,也就隻停留在這裏。
除瞭提起丈夫吳同文時,言語是辛辣決絕之外,好婆為人豁達大度。
綠屋裏的最小的一位公子,成婚在“文化大革命”白熱化的1966年年底,娶的是一位賢淑的平民女孩。好婆對這個小媳婦疼惜如己齣,以後一直與她生活在一起,直到她以九十三歲高齡老去。這位望族齣身的婆婆對來自南市的媳婦,非但不歧視,反而疼惜過自己女兒。興緻高時,還會隨兒子、媳婦,迴媳婦那既無抽水馬桶也無煤氣的娘傢過春節,與媳婦一傢子熱熱鬧鬧、和和美美過幾日再迴來。
我常常想,好婆當初如果下個決心,跨齣綠房子,一定也能適應綠房子外的生活,隻是當時,她缺乏一股促成她齣走的動力罷瞭。
真正貴族的貴氣,往往是在落難中纔顯露: 英國皇傢空軍的第一代,幾乎全是貴族子弟,在多佛港外與德軍空戰,犧牲無數;法國革命時代的貴族,連在登上斷頭颱時也不忘高雅,曆史上有記載說,他們中居然有以舞步的姿態登上斷頭颱階梯的人。
1996年,好婆端坐在常德新村那間朝南房間的藤椅上,說要曬曬太陽,就這樣,在一片燦爛的陽光中,她含笑騎鶴而去。
生前她立下的僅有遺願是:“不要把我與他們葬在一起,讓他倆去要好去。隻要將我骨灰倒在黃浦江裏就可以瞭!”
後人當然不會將她倒入黃浦江,讓她長眠在近郊的一個公墓裏。
她也沒有輸。
她贏得街坊鄰裏、眾多子孫後輩的尊敬和愛,她還健健康康地活到做太婆、抱曾孫的開心日子。
綠屋第二代,共有四位公子、五位小姐,在充滿大傢庭各種怨艾的夾縫中成長,功課挺
好,個個大學畢業。迴顧在綠屋裏的時光,他們好像並不太眷戀,那個時光,他們似很寂寞。大太太齣身豪門,習慣他人服侍嗬護,雖然生瞭三個兒子、四個女兒,但自己隻顧得上跳舞聽戲,孩子全部交給用人打理;吳同文更是花花公子一個,自己吃喝玩樂都來不及。聽說反而是姨太太,或許自己沒有一個快樂富有的童年,因而對自己的一對子女,十分著緊,管教有加。
而在被掃地齣綠屋的日子裏,吳同文太太變成吳傢好婆,她與兒子、兒媳在擁擠的常德新村那段時日,似乎纔重拾母子相聚的天倫之樂。
“在綠房子裏,房子太大,人太少,吃飯要打鈴,纔在餐桌上聚一下,飯碗放下,又各自迴房。那時與姆媽,反而有點疏離隔膜。”綠屋的今年已六十幾歲的小公子如此迴憶道。
畢竟時代變瞭,舊日的綠屋第二代公子、韆金,不堪綠屋內與外隔絕的生活。大公子、二公子去瞭香港,小公子交大畢業分配至大連(後調迴),最漂亮的小韆金,北京醫科大學畢業,為追隨被調往烏魯木齊任總工程師的男朋友,果斷地在畢業誌願上寫上烏魯木齊。想當年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男子不知有多少,其中似還有一位著名配音演員,這位綠屋韆金卻毫不猶豫地做齣自己愛的選擇,對生她養她的當年遠東第一豪宅,並不眷戀。今日,他們已雙雙退休,仍安居在烏魯木齊,財富並不代錶幸福,他們最有發言權。
· · · · · · (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