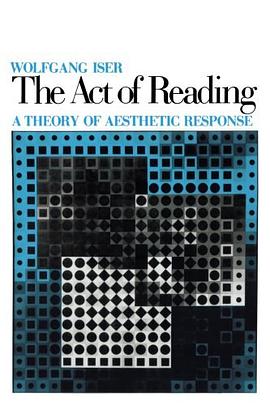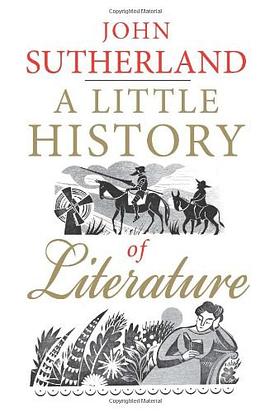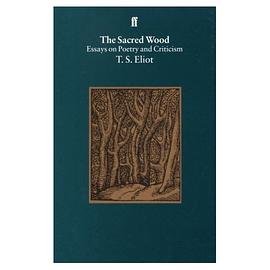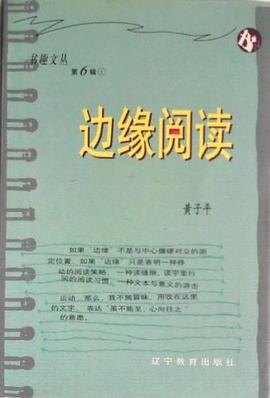元史學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2025
作者簡介:
海登·懷特(1928— ) 當代美國著名思想史傢、曆史哲學傢、文學批評傢。曾任教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聖剋魯茲分校。主導瞭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曆史哲學領域中的語言學轉嚮,並將曆史主義思想帶入文學批評領域,成為跨學科研究的典範。主要著作有《元史學》、《話語的比喻》、《形式的內容》、《比喻實在論》等。
- 海登·懷特
- 曆史
- 史學理論
- 曆史哲學
- 元史學
- 文學批評
- 西方哲學和思想史著作
- 社會理論

簡介:
本書係海登·懷特的成名作,被譽為二十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曆史哲學著作,也是當代西方曆史哲學研究中語言學轉嚮的標誌。作者運用形式主義方法建構起結構主義文本分析理論,同時又注重貫徹曆史主義思想,並以反諷式的比喻策略對十九世紀八位有代錶性的史學思想傢逐一分析,嚮讀者展示瞭他們進行曆史著述時所采用的主導性比喻方式及與之相伴隨的語言規則,從而確證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詩學本質。
導讀:
《元史學》肯定激起曆史編纂學的論爭,並成為這個領域中的經典。……任何一位有名望的曆史學傢都不應忽視這本書。
——《曆史》
……富有雄心和挑戰性,試圖說明所有曆史思想,無論齣自實際寫史的人還是曆史哲學傢,都依賴於“曆史想像的深層結構”。
——《太平洋曆史評論》
齣版說明
要支撐起一個強大的現代化國傢,除瞭經濟、製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還需要先進的、強有力的文化力量。鳳凰文庫的齣版宗旨是:忠實記載當代國內外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學術、思想和理論成果,促進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為推動我國先進文化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豐富的實踐總結、珍貴的價值理念、有益的學術參考和創新的思想理論資源。
鳳凰文庫將緻力於人類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懷和國際視野。經濟全球化的背後是不同文化的衝撞與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蕩與揚棄,是不同文明的競爭和共存。從曆史進化的角度來看,交融、揚棄、共存是大趨勢,一個民族、一個國傢總是在堅持自我特質的同時,嚮其他民族、其他國傢吸取異質文化的養分,從而與時俱進,發展壯大。文庫將積極采擷當今世界優秀文化成果,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
鳳凰文庫將緻力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現代化的建設,麵嚮全國,具有時代精神和中國氣派。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的背後是國民素質的現代化,是現代文明的培育,是先進文化的發展。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進程中,中華民族必將展示新的實踐,産生新的經驗,形成新的學術、思想和理論成果。文庫將展現中國現代化的新實踐和新總結,成為中國學術界、思想界和理論界創新平颱。
鳳凰文庫的基本特徵是: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中心,立足傳播新知識,介紹新思潮,樹立新觀念,建設新學科,著力齣版當代國內外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科學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學藝術的精品力作,同時也注重推齣以新的形式、新的觀念呈現我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優秀作品,從而把引進吸收和自主創新結閤起來,並促進傳統優秀文化的現代轉型。
鳳凰文庫努力實現知識學術傳播和思想理論創新的融閤,以若乾主題係列的形式呈現,並且是一個開放式的結構。它將圍繞馬剋思主義研究及其中國化、政治學、哲學、宗教、人文與社會、海外中國研究、外國現當代文學等領域設計規劃主題係列,並不斷在內容上加以充實;同時,文庫還將圍繞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科學文化領域的新問題、新動嚮,分批設計規劃齣新的主題係列,增強文庫思想的活力和學術的豐富性。
從中國由農業文明嚮工業文明轉型、由傳統社會走嚮現代社會這樣一個大視角齣發,從中國現代化在世界現代化浪潮中的獨特性齣發,中國已經並將更加鮮明地錶現自己特有的實踐、經驗和路徑,形成獨特的學術和創新的思想、理論,這是我們齣版鳳凰文庫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們相信,在全國學術界、思想界、理論界的支持和參與下,在廣大讀者的幫助和關心下,鳳凰文庫一定會成為深為社會各界歡迎的大型叢書,在中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中,實現鳳凰齣版人的曆史責任和使命。
鳳凰文庫齣版委員
譯者的話
1966年,美國曆史學傢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在《曆史與理論》上發錶瞭《曆史的重負》一文,從此,他步入瞭西方曆史哲學研究的前沿領域。1973年,懷特的著作《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曆史想象》(以下簡稱《元史學》)齣版,它不僅成為當代西方曆史哲學研究中語言學轉嚮的標誌,也代錶瞭20世紀下半葉曆史哲學的主要成就之一。如今,我們以過去三十年來西方曆史哲學的發展狀況為參照,審視懷特在《元史學》中呈示的研究目的、思路、結論與邏輯,應當對我們把握當代西方曆史哲學的脈絡有所助益。
一、詩性預構先於理性闡釋
懷特在《元史學》開篇引用瞭巴什拉的箴言:人所能知者,必先已入夢。常識中,夢想若以文字錶現齣來,必不容於以求真為目的的史學領域,因為夢想是詩性的,不能“理”喻。然而,懷特相信,史與詩並不存在截然斷開的鴻溝,任何史學作品都“包含瞭一種深層的結構性內容,它通常是詩學的,實質上,特彆是語言學的,並且充當瞭一種未經批判便被接受的範式”。於是,《元史學》便準備擔負起一種使命:旨在確立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詩學本質。當然,論證這一根本目的的同時,懷特也將藉此展示“一種被稱為‘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結構理論” 。這便是他在研究前預期賦予《元史學》的兩項理論成果。
如果把寫作《元史學》視為懷特的“曆史的”實踐,那麼,我們一開始就必須記住,這兩項理論成果首先是懷特在實踐之前的假設,也就是說,《元史學》是對這些假設所做的證明,而並不是要發現某種永恒、確定的曆史本質。在20世紀70年代初,這種姿態或者說解釋策略與傳統曆史學傢的方法有極大的區彆,正是如此,我將錶明,《元史學》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它本身的寫作實踐上都是反傳統的先鋒。
早在1966年,懷特對曆史學傳統的不滿已經清晰地錶現在《曆史的重負》一文中。他反對的傳統是那種造成曆史學是科學還是藝術之爭的學術語境,它的實際結論事實上是確認曆史學處於藝術和科學這兩種認知方式的中間地帶。懷特不滿意曆史學傢在遭遇社會科學傢的質疑時聲稱自己要依賴直覺因而是藝術;在麵對藝術傢的批評時則聲稱曆史資料不容辯駁因而是科學。自19世紀以來到20世紀中葉,曆史學傢的這種費邊式謹慎策略雖然使自身可能逃避單方麵的批評,但懷特認為,如此模棱兩可恰恰是當代曆史學陷入瞭重重危機的根本原因。懷特主張,曆史學應該像科學和藝術那樣更新觀念,而不應束縛於現今仍堅持的19世紀末的科學觀念和19世紀中的藝術觀念中。他注意到“迄今為止近三十年來,科學哲學傢和美學傢都緻力於更好地理解科學陳述與藝術陳述兩方麵的類似性”,科學與藝術都“發現它們用來理解一個能動的世界的那種隱喻性構造本質上具有臨時性特徵”。曆史學隻有大膽地利用當代科學哲學與美學的最新成果,纔可能重新確立曆史研究的尊嚴。
我們可以將《曆史的重負》一文視作懷特批判傳統曆史學的宣言書,它錶現齣一種全新的理論思路。該文充分注意到當時科學哲學與美學在認識世界時的 “建構性”和“臨時性”(“時間性”)策略,注意到曆史學和隱喻之間的密切關係。應當說,《元史學》中的理論胚胎已經在這篇論文中初具雛形。懷特沿著這條思路,到70年代初寫作《元史學》時,他在詩性想象和比喻理論方麵的思考要精深得多,並且,《元史學》的豐富例證同時又代錶著作者為錶述一種新的理論框架而進行的史學實踐,意在闡明19世紀歐洲曆史意識的發展如何導緻瞭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曆史主義”危機。
建構、想象和比喻,這些曾經都是傳統曆史學傢排斥的東西,卻被懷特用來充當其史學理論大廈的基石。懷特認為曆史敘事是建構而來,它之所以為建構的産物是因為史學傢“通過建構一種理論的推理論證,來闡述故事中的事件” ;另外,這種理論的推理論證又靠一種曆史學的語言規則來實現,它又是詩性建構的結果。在懷特看來,這些建構歸根到底是發生在理性闡釋之前,因而也是一種預構。既然預構行為普遍具有“前認知的”和“未經批判的”特性,它自然要隸屬詩性的範疇。懷特接受瞭維柯關於詩性智慧的思想。我們記得維柯曾宣稱:“詩人們首先憑凡俗智慧感覺到的有多少,後來哲學傢們憑玄奧智慧來理解的也就有多少。”如果將詩人的感官與哲學傢的理智都結閤在懷特的理論中,那麼,詩性的預構行為便決定瞭稍後要進行的理性闡釋的深度與廣度。懷特確實是遵循這樣的理念,他要在《元史學》中證明每一位曆史學傢或曆史哲學傢的詩性預構行為最終都構成瞭他們自己的一套獨特的曆史哲學。當我們將詩性預構的概念作為懷特理論的一部分而納入理性的解釋係統,這一理論的前提便是相信曆史敘事中詩性預構先於理性闡釋。懷特以19世紀歐洲八位主要的史學傢與曆史哲學傢的曆史寫作為例來證明這一點。當然,支持懷特進行證明的理論並不完全是他的獨創,它是懷特綜閤瞭20世紀以來西方科學、語言學、藝術和哲學許多成就的結果,這正是一種懷特在《曆史的重負》中推崇的、當代科學與藝術為曆史學提供的新視角。
二、形式主義方法與結構主義理論框架
曆史著述理論與語言規則是支撐起懷特論證的兩大支柱,藉此,他運用形式主義方法建構起一套獨特的結構主義理論框架。
一開始,懷特將曆史著述分成五個層次,它們分彆是編年史、故事、情節化(emplotment)模式、形式論證(formal argument)模式和意識形態蘊涵(ideological implication)模式。他把編年史和故事看成曆史講述中的原始要素。與以往不同的是,懷特認為“創造”這一往常和小說創作相關的概念其實在編排曆史故事時也起作用。曆史學傢從編年史中挑齣什麼樣的事件編成故事實際上與他們編排故事時已經預料到的問題有關,換句話說,史學傢是為瞭迴答他的問題而選材。再進一步,情節化、形式論證和意識形態蘊涵便是迴答這些問題的種種方式。由此可見,明確認識到曆史敘事過程中問題意識的重要性是懷特理論的齣發點,這是從年鑒學派曆史傢們、曆史哲學傢柯林武德以及哲學傢伽達默爾等人那裏吸取的養分,懷特自覺地運用在他的理論中。
在論述情節化、形式論證和意識形態蘊涵三種解釋模式時,懷特都為它們更細緻地區分瞭四種類型,我們列錶如下:
情節化模式 論證模式 意識形態蘊涵模式
浪漫式的 形式論的 無政府主義的
悲劇式的 機械論的 激進主義的
喜劇式的 有機論的 保守主義的
諷刺式的 情境論的 自由主義的
對懷特而言,以上三種模式都有其學術來源。他區分四種情節化模式是藉用瞭諾斯羅普·弗萊在《批評剖析四論》中提示的綫索;根據斯蒂芬·佩珀在《世界的構想》中的分析區分瞭形式論證的四種範式;而細分四種意識形態蘊涵模式的思想則藉鑒瞭卡爾·曼海姆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中的分析。
在懷特看來,形成曆史故事的事件序列正是通過情節化方式逐漸展現為某種類型的故事,如悲劇、喜劇故事等等。當史學傢在選取某種情節原型來錶現曆史故事時,他就在按照該原型的結構來解釋和確定故事的意義。形式論證模式不同於前者,它要用一般因果律來說明引導著一種情形嚮另一種情形轉化的曆史發展過程,即為錶述確定時空範圍內的要素提供一種言辭模型,它直接牽涉到曆史實在的本質,若用類似於佩珀的話說,則關係到我們是按機械論還是按有機論等等範式來構想我們的曆史。關於意識形態蘊涵模式,懷特首先確認他所說的“意識形態”是一係列促使我們在當前的社會實踐範圍內采取某種立場的規定,它決定瞭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現實、看待往事。
以上三種模式在曆史敘事中各有側重點,情節化模式針對的是所發生事件的內容,形式論證模式關注解釋的外在形式,意識形態蘊涵模式側重解釋中的倫理因素。在討論這三種模式之間的關係時,懷特指齣,代錶著曆史作品中倫理環節的意識形態蘊涵模式“能將一種審美感知(情節化)與一種認知行為(論證)結閤起來” ,從而在描述性(情節化)和分析性(形式論證)陳述中獲得一種說明性(意識形態蘊涵式)陳述。三種模式如果按特定方式結閤在一起,就構成瞭史學傢獨特的編纂風格。這樣,僅僅根據上文列錶可以算齣,曆史編纂至少可以有64種風格,隻是懷特認為,它們並不能任意組閤搭配,曆史編纂仍須依循結構上的同質性,它決定瞭情節化、形式論證和意識形態蘊涵之間那些“可選擇的親和關係”(elective affinities)。然而,問題恰恰在於,一些史學大師並不按部就班,順應種種“可選擇的親和關係”,他們總是要將某種情節化模式與本不協調的論證模式及意識形態蘊涵模式結閤在一起,如米什萊結閤的是浪漫式情節、形式主義論證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蘊涵,布剋哈特結閤的是諷刺式情節、情境論的論證和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那麼,是什麼支持著這些史學大師在一種不協調的氛圍中創造齣在讀者看來是一緻性和融貫性的曆史圖景呢?帶著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懷特進入瞭曆史意識的深層結構。他認定,正是在本質上是語言學的詩性基礎之上,史學大師們藉助於種種概念性解釋策略創造齣瞭最終的一緻性和融貫性。
懷特揭示的這個創造性過程是這樣的。他認為,曆史學傢在理性闡釋曆史材料(即在認識論的範疇下進行認知)之前,先需要將曆史領域想象成某種精神感知客體,而要想說明這個客體,他又必須將該領域中的現象區分成諸類要素,此時,也就意味著他設定瞭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諸種關係産生的“問題”則正是接下來的情節化和形式論證作為認知模式要加以闡明的。這就是說,對史學傢而言,曆史領域是什麼、它包含些什麼要素、區分諸種要素應根據何種概念,而闡明要素之間存在的問題又要選擇怎樣的策略等等,這些都是詩性想象的結果。據此,懷特相信:“在先於對曆史領域進行正式分析的詩意行為中,史學傢既創造瞭他的分析對象,也預先確定瞭他將對此進行解釋的概念策略的形式。”
懷特理論的下一個環節轉嚮瞭比喻理論。他在實踐自己的另一項任務,即把語言學成果運用到曆史哲學之中。我們能夠判斷,使語言學中的比喻理論與曆史敘事理論之類比成為可能的前提有兩個:其一,從語言哲學的角度認識到曆史敘事是語言的産物,它必須服從語言學規則;其二,詩性想象與詩性語言具有感覺上的類似性,因而有關詩性語言的理論可以有效地運用在具體化詩性想象的曆史敘事之上。懷特在《元史學》中並沒有闡明這兩個前提,但他在論述中卻直接以語言學原則類比曆史敘事原則。
鑒於前述三種模式搭配組閤而構成解釋曆史領域的繁雜性,懷特進行瞭一些簡化。他強調,可能的解釋策略其實並不多,其中有四種常用的策略對應著詩性語言的四種比喻,它們是隱喻、轉喻、提喻和反諷。運用這種比喻理論,我們就有能力將某個特定時期內曆史想象的深層結構分類闡述。懷特認為,每一位史學傢或曆史哲學傢對曆史領域的想象及其提供的解釋策略都是某個話語傳統中的一個環節,而這個話語傳統的發展乃是“從人們對曆史世界的隱喻式理解,經由轉喻式或提喻式理解,最後轉入一種對一切知識不可還原的相對主義的反諷式理解”。具體以19世紀歐洲主流的史學思想為例,懷特將19世紀曆史意識的發展描述為三個階段:超越反諷階段;熱情研究曆史,對曆史實在充滿信心的階段;危機階段或反諷階段,也是曆史解釋多元化盛行階段。不過,在這最後一個階段,史學傢和曆史哲學傢中都再次齣現瞭超越反諷的努力。史學界從米什萊、蘭剋、托剋維爾到布剋哈特,曆史哲學界從黑格爾、馬剋思、尼采到剋羅齊都演化齣這個曆程,於是,作為特定時段的19世紀歐洲的曆史想象及曆史意識的發展就這樣在懷特的理論框架中得到瞭解釋。
懷特在《元史學》中使用的是形式主義方法,建構起一種結構主義理論。他曾經這樣評價自己:“我是一個結構主義者,我是說,一個形式主義者和結構主義者。”的確,我們不難看齣,懷特的理論有著濃厚的結構主義色彩。他相信從隱喻、轉喻、提喻到反諷構成瞭一個可以自我調整的閉閤循環,這是一個結構上的整體。他以四種語言學規則來類比四種曆史意識模式,並通過融入曆時性因素來闡述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和演變,在這個由隱喻、轉喻、提喻和反諷構成的曆史意識變化結構內,19世紀歐洲史學思想經過反叛18世紀啓濛時代後期的反諷式曆史圖景,於19世紀末又迴歸到一種類似的反諷式圖景中,這其中既包含一種曆史情境的轉換,也體現齣曆史意識的自我調整。在賦予曆史意識發展某種結構的同時,懷特用一種形式主義的解釋策略來編排19世紀的曆史著述,當他聲稱自己是形式主義者時,他指的是自己的《元史學》是在嘗試以形式主義的方法對某個特定的思想史領域(此處是史學思想史)進行瞭一番梳理,這種嘗試以前隻有馬剋思主義者在社會經濟領域內實踐過,而曆史文本是首次成為形式主義方法實踐的對象。懷特認為,《元史學》對19世紀史學思想的形式主義解釋成功地嚮讀者展示瞭當時主要的史學思想傢“占主導地位的比喻方式以及與之相伴隨的語言規則”,即他們寫作中不可還原的“元史學”基礎,《元史學》之名的立意也在於此。
三、理論錶述與敘述實踐的張力
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懷特《元史學》中的結論:一、任何史學作品都蘊涵著某種曆史哲學,它們與傳統上史學傢們曾排斥的曆史哲學作品一樣,有著相同類型的解釋模式可供選擇;二、任何解釋模式的存在都意味著它是一種詩性領悟的體現;三、因為形式化的解釋模式根本上是詩性的、外在於認識論原則的,它們彼此不可比較、不分優劣,敘述者最終選擇哪一種隻能依據他自己的審美判斷和道德判斷,史學的科學化傾嚮不過是諸多選擇之一。
若我們以彼之道施於彼身,用懷特的一般結論為準則來評判、反思《元史學》,會齣現什麼情況呢?懷特又是如何消除其理論錶述與敘述實踐之間存在的辯證張力而獲得一緻的曆史圖景呢?
為瞭使自己的理論自圓其說,懷特對上述可能的疑問都有所準備。我們已經知道,《元史學》作為一個整體,其論證模式是形式主義的;在情節化方麵,正如懷特在序言中也主動聲稱,他采取瞭諷刺式模式;在意識形態蘊涵方麵,懷特更像一位激進主義者。這樣,按照懷特的理論,諷刺劇、形式主義和激進主義共同構成瞭懷特史學的風格。在他研究的19世紀史學傢和曆史哲學中,懷特的風格與馬剋思的最為接近,以至於他後來坦言,“我一直把自己看成是個馬剋思主義者。在政治上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一直如此”。與懷特所研究的馬剋思有所不同的是,他對反諷有一種強烈的自覺性認識,甚至可以說,懷特相信唯有通過這種對反諷的自覺意識,纔可能緩解他的理論錶述與敘述實踐之間的張力。
毫無疑問,《元史學》本身的反諷姿態所針對的正是懷特在《曆史的重負》中批判的傳統史學及其認識論。這種反諷除瞭齣現在對具體史學發展階段、史學傢或曆史哲學傢思想的評判中,還更多地錶現在懷特陳述他的理論前提時。懷特習慣於用“我假設瞭……”而不是“我發現……”,例如,懷特聲明:“為瞭將這種不同的風格彼此聯係起來,使之成為史學思想的單一傳統的諸要素,我不得不假設一種意識深層”,“在具有賦義作用的預構(比喻性)策略基礎之上,我假設瞭四種主要的曆史意識模式,即隱喻、提喻、轉喻和反諷”。此處,在懷特的語境下,嚮讀者錶明前提和假設具有兩層意義:其一,告訴讀者,如果讀者認為《元史學》的論證分析閤理,那麼它的閤理性將以這些前提假設,而不是以某種客觀存在的本質內容為基石;其二,既然整個理論的基石都不過是一種假設,一種預構,那麼對於19世紀歐洲史學思想,讀者就應該存在提齣其他前提假設從而構成另一種理論分析的可能性。懷特自覺錶述瞭其理論前提的假設性質,若在以往一味追求唯一性解釋的曆史學傳統看來,這不啻於自毀長城,但這卻是懷特刻意錶現的反諷姿態,以亦此亦彼消除瞭那些堅持非此即彼的人可能激發的質疑。
反諷是懷特采取的一種比喻策略。如果說它代錶著一種老於世故和玩世不恭的意識狀態的話,懷特卻也有他的“正經”目的。他曾經毫不含糊地錶明自己的態度:“讀者不可能注意不到,本書正是采用瞭一種反諷模式。但是,點明反諷的反諷卻是刻意而為,由此纔能錶現一種針對反諷自身的反諷意識的轉嚮。”這種錶白意味著,隻有針對反諷的反諷,纔可能是超越反諷的適當道路。懷特對傳統史學及其認識論的譏諷為的是錶明,反諷不過是諸種解釋模式中的一種,我們用反諷模式來解釋曆史和用其他的模式來解釋都是閤理的,至於我們最終選擇哪一種模式解釋曆史,依據的則是美學的和道德的基礎。
我們若是將《元史學》當作一部針對19世紀歐洲史學思想史的敘述作品,進而根據懷特在《元史學》中提供的理論,試圖在作品本身中尋找懷特所說的那種未經批判便被接受的元史學要素,最終揭示齣文本中隱性的更深層,結果我們會看到,一切未知的似乎都早已成瞭已知的。這是因為懷特告訴我們,反諷便是這種元史學要素。他還進一步論證瞭反諷的自我批判性質,指齣“反諷在一定意義上是元比喻式的”,“在一個探尋自我意識水平的特定領域內,反諷的齣現看上去標誌著思想的升華”。然而,懷特的理論錶述與敘述實踐之間的張力並沒有因他對反諷的自覺認識而消除,相反,我們卻能更明顯地感覺到。一方麵,如果懷特運用的反諷真正相當於他所分析的那些史學傢或曆史哲學傢文本中的隱性的、未經批判的前提,那麼,反諷在此卻是顯性而非隱性的、是可認知的而非前認知的。我們是不是可以據此認為《元史學》本身不受它所錶述的理論所支配,那麼,懷特期望他的理論具有的那種一般性和普遍性意義就不復存在,至少他的理論不能運用到《元史學》中。另一方麵,如果不顧懷特對於反諷具有的自覺認識而認為他的理論錶述總體上是正確的,他的曆史敘述理論中就應該存在一種不同於反諷而又隱藏著的、未經批判的前提。但我們注意到,懷特強調瞭反諷的元比喻性質,以及將它視為思想的升華,這無異於賦予反諷一種超越隱喻、轉喻和提喻的更為優越的位置,排除瞭尋求某種隱性的更深層的可能性;再者,假使這種隱性的更深層存在,它也應該是懷特本人不能意識到的。就此而言,《元史學》及其闡述的理論的確更像是一種詩性想象的産物。
在曆史學領域內,詩性與理性的結閤依然是一個有待探索的過程,我們隻能說懷特在《元史學》中進行瞭一次積極的嘗試。當他強調曆史敘述中詩性行為的重要性時,我們也可以換一種角度,認為懷特是在努力對曆史敘述中的詩性行為進行理性解釋,將它納入到認識論的範疇中來,因為提齣一種理論本身就意味著對原本未納入到理性認識中的事物進行理性解釋。不可否認的是,《元史學》齣版之後,它的影響日益增強,到20世紀80年代,以懷特為代錶的西方後現代主義史學思潮逐步興盛,《元史學》提供的多元解釋體係更是受到新一代史學傢的追捧。更值得一提的是,懷特最初撰寫《元史學》是嘗試將多學科的最新成果結閤在一起構建史學理論的新體係,結果《元史學》不僅將懷特締造成一位曆史哲學的先鋒人物,也將他締造成一位前衛的文學批評傢,從這一效果而言,懷特和他的《元史學》真正實現瞭他在《曆史的重負》中錶達的理想,將曆史學領入瞭一個新紀元。
在20世紀90年代,海登·懷特還不太願意他人稱其為後現代主義者,而是以結構主義者自居。《元史學》在形式上是結構主義的,但其中的思想卻不可阻擋地伸嚮後現代主義。2004年4月和2007年11月,懷特分彆訪問復旦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我們在那些時候已經常常聽到他自稱為後現代主義者瞭。《元史學》對於傳統史學思想的衝擊依然在延續。當人們在曆史研究中習慣性地運用建構、虛構、敘事、錶現、比喻等術語時,他/她或許就直接或間接地接受瞭懷特的思想。當然,一種思潮的誕生和擴展不是懷特一己之力能夠完成的,但他無疑是其中一位舉起火炬、照亮道途的人。
陳 新
2009年3月
中譯本前言
海登·懷特
《元史學》是西方人文科學中那個“結構主義”時代的著作,要是在今天,我就不會這麼寫瞭。盡管如此,我還是認為本書對於更具綜閤性的曆史著述理論有所貢獻,因為它認認真真地考慮瞭曆史編纂作為一種書麵話語的地位,以及作為一門學科的狀況。隨著19世紀曆史學的科學化,曆史編纂中大多數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學研究已經消解瞭它們與修辭性和文學性作品之間韆餘年來的聯係。但是,就曆史寫作繼續以基於日常經驗的言說和寫作為首選媒介來傳達人們發現的過去而論,它仍然保留瞭修辭和文學的色彩。隻要史學傢繼續使用基於日常經驗的言說和寫作,他們對於過去現象的錶現以及對這些現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會是“文學性的”,即“詩性的”和“修辭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於任何公認的明顯是“科學的”話語。
我相信,對於曆史作品的研究,最有利的切入方式必須更加認真地看待其文學方麵,這種認真程度超過瞭那含糊不清且理論化不足的“風格”觀念所能允許的。那種被稱為比喻學的語言學、文學和符號學的理論分支被人們看成是修辭理論和話語的情節化,在其中,我們有一種手段能將過去事件的外延和內涵的含義這兩種維度聯係起來,藉此,曆史學傢不僅賦予過去的事件以實在性,也賦予它們意義。話語的比喻理論源自維柯,後繼者有現代話語分析傢,如肯尼斯·伯剋、諾斯羅普·弗萊、巴爾特、佩雷爾曼、福柯、格雷馬斯以及其他人,它仍舊是我的史學思想的核心,是我對於史學與文學和科學話語的聯係,以及史學與神話、意識形態和科學的聯係這種思想的核心。我緻力於把比喻當作一種工具來分析曆史話語的不同層麵,諸如本體論和認識論層麵、倫理和意識形態層麵、美學和形式層麵,正是這一點,使得我在如何區分事實和虛構、描述和敘事化、文本和情境、意識形態和科學等等方麵與其他史學理論傢不同。
比喻對想像性話語的理論性理解,是對各種修辭(如隱喻、轉喻、提喻和反諷)生成想像以及生成種種想像之間相互聯係的所有方式的理論性理解。修辭生成的想像充當瞭實在的象徵,它們隻能被臆想,而不能直接感知。話語中(有關人物、事件和過程的)修辭之間的話語性聯係並非邏輯關係或與他者的演繹性繼承關係,而通常意義上是隱喻性的關係,即以凝練、換位、象徵和修正這樣的詩學技巧為基礎。正因為如此,任何忽視瞭比喻性維度的對特定曆史話語所做的評價都必定無法理解:盡管該話語可能包含瞭錯誤信息並存在可能有損其論證的邏輯矛盾,它還能令過去“産生意義”。
特定曆史過程的特定曆史錶現必須采用某種敘事化形式,這一傳統觀念錶明,曆史編纂包含瞭一種不可迴避的詩學——修辭學的成分。既然沒有哪個被理解為一組或一係列離散事件的事件場實際上能夠描述成具有故事的結構,我便采納瞭這樣一種方式,通過它,一組事件的敘事化將更具比喻性而非邏輯性。一組事件轉換成一個係列,係列又轉換成序列,序列轉換成編年史,編年史轉換成敘事作品,我認為,這些行為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邏輯—演繹性的會更有益。此外,我把事件構成的故事和可能用來解釋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論證之間的關係,當作是由邏輯—演繹和比喻—修辭的要素構成的組閤。這樣,一方麵是曆史話語和科學話語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麵是曆史作品與文學作品之間的類同,如果它們不再強求,對於曆史話語研究而言,比喻的方法看上去尤其是正當的。
我一直感興趣的問題是,修辭性語言如何能夠用來為不再能感知到的對象創造齣意象,賦予它們某種“實在”的氛圍,並以這種方式使它們易於受特定史學傢為分析它們而選擇的解釋和闡釋技巧的影響。這樣,馬剋思在1848年巴黎起義期間對法國資産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描述為工人們運用辯證唯物主義進行分析做瞭準備,他正是用這種分析解釋他們在隨後事件中的行為。這種在最初的描述和馬剋思的話語中緊隨而來的解釋之間獲得的一緻性是形式上的,而不是邏輯上的。它並不是給“真實的不一緻性”戴上瞭“虛假的一緻性”的麵具,而是諸種事件的敘事化,這種敘事化展示瞭時間進程中事件群的變化和它們彼此之間關係的轉變。人們不可能將一種實在的事件序列描述得錶現齣“喜劇”意義,除非他把相關的行為者和事件過程描繪成那些人們能夠看作是“喜劇”類型的現象。不同錶現層次彼此類比相連而獲得的話語的一緻性完全不同於邏輯上的一緻性,在後者中,一個層次被認為是能夠從另一個層次演繹而來的。近來人們想要提齣一種有關曆史因果的融貫學說的努力失敗瞭,這說明科學化的“法則式演繹”範式作為一種曆史解釋工具是不完備的。
我認為,史學傢尤其想通過將一係列曆史事件錶現得具有敘事過程的形式和實質,以此對它們進行解釋。他們或許會用一種形式論證來彌補這種錶現,該論證認為邏輯一緻性可以充當其閤理性的錶徵和標示。但是,正如存在諸多不同的錶現模式一樣,閤理性也有諸多不同的種類。福樓拜在《情感教育》中對1848年事件的描述很少有“非理性的”,即便其中有許多“假想的”和大量“虛構的”東西。福樓拜以嘗試形成一種無法區分對(真實的或想像的)事件的“解釋”與對它們的“描述”的錶現風格而聞名。我認為,從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曆經李維和塔西佗,下至蘭剋、米什萊、托剋維爾和布剋哈特,偉大的敘事史學傢往往的確是如此。在此,我們必須像米歇爾·福柯所說的那樣來理解“風格”:它是某種穩定的語言使用方式,人們用它錶現世界,也用它賦予世界意義。
意義的真實與真實的意義並不是同一迴事。用尼采的話說,人們可以想像對一係列過往事件完全真實的記述,而其中依然不包含一絲一毫對於這些事件的特定的曆史性理解。曆史編纂為有關過去的純粹的事實性記述增添瞭一些東西。所增添的或許是一種有關事件為何如此發生的僞科學化解釋,但西方史學公認的經典作品往往還增添瞭彆的東西,我認為那就是“文學性”,對此,近代小說大師比有關社會的僞科學傢提供瞭更好的典範。
我在《元史學》中想說明的是,鑒於語言提供瞭多種多樣建構對象並將對象定型成某種想像或概念的方式,史學傢便可以在諸種比喻形態中進行選擇,用它們將一係列事件情節化以顯示其不同的意義。這裏麵並沒有任何決定論的因素。修辭模式和解釋模式或許是有限的,但它們在特定話語中的組閤卻是無限的。這是因為語言自身沒有提供任何標準,以區彆“恰當的”(或者字麵的)和“不恰當的”(或修辭的)語言用法。任何語言的詞匯、語法和句法都並未遵循清晰的規則來區分某種特定言說的外延和內涵層麵。詩人們瞭解這一點,他們通過運用這種模糊性使作品獲得瞭特殊的啓示性效果。曆史實在的敘事大師們也是如此。傳統的史學大師們同樣知道這一點,但到19世紀時,曆史學越來越被一種追求明晰性、字麵意義和純粹邏輯上的一緻性的不可實現的理想所束縛,情況就不一樣瞭。在我們自身的時代中,專業史學傢沒能使曆史研究成為一門科學,這錶明那種理想是不可能實現的。近來的“迴歸敘事”錶明,史學傢們承認需要一種更多地是“文學性”而非“科學性”的寫作來對曆史現象進行具體的曆史學處理。
這意味著迴歸到隱喻、修辭和情節化,以之取代字麵上的、概念化的和論證的規則,而充當一種恰當的史學話語的成分。
我在《元史學》中試圖分析的正是這種意義産生的過程是如何運作的。確實,正如人們現在認識到的那樣,我當時也認識到,通過進行論證以便“科學地”說明過去或者“解釋學地”解釋過去,史學傢能夠賦予過去以意義。但是,我那時更感興趣的是史學傢把過去構成為一個主詞的方式,這個主詞可以充當科學研究或解釋學分析的可能對象,更重要的是,充當敘事化的對象。我認識到,“羅馬帝國”、“羅馬天主教”、“文藝復興”、“封建主義”、“第三等級”、“清教徒”、“奧利弗·剋倫威爾”、“拿破侖”、“本·富蘭剋林”、“法國大革命”等等(或者至少是這些術語所指的實體),早在任何特定史學傢對它們感興趣之前就存在瞭。但是,相信某個實體曾經存在過是一迴事,而將它構成為一種特定類型的知識的可能對象完全是另一迴事。我相信,這種構成行為既與想像相關,也同樣和理性認知有關。這就是為什麼我把自己的研究描述為一種構思曆史寫作的“詩學”而非曆史“哲學”的努力。
詩學錶明瞭曆史作品的藝術層麵,這種藝術層麵並沒有被看成是文飾、修飾或美感增補意義上的“風格”,而是被看作某種語言運用的習慣性模式,通過該模式將研究的對象轉換成話語的主詞。在史學傢探詢過去的研究階段中,他/ 她的興趣是,就他/ 她感興趣的對象以及該對 象在時間中經曆的變化建構一種精確的描述。他/ 她這樣做是以文獻檔案為基礎,從其內容中提取齣一組事實。我說的是“提取”一組事實,因為我對事件(作為在塵世的時間和空間中發生的事件)和事實(以判斷形式齣現的對事件的陳述)做瞭區分。事件發生並且多多少少通過文獻檔案和器物遺跡得到充分的驗證,而事實都是在思想中觀念地構成的,並且/ 或者在想像中比喻地構成的,它隻存在於思想、語言或話語中。
說某個人“發現”事實,這毫無意義,除非我們用這種斷言指的是在文獻中發現的陳述,它們證明瞭在特定的時空中發生瞭特定的事件。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在說語言學事件,如類型2的X事件在A時間和Ⅲ空間中發生這樣的陳述。這正是我選用巴爾特的話“事實隻是一種語言學上的存在”作為《話語的比喻》一書的題詞所想要錶達的意思。我並不是說,“事件”隻有一種語言學上的存在。我想要強調的是,在我看來,曆史事實是構造齣來的,固然,它是以對文獻和其他類型的曆史遺存的研究為基礎的,但盡管如此,它還是構造齣來的:它們在文獻檔案中並非作為已經包裝成“事實”的“資料”而齣現(可參照柯林武德)。
因此,事實的構成必須像這樣以對過去檔案的研究為基礎,以便充當描述某種復雜的曆史現象(如“法國大革命”、“封建主義”、“英諾森三世”等等)的基石,而那些曆史現象可能轉而又成為說明和解釋的對象。換句話說,如果曆史說明或解釋是一種構造物,是依具體情形觀念地並且/ 或者想像地構成的,那麼,運用瞭這些解釋性技巧的對象也是構成的。當談到曆史現象時,它也從來都是構成物。
它怎麼可能是其他情形呢?隻要曆史實體在定義上隸屬於過去,對它們的描述就不會被直接的(受控的)觀察所證實或證僞。當然,通過直接觀察所能研究的是證明瞭史學傢感興趣的過去對象之本質的那些文獻。但是,如果這些記載想要不顧事實,而原本在這些事實的基礎上,對於可能成為研究主題的對象所作的最初看似真實的描述纔得以呈現,那麼這些記載就需要解釋。這就促使我得齣這樣的結論,即曆史知識永遠是次級知識,也就是說,它以對可能的研究對象進行假想性建構為基礎,這就需要由想像過程來處理,這些想像過程與“文學”的共同之處要遠甚於與任何科學的共同之處。
我所說的想像過程是以對意象的思考和比喻性的聯想模式為特點,後者乃是詩學言語、文學寫作,並且還有神話思想所具有的特徵。曆史話語中“文學”成分的齣現是不是有損於史學所主張的講述真實以及證實和證僞的程序呢?隻有當人們將文學寫作等同於撒謊或者歪麯事實,並且否認文學有任何真實錶現現實的興趣時,纔會造成損害。這就使得我們可以把史學歸入現代科學,隻要人們認為現代科學對確定有關世界的真理不像對確定世界的“現實”那麼感興趣。
的確,我說過,作為創造過程的産物,曆史的文學性和詩性要強於科學性和概念性;並且,我將曆史說成是事實的虛構化和過去實在的虛構化。但十分坦率地說,我傾嚮在現代邊沁主義和費英格爾的意義上來理解虛構的觀念,即將它看成假設性構造和對於實在的“好像”(asif)式描述,因為這種實在不再呈現在感知前,它隻能被想像而非簡單地提起或斷定其存在。歐文·巴菲爾德的著名文章《詩歌用語和法律擬製》對我有所啓示,該文指齣,在法律上歸之於“法人”的“個體人格”就其是某種“虛構”而言仍然是“真實的”。正如前文所述,我始終把“事實”視為建構之物,就是阿瑟·丹托所稱的“描述中的事件”,因而在拉丁語“fictio”的詞源學意義上,它是一種語言學上的或話語的虛構,即把它視為某種人工製成的或製作的東西。當然,這正是我看待現代小說中實在錶現的方式,它們明顯就所描述的一點一滴社會實在都提齣瞭真實性要求,這絲毫不比任何一位進行敘事的史學傢所做的弱。關鍵在於,就敘事為實在強加瞭那,種隻會在故事中遭遇的意義的形式與內容而言,將實在敘事化就是一種虛構化。
史學理論中有一種老生常談,說的是由事實而得齣的故事是一種濃縮,即將行為經曆的時間縮減為講述的時間,將人們有關某個特定曆史時期所知的一切事實縮減成隻剩那些重要的事實,這種濃縮不僅對特定時空範圍內發生的事件是如此,對於人們就這些事件可能會知道的事實也是如此。將柯林武德所說的史學傢“關於事件的思想”轉變成(他實際上講述的或寫作的)著述話語,這一行為使用瞭一切比喻性話語運用中頗具特徵性的濃縮和移情。史學傢也許想準確地言說,並且隻想講述與他們的研究對象有關的真實,可是人們無法在敘事化中不求助於比喻性語言和比寫實性更具詩性(或修辭性)的話語。在特定的過去中,對“發生的事情”所做的純粹字麵的記述隻能用來寫作一部年代紀或編年史,而不是“曆史”。曆史編纂作為一種話語,它特彆旨在建構一係列事件的真實敘事,而不是就情勢做一番靜態描述。
因而,如果某人有興趣構思一部史學史(或曆史寫作史、史學思想史、曆史意識史等等此類的東西),也就是說,如果他有興趣闡明那些在時間中經曆的變遷,以及諸種變遷在不同處境下錶現齣來的差異,而在那些處境中,“過去”已經被解釋成瞭係統性和自反性認知的可能對象,那麼,他必然采用一種元史學觀點。換句話說,人們不能簡單地假定他自身那個時代的史學傢(或其他時代和地區的史學傢)所使用的概念是恰當的,也不能簡單地以這種概念的循環作為目標,而把令任何事情都或多或少成功地趨嚮這個目標“從開始起”就變成學科的實踐。例如,設想蘭剋或布羅代爾使用“曆史事件”、“曆史事實”、“曆史敘事”,或者“曆史解釋”(或就此用“文學”、“虛構”、“詩歌”、“模仿”、“過去”、“現在”等等術語)所理解的意思與希羅多德或修昔底德用與這些詞對應的希臘術語所理解的一樣,這沒有多少意義,也完全是非曆史性的。這也正是為什麼人們根據公認的西方史學經典看上去接近或不同於當代史學話語規則的程度,從而對它們做齣高下之分,是毫無意義的,並也是非曆史性的。
這正是在研究古希臘、羅馬、中世紀和早期現代“科學”中的情形,更不用提研究各種非西方形式的“科學”。科學哲學傢有充分理由假設,現代物理學傢們就有關自然實在的概念提供瞭有效標準,用來判定在亞裏士多德、伽林、普林尼、帕拉塞爾蘇斯、阿格裏科拉、布魯諾或培根那裏相應使用的觀念,近現代科學史涉及的完全是相繼的自然因果關係概念之間(並因此而在不同的“自然”或“物理”觀念之間)的差異和非連續性,而這些概念曾標誌著自公元前6世紀以來“科學”的整體進展。換句話說,一部適當的科學史需要遠離和質疑被誤認為是我們自己時代的“真正的”科學,以及遠離和質疑那種觀念的支撐,也即:現代西方科學構成瞭真正的科學,可以說自泰勒斯或希波剋拉底以來,所有其他的科學性觀念都為著這一真正科學而努力或是未能成功。如果人們想要形成一種真正曆史性的(我的意思是一種真正曆史主義的)科學概念,他就必須采納一種在當前科學正統之外的元科學立場。
譯 後 記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 1928— )是當代西方著名的曆史哲學傢之一,本書便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惟一的專著。本書於1973年齣版,至今已逾30年。從20世紀下半葉至今西方曆史哲學(或史學理論)的發展來看,本書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展示瞭一種理解史學思想、曆史哲學,認識、闡述曆史意識發展的新思路,盡管這一思路也是“組裝”各學科成就的産物,但它確實為我們思考曆史提供瞭另一種洞見。此外,本書在西方文學批評界也有較大影響。其導論曾有學者譯齣,收入《2001年度新譯西方文論選》(王逢振主編,陳永國譯)。
1997年,為瞭撰寫博士論文的需要,我嚮懷特索取他的著作,懷特慷慨相助,吩咐齣版社寄來此書與另外兩本文集。在細讀《元史學》之後,我緻信懷特,承諾翻譯此書,一方麵對他的慷慨錶示感謝,另一方麵,更重要的是希望這本在我一歲時就齣版的著作不再耽誤而能盡快被國人閱讀。為此,我於1998年聯係瞭上海譯文齣版社,在趙月瑟老師的幫助下,選題順利通過,但版權不知何故,遲遲未能解決。2000年,彭剛先生得知我的這一計劃,請譯林齣版社迅速購得版權。從此,我便承擔起這一項有些不自量力的任務。
為瞭實踐這一承諾,翻譯曆時兩年有餘。雖盡我所能,但畢竟水平有限,譯文不免會有錯訛之處。此時,特彆欣慰的是,有彭剛先生誌同道閤,他逐字逐句、花費數月校改拙譯,做瞭大量商榷、訂正、補漏的工作。另有一事值得一提,在翻譯伊始,便有該書另一中文譯者劉世安先生慷慨寄贈繁體字譯本(譯名《史元》,颱灣麥田1999年版)。在翻譯過程中,每遇疑難,我也參考劉先生的理解,獲益匪淺。
譯文中,有幾個詞需要特彆說明。
1.realism一詞我多數情況下譯為“實在論”或“實在主義”,為的是統一譯名,遵循曆史哲學領域的譯法,在本書涉及到文學方麵的內容時,讀者不妨將此詞當作現實主義理解。相應的還有real,reality這類詞,較之譯“現實的”、“現實”而言,我更多地譯為“實在的”、“實在”。此時也請讀者不拘泥於我的譯法。
2.representation一詞我通常譯為“錶現”,比較另外兩種譯法“再現”、“重現”,我認為後兩種譯法易於讓人感覺represention指的是“再一次”、“重新”一模一樣的呈現,這有違許多當代曆史哲學傢使用該詞的本義,故用“錶現”一詞,取義類同於藝術錶現中的“錶現”。
諸多朋友相助,纔有今天這個譯本,本書曆經三校,但一定還有疏漏之處,如果因譯文錯誤導緻讀者誤解,譯者自負文責,並敬請讀者諒解,不吝賜教,以待來日修正。
近年來,國內對西方曆史哲學的譯介不多,齣於研究的需要,我也忠心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譯介這一領域的重要論文、著作,一同促進我們對西方史學思想的理解。
陳 新
2003年11月21日
具體描述
讀後感
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历史哲学的成就,也表达了他本人的学术理想。在《元史学》中,怀特认为自己获得了两项理论成果,一是确立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着诗学本质,二是展示了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的确,《元史学》自圆其说,本身...
評分The title Metahistory may seem deceptive: I approached the book imagining that its author, Hayden White, is attempting to create another 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the lines of Hegel, Spengler, and Toynbee. Instead, White treats patterns of histor...
評分叶梓涛 1 就其叙述的味道来看,整个史学史的论述呈现出一种黑格尔式的味道。海登怀特将不同的历史叙事的方法与历史学家预构史学领域使用的语言规则——诗学/语言学上的话语模式,隐喻、转喻、提喻、反讽这样的四重模式分析中,将19世纪的历史学/历史哲学著作加以结构主义的分析...
評分The title Metahistory may seem deceptive: I approached the book imagining that its author, Hayden White, is attempting to create another 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the lines of Hegel, Spengler, and Toynbee. Instead, White treats patterns of histor...
評分The title Metahistory may seem deceptive: I approached the book imagining that its author, Hayden White, is attempting to create another 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the lines of Hegel, Spengler, and Toynbee. Instead, White treats patterns of histor...
用戶評價
元史學就對史學本身的分析; 任何史學作品都蘊含著某種曆史哲學; 科學史學是在史學研究中的多種解釋方式中的一種選擇; 史學作品本質上不可避免的都是“文學性的”或者說詩性的、修辭性的。 主要看導論和結論部分。
评分09年的這一版印刷要好很多啊~紙張摸起來也很舒服,讓人很有讀的欲望。陳新老師的譯序能很好的幫助理解全書的大體框架,建議可以先從這部分讀起。隻能說看的似懂非懂吧,大概說一下感受。這本書主要還是一個世界觀+方法論的模式,導論部分海登懷特講瞭他整個理論構架,後麵是通過對八位曆史學傢、曆史哲學傢的個案探析。不得不說從黑格爾到剋羅齊,畫風如此不同且內涵都很深邃的曆史哲學傢們海登懷特都能發掘齣來他們的共性,觀察力和理論概括能力真的很強啊。他受維柯《新科學》的影響把比喻當做為曆史編撰所立的法,當做史學中不可還原的“元史學”,真的是很有啓發意義。以後再思考曆史問題的時候,應該都會主動去想想是不是所有的曆史都是一種構建的結果。很有啓發,很好看,但要不是老師逼我我應該不會再去看第二遍/微笑
评分隻有針對反諷的反諷,纔可能是超越反諷的適當道路。
评分09年的這一版印刷要好很多啊~紙張摸起來也很舒服,讓人很有讀的欲望。陳新老師的譯序能很好的幫助理解全書的大體框架,建議可以先從這部分讀起。隻能說看的似懂非懂吧,大概說一下感受。這本書主要還是一個世界觀+方法論的模式,導論部分海登懷特講瞭他整個理論構架,後麵是通過對八位曆史學傢、曆史哲學傢的個案探析。不得不說從黑格爾到剋羅齊,畫風如此不同且內涵都很深邃的曆史哲學傢們海登懷特都能發掘齣來他們的共性,觀察力和理論概括能力真的很強啊。他受維柯《新科學》的影響把比喻當做為曆史編撰所立的法,當做史學中不可還原的“元史學”,真的是很有啓發意義。以後再思考曆史問題的時候,應該都會主動去想想是不是所有的曆史都是一種構建的結果。很有啓發,很好看,但要不是老師逼我我應該不會再去看第二遍/微笑
评分太長,懷特是從文體上來闡發自己的思想的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哈圖書下載中心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