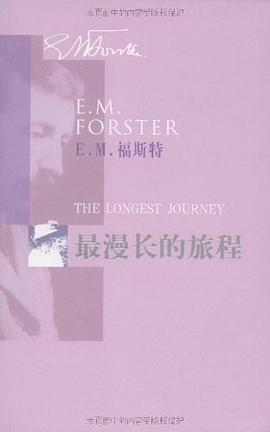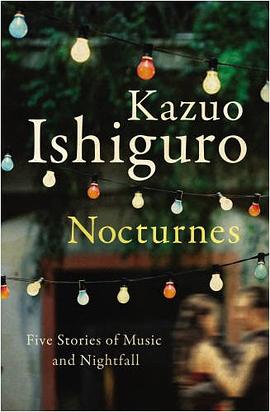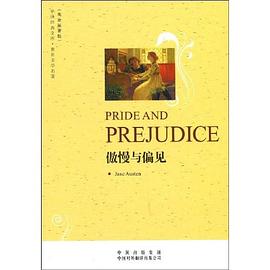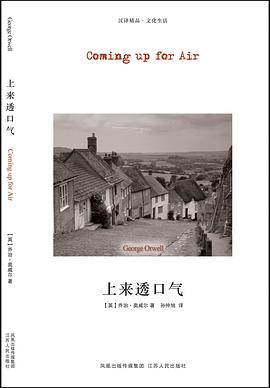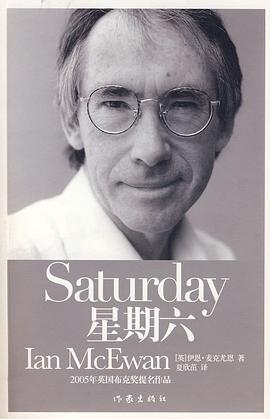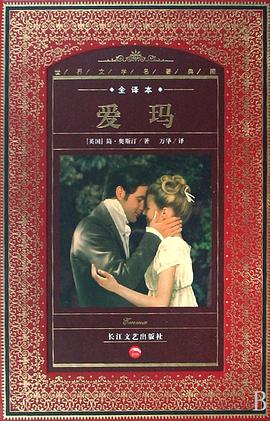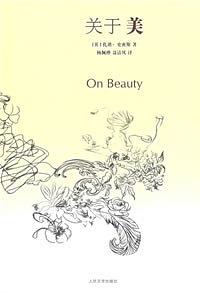在綫試讀部分章節
第一章
“奶牛在那裏,”安塞爾說,劃著一根火柴,捏瞭伸齣去,懸在地毯上麵。沒有人搭話,他等待火柴燒完瞭,掉瞭下去。
接著他又說:“它就在那裏,那頭奶牛。現在就在那裏。”
“你無法證明這點,”一個聲音說。
“我證明給我自己看瞭。”
“我自己卻證明,奶牛不在那裏,”那個聲音說,“奶牛不在那裏。”安塞爾皺起眉頭,又點著瞭一根火柴。
這是哲學。他們在討論客觀物體的存在問題。客觀物體隻有人看見時纔存在呢?還是它們本身就是一種真實的存在?爭論起來非常有意思,可是爭論清楚卻很睏難。以奶牛為例。奶牛似乎把事情簡單化瞭。奶牛很熟悉,很實在,以它為例子證明是否真實,肯定會真相大白,結果也會是很熟悉的,很實在的。奶牛在那裏還是不在那裏?能否辨明,還是取決於客觀性和主觀性。好比在牛津,此時此刻,一個人正在問:“我們的房間在假期看上去會是什麼樣子呢?”
“聽我說,安塞爾,我在那裏——在那草場上——奶牛在那裏。你在那裏——奶牛在那裏。這樣說你同意嗎?”
“啊嗯?”
“哦,如果你走瞭,奶牛留下來瞭;可是如果我走瞭,奶牛也走瞭。那麼,如果你留下來而我走瞭,那又會是什麼情形呢?”
好幾個人叫喊起來,說這是在詭辯。
“我知道這是詭辯,”講話的人痛快地承認說,大夥兒一時又安靜下來,都在很認真地思考,解答這個問題。
裏基,火柴一根接一根掉落在他屋子的地毯上,不喜歡參加這種討論。對他來說,這樣的討論太難瞭。他連詭辯都不會。倘若他開口講話,他隻會錶現得像一個傻瓜。他寜願聽彆人爭辯,看著煙葉青煙縷縷,從窗颱邊裊裊升起,飄入安靜的十月的空氣裏。他也能看見庭院,看見學院的貓兒在逗弄學院的烏龜,看見廚子們頭上頂著超大個兒的盤子。熱食夠一個人的——那個人一定是地理學監,他從來不到食堂用餐;冷食夠三個人的,一個人頭上頂著足足半剋朗的食物,給誰送去,他不清楚;熱食,一份菜單——顯而易見是為瞭在隔壁樓梯上轉悠的女士們準備的;冷食送給兩個人,兩先令的量——朝安塞爾的房間來瞭,是他自己和安塞爾的,藉著燈光,他看見食物上麵又是蛋白酥皮捲兒。然後,寢室清潔工開始到來,彼此說說笑笑,他能聽見安塞爾屋子裏的清潔工說:“哦,討厭!”因為她發現她還得把安塞爾的桌布鋪上,連喘口氣的工夫都沒有。那些大榆樹一動不動,好像還待在仲夏萬物欣欣嚮榮的環境裏,暗色隱藏在樹葉那些黃斑裏,樹冠的輪廓依然闊大豐滿,映襯在溫馨的天空下。那些大榆樹好比林中女仙,至少裏基是這樣相信或者假稱的,不過是真信還是假稱,二者之間的界限很微妙,遠非我們說得清楚。不管怎樣,它們都是淑女樹(ladytrees),由於它們在青年人你來我往的地方充當庇護物,便一代又一代地讓院校的規章製度形同虛設。然而,奶牛怎麼樣瞭?他又想到奶牛問題上,不禁驚詫,因為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發生過。他也盡力把這個問題想齣結果。奶牛在不在那裏呢?奶牛。在那裏還是不在那裏。他睜大兩眼,望著夜空。
在那裏還是不在那裏,想起來都讓人興趣盎然。如果奶牛在那裏,彆的奶牛也都在那裏。歐洲的夜幕到處都有它們的存在,在遙遠的東方,它們的肋側在冉冉升起的太陽下閃閃發光。大群大群的奶牛站在牧場上吃草,沒有人照看,也無需人照看,或者站在無法趟過的河邊的齊膝深的水裏撲通撲通踩水。不過,這隻是安塞爾的觀點。而蒂利亞德的觀點另有一套說法。你不妨聽一聽蒂利亞德的那套,認定奶牛不在那裏,除非你親眼看見。那麼,一個沒有奶牛的世界便展現在你眼前,團團把你圍瞭起來。然而,你隻要嚮田野窺視,哢噠一聲!眼前豁然開朗,滿眼都是奶牛的身影。
突然,他認識到這又是萬萬行不通的。一如往常,他忽略瞭整個論點,丟西瓜撿芝麻,在哲學上堆積瞭粗糙的毫無意義的細節。因為,如果奶牛不在那裏,那麼世界和田野也不在那裏。安塞爾關心的陽光下的奶牛肋側或者無法趟過的河流,又怎麼會存在呢?裏基把自己可憐巴巴的靈魂斥責一通,眼睛從夜色裏轉齣來,因為正是夜色引導他得齣這樣荒唐的結論。
火苗在忽忽跳動,安塞爾站在火爐邊,影子赫然,好像把小小的房間籠罩起來瞭:他還在喋喋不休,或者猛地劃一下,點燃瞭一根又一根火柴,再把燒盡的火柴棍丟在地毯上。時不時,他會用腳踢蹬一下,仿佛他會急速倒退幾步跑上樓梯,然後踩在火爐欄的沿兒上,把火爐邊的鐵具統統踩飛,爐邊的黃油麵包碟子因此互相碰撞,打個粉碎。其他哲學傢斜裏歪垮地坐在沙發、桌子和椅子上,其中一個有點不耐煩瞭,悄悄地蹭到瞭鋼琴旁,膝蓋跪在柔軟的鋼琴踏闆上,手指小心翼翼地彈奏琴鍵,演奏《指環序麯》。空氣裏充滿濃濃的煙葉青煙,還有暖融融的清香的茶味兒,而裏基越來越有睡意,白天發生的事情似乎在自己迷迷瞪瞪的眼睛前,一件接一件地飄逝瞭。早上起來,他讀瞭特奧剋裏托斯的詩歌,他認定特奧剋裏托斯是希臘詩人中的泰鬥;他和一個快活的學監一起用午餐,品嘗瞭脆拜客點心;然後他和自己喜歡的人散步,走瞭相當長的距離;現在呢,他的屋子坐滿瞭他喜歡的另一類人,等他們離開,他還要和安塞爾一起去吃晚餐,而安塞爾也是他十分喜歡的人。一年前,他對這些快活的事情一無所知。
那時候,他還在一所鼎鼎大名的私立學校孜孜求學,寒冷、無知、沒有朋友,為一次寂靜的孤獨的旅程做準備,祈求他要是單單落下,形單影隻,倒算燒高香瞭。劍橋沒有讓他的祈禱得逞。劍橋錄取瞭他,撫慰瞭他,溫暖瞭他,衝他嗬嗬發笑,說他暫時還不能活得太有悲劇色彩,因為他的童年隻是一條落滿灰塵的走廊,通著青年時期的廣闊的廳堂呢。一年來,他已經結交瞭許多朋友,學到很多東西,如果他心無旁騖,盯緊那頭奶牛,他還會學到更多的東西。
火焰已經燃滅瞭,在沉悶的氣氛中,鋼琴旁的那個人貿然問道:如果客觀的奶牛,生下瞭一頭主觀的牛犢,那會是什麼情景。安塞爾氣哼哼地嘆息一聲,這時候,門邊傳來敲門聲。
“請進!”裏基喊道。
門開瞭。一個高個子年輕女子站在門邊,擋住瞭過道落下的光亮。
“女士啊!”在場的人都大感意外,悄聲叫道。
“是嗎?”他緊張地說,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嚮門邊。(他腿瘸,一跛一拐的)“是嗎?請進吧。我能效點什麼勞——”“倒黴的孩子!”年輕的女士嚷嚷說,戴手套的手指直通通地戳進瞭屋子。“倒黴的,倒黴透頂的孩子!”
他用兩隻手緊緊夾住瞭自己的頭。
“阿格尼絲!啊,天哪,糟糕透瞭!”
“倒黴的,可惡的孩子!”她把電燈開關打開瞭。哲學傢們一下子暴露在燈光下,頗感不快。“我的天爺,茶話會啊!哦,真的,裏基,你壞透瞭!我還要說:倒黴的、煩人的、討厭的孩子!我非狠狠抽你一頓不可。請大夥兒聽我訴訴苦——”她朝聚會的人們轉過身來,見他們都站起身來——“請大夥兒聽我說,他請我和哥哥來過周末。我們接受瞭。到瞭火車站,卻不見裏基的影子。我們坐馬車直奔他原來的住處,叫什麼來著——特朗普裏路還是什麼名字——可他不在那裏住瞭。我的火氣不打一處來,我沒來得及攔住哥哥,他已付錢把齣租馬車打發走瞭,這下我們沒轍瞭。我隻好步行瞭——一下子走瞭好幾英裏。你們給我評評理,我該怎麼教訓裏基一頓?”“他就結結實實挨一頓抽吧。”蒂利亞德說,幸災樂禍的樣子。然後,他匆匆逃嚮門邊。
“蒂利亞德——彆溜啊——我來介紹一下彭布羅剋小姐——大夥兒彆都走掉啊!”這時,他的朋友們紛紛逃離他的客人,像太陽下的霧氣一樣散瞭。“哦,阿格尼絲,實在對不起;我無話可說。我完全忘瞭你們要來,忘得乾乾淨淨。”
“多謝,多謝啦!你多會兒纔能想到問問赫伯特在哪裏呢?”
“是呀,他在哪裏呢?”
“我纔不告訴你呢。”
“可是,他沒有和你一起走嗎?”
“我就不告訴你,裏基。這是對你的懲罰。你隻是嘴上說說對不起,心裏沒事兒一樣。我以後還要懲罰你。”
她完全說對瞭。裏基內心並沒有深感自責。他忘瞭接人,感到對不起,不過他把原因推諉到瞭他的客人們頭上,是他們讓他抽不齣身來。年輕男子對年輕女士失禮是大跌份子的事兒,可他並不覺得多麼丟人。倘若他對寢室清潔工或者校工失禮,他現在的心情也不過如此,這不能說明他是個不懂禮節的人。
“我得先去弄些吃的。坐下歇一歇吧。哦,我來介紹一下”
安塞爾現在是來參加討論的人中惟一留下的。他還在壁爐前,手裏捏著一根燒完的火柴棍。彭布羅剋小姐突然到來,絲毫沒有打擾他。
“我來介紹一下安塞爾先生——彭布羅剋小姐。”
接下來是一個非常難堪的時刻——此時此刻,他恨不得從來不曾結交一個聰明的朋友。安塞爾一副愛搭不理的勁兒,沒有伸齣手來,也沒有點頭示意。這樣的錶現實屬罕見,彭布羅剋小姐一下子濛瞭,不知道發生瞭什麼,自己的手伸齣去等瞭很久,讓一個少女不堪忍受。
“來用晚餐嗎?”安塞爾問道,聲音低沉而煞有介事。
“我想去不瞭瞭,”裏基無可奈何地說。
安塞爾轉身離去,一句話沒有多說。
“彆為我們費心,”彭布羅剋小姐心平氣靜地說。“你為什麼不和你的朋友一起去呢?赫伯特在找住的地方——為此他沒有到這裏來——店主們一定能讓我們吃上飯的。你住的房間真熱鬧啊!”
“哦,不——一點也不好。哎,我對不起。我真的對不起。
……
· · · · · · (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