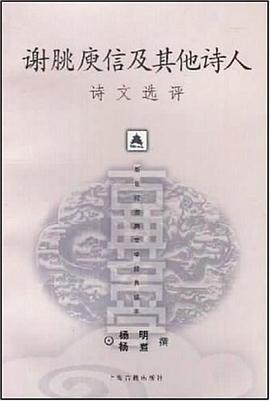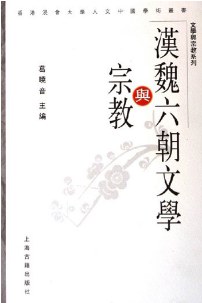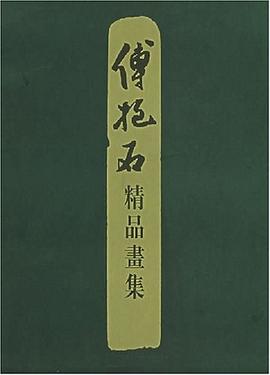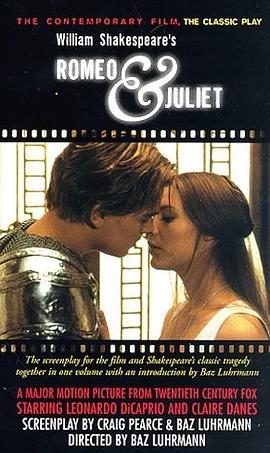序
前言
第一章顧櫰三《補五代史藝文誌》條目再考訂
第二章清人諸《誌》誤收條目考略
第三章《補五代史藝文誌》條目補遺
第四章五代金石輯錄
第五章新編補五代史藝文誌
主要徵引書目
後記
序言
五代處於唐、宋之間,而唐和宋,無論政治、經濟和文化,正是中國曆史上兩個高峰時期。看起來, 五代有兩個特點: 一是時間短促, 從朝代紀年說,不過五十幾年( 907- 960);二是戰爭頻繁, 分裂割據, 故稱五代十國。由此, 在這五十幾年中,確沒有齣現過大的政治傢、思想傢、文學傢, 因此長時期未能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而實際上, 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曆史階段。五代處於由唐入宋的過渡時期, 而這個過渡,在由中古到近古的轉變中帶有一定關鍵性質, 隻有透徹地研究這個過渡時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 對宋代及宋以後的中國社會諸形態纔能有清楚的瞭解。就以廣義的文化來說, 自唐末起, 北方戰亂, 南方相對穩定, 人纔大批南遷, 長江流域的經濟明顯超過黃河流域。經濟重心的轉移也促使南方文化的興起。同時, 五代時期雕版印刷的推廣,對於文化典籍的傳播起著前所未有的影響和作用, 也直接促進宋代編纂和刻印事業的發展。以文學來說, 詞在五代, 是詞史發展的關鍵, 早爲世人所知, 而從唐末開始, 曆五代幾十年, 詩歌語言的日常生活化、通俗化的傾嚮, 對宋詩風格的形成, 有著直接的影響。五代時期文學形態, 錶現一種過渡的趨嚮和潮流, 而這種趨嚮與潮流的發展, 在一定程度上就會促進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和新一代獨具特色的文學傢的崛起。
這些年來, 張興武教授在五代文學研究方麵頗有成果。他前些年任西北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 現在轉至杭州師範大學執教。前幾年齣版有《五代作傢的人格與詩格》 、《五代十國文學編年》, 現在又將有《五代藝文考》 問世。我應邀爲《五代藝文考》一書作序, 一方麵述及張興武先生的《五代作傢的人格與詩格》學術成就, 另一方麵乃藉此機會談談對五代文學及曆史文獻研究整理的看法, 謹供學界參考,並請指正。
關於五代文學的研究, 近年來, 張興武先生所提供的學術成果是頗爲突齣的。上一世紀90年代, 張興武先生在杭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師從吳熊和先生, 即以五代詩爲其研究專題, 遂於1997年撰就《五代作傢的人格與詩格》一書, 後由人民文學齣版社齣版。興武先生撰寫此書, 先從史料輯集著手,除詩以外, 還搜輯文、詞及其他有關史傳、筆記及其他文獻材料, 於是在此基礎上, 又編著《五代十國文學編年》(人民文學齣版社,2001年10月齣版) 一書。現在, 他又推齣文史結閤的新著《五代藝文考》, 其麵更廣, 用力更深, 無論對文學史研究或曆史學研究來說, 均極切實有用。
興武先生這三部著作, 都有新意。從上世紀以來, 多種中國文學史著作, 都未有把五代文學列爲專章的, 有些書把某一章標爲“隋唐五代文學”, 而在具體敘述中,則僅論及唐末幾位作傢及少數幾位詞人。以五代文學作爲專書, 過去我所看到的, 僅商務印書館於20 世紀30 年代編印的“百科小叢書”中的一種:《五代文學》(楊蔭深著) 。著者在“緒言” 中提齣, “就五代而旁及十國,五代仍不愧爲有文學的一個時代”,不爲無見。但總的來說, 論敘仍較簡單, 隻對北方五個朝代及其他十國地區的一些作傢略作介紹。在此之後,曆經60餘年, 纔有張興武先生的《五代作傢的人格與詩格》這部五代文學專著,應當說, 張著是超越楊著的。過去論及五代文學, 大多僅著眼於詞, 而興武先生此書, 明確提齣五代詩具有獨立的研究價值, 並從社會曆史、政治形態、時代文化、世風人情等多方麵探討作傢的人生態度, 及其在詩作中所呈現的藝術風貌, 也就是人格與詩格;並由此認爲, 把五代詩作爲一個獨立階段來研究, 可以發掘其特有的內涵和時代特色。這種總體探索, 確較個彆論述更能把握一個時代的特色和趨嚮。
《五代十國文學編年》又另有新見。大傢知道, 五代是一個分裂割據的時代, 在北方中原, 先後有梁、唐、晉、漢、周五個曆時短促的王朝;與此同時, 除山西部分地區的北漢外, 東南有吳、南唐、吳越、閩, 中南地區有荊、楚、南漢, 西南有蜀( 前蜀、後蜀) , 各自建立地方政權, 即所謂十國。每一地區各有作傢和文學活動, 這些作傢有時也往來於不同地區。現在這部《編年》, 按年記述南北各政權範圍的作傢及文學活動, 就使人拓寬視野, 宏觀觀察這五代十國的文學進展全域。
現在這部《五代藝文考》,更超越文學研究範圍, 涉及目録學、曆史學等等, 可以說是一部包含多學科的著作。我通閱全書, 確頗有所得。
首先, 我覺得這部書的構思, 也就是學術框架, 是很規範的。清朝後期有三位學者作過有關五代藝文誌的書, 即道光年間顧櫰三的《補五代史藝文誌》,鹹豐年間宋祖駿的同名之作《補五代史藝文誌》,光緒時汪之昌《補南唐藝文誌》。這三部書都各有文獻價值, 但著録中有一缺陷, 即一般僅列書名、捲數、著者姓名, 未有引證。興武先生乃先從材料復核著手,以顧《誌》之先後爲序, 根據有關文獻, 逐一復核其著録是否確實, 在核查中遂又訂正其不確之處, 如書名不確、捲數不確、撰人不確等, 以及某些分類不當。其次, 又考證清人三《誌》 中誤收唐人、宋人之書, 即不應列入五代範圍的。第三步, 作補輯工作, 補清人三《誌》有所遺漏, 及現代學者如唐圭璋先生《南唐藝文誌》等有所未收的;與此同時, 又注意輯集金石碑刻材料, 作《五代金石輯録》。這樣, 既有復核、訂正, 又作新的補充, 在此基礎上, 乃有《新編五代藝文誌》, 也就是作爲研究的成品, 嚮讀者提供既信實又完整的五代時期著作總目。
另外, 本書的時間斷限及取捨原則, 很有科學性。作者在《五代作傢的人格與詩格》中曾提及我關於這方麵的一種看法, 並錶示認同。我於1989 年爲美籍華裔教授李珍華先生點校的《五代詩話》所作的序言中, 曾談及, 我們若專作五代文學係年, 似可以從唐僖宗光啓元年( 885 年) 開始, 那時黃巢起義雖平復, 但各地節鎮已乘機擁兵自立, 中央朝廷名存實亡, 當時的一些著名作傢如韋莊、韓偓、黃滔、杜荀鶴等, 皆由唐入五代。作傢的創作, 包括其他一些曆史、哲學、藝術、宗教等著作, 確不能機械地拘限於王朝紀年。興武先生在前後三書中,都認爲五代文學創作及其他文化活動, 都應從唐昭宗朝開始考慮, 這樣纔可以有一完整的把握。而同時在具體取捨上, 又很謹嚴, 指齣顧、宋二《誌》 , 又誤將不少唐、宋人的著述闌入其中。有些是明顯與五代相隔較遠的, 如《渚宮舊事》, 著者餘知古, 本書《考略》中引《新唐書·藝文誌》地理類注“文宗時人”。按《新唐書·藝文誌》另一處亦有餘知古, 即《新誌》四總集類《漢上題襟集》十捲, 注雲:“ 段成式、溫庭筠、餘知古。”此爲徐商於唐宣宗大中十年至鹹通元年( 856- 860) 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 段成式、溫庭筠與餘知古在其幕府時唱和之作( 參見鄙人主編的《唐纔子傳校箋》捲八《溫庭筠傳》) 。則其《渚宮舊事》當也於大中後期在襄陽時所作, 雖然較文宗時晚十餘年, 但仍距昭宗有30 年。又如《五代記》著者孫衝, 《考略》中引《宋史·藝文誌》及《宋史》本傳, 明載其與寇準同時, 距北宋建國已有40 年。有些則是與宋初時間相接的, 如《江南録》著者徐鉉、湯銳, 都是由南唐入宋的, 但《考略》中據史書所載, 考明此書乃奉敕即奉宋太宗之命而作, 因此也不宜列入五代之書。這樣的處理確很規範。
本書另一新意之作, 是《五代金石輯録》, 就是據《寶刻類編》、《輿地碑記目》、《金石萃編》等著録的碑刻、題名等加以輯入。這些雖爲單篇, 未是成書, 但其中確有不少重要材料, 對於文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和用途, 因此不宜受過去藝文誌著録中傳統框架的限製。我這次通閱所録, 又有一新得,即興武先生此次所輯, 是按國彆編録的, 我發現屬北方幾個正統王朝的碑刻、題名, 數量並不多, 最多的則是南唐、吳越和前後蜀的。這使我想起《五代作傢的人格與詩格》中幾次提及,因北方戰亂頻繁, 南方相對穩定, 經濟重心南移, 文學作傢也逐步南遷。書中提及, 唐末後梁時南下作傢的主要流嚮爲西蜀和閩中, “沙陀三王朝”時期南遷作傢的基本歸屬, 以吳和南唐居多, 而吳越又少涉戰亂, 其國主也好文尚士。由此可見,金石輯録並不是單純的文獻資料, 我們由此可與文人趨嚮及文化流播聯係起來。
藝文誌, 作爲書目著録的一種文體, 是極有特色並極有學術意義的。清代著名學者王鳴盛在其所著《十七史商榷》中就說:“藝文誌者, 學問之眉目, 著述之門戶也。”( 捲二) 上一世紀90 年代前期, 原南京大學校長、著名學術前輩匡亞明先生任國傢古籍整理齣版規劃小組組長, 在製訂1991- 2000 年規劃時, 他特地提齣由古籍小組主持, 編纂《中國古籍總目提要》。當時我被任爲古籍小組秘書長, 就負責籌辦此事, 在我起草的《中國古籍總目提要編纂總綱》中, 就曾提齣:“古籍編目並不單純是一種技術性的工作。我國古代著名的目録學著作, 從漢朝劉嚮的《七略》、班固的《漢書·藝文誌》起, 一直到清朝的《四庫全書總目》, 都是傳統學術的綜閤研究。它們的作者大多能體現這一時代的學術成就, 反映一個時代的文化發展。”我現在引用十年前所寫的這段話, 是想進一步說明, 這部《五代藝文考》, 經過廣泛輯集與細心疏證, 就五代時期各類著作作係統、確切的著録, 可供學術界有效地利用, 其本身即又成爲一項學術研究成果。《舊五代史》 除記傳外, 有十誌, 但無“藝文”。《新五代史》僅有“司天”、“職方”二考, 根本不立誌,清修《四庫總目提要》明確指責:“此書之失, 此爲最大。”( 捲四六史部正史類二) 唐朝著名史學傢劉知幾曾提齣史傢必須兼有史纔、史學、史識三長, 尤以史識爲重, 但很奇怪, 卻在所著《史通》 捲三《書誌》中提齣沒有必要修藝文誌。歐陽修當不緻受《史通》的影響, 他在《新五代史》中曾兩次提及“五代亂世,文字不完”(捲五九《司天考》、捲六〇《職方考》) , 可見是受當時客觀條件限製, 文獻資料缺乏, 未能編修較有規模的《藝文誌》, 如《新唐書·藝文誌》那樣有四捲之多。《漢書·藝文誌》、《隋書·經籍誌》及兩《唐書》的《經籍》、《藝文》二誌, 一個很大的優勢是當時著録之書, 絕大部分後世失傳, 我們今天可據以查考當時著述情況。清朝及近世學者所補前史藝文誌之書,當然不像前人那樣能目睹原書, 但仍有兩個優點: 一是廣輯群書, 補前誌之缺;二是細核史料, 糾前誌之失。這種工作, 看來瑣細碎雜, 實則專研精治, 極有裨於今世。我個人是希望我們學界能多齣這樣實學之作的。
傅璿琮
2003年5月於北京
· · · · · · (
收起)